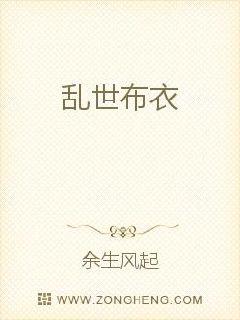第五十七章 生辰,忌日
进阁,阁门打开的一瞬间,晃如隔世一般,周染濯有些惊讶。
阁内陈设与夏景笙他们的并没多大差别,都是按礼安排的,这些倒看不出什么,但有一点:这偌大一座阁,这么大的院子里,竟一个下人也见不着。
夏景宸一堂堂的大将军没人伺候吗?
周染濯心里有疑,却也没说什么,还是先将夏景宸扶进屋中,谁知一开门,更为疑惑的来了。
夏景宸的屋中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还有一堆箱子,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摆的乱七八糟的,简直要没有下脚的地方了,竟也没人收拾。
“这都是些什么啊……”夏景宸也满脸的疑惑,在周染濯的搀扶下先趴到了榻上。
“将军,这些不是您的物件吗?”周染濯惊异的问道,难道除了夏景宸,还有旁人能在承啸阁肆意摆放?
“不是啊……”夏景宸皱着眉头,盯着那一堆物件想了好久,好一会儿了,夏景宸才突然想到,长舒一口气,低着头笑了笑,摇摇头叹气,似是无奈着。
“将军怎么了?”周染濯听了夏景宸的指示拿了烧酒回来,正见这一场面,便问了一句。
“没什么,只是才想到,怪不得屋里会摆这么多的物件,今日是我生辰,都是大臣们的献礼。”夏景宸解着自己的衣服。
“生辰?”
“是啊。”
周染濯更是存疑了,他从未见过哪个手握实权、位高权重的将军没人伺候,生辰竟还如此清静的,这不合常理啊,若是不识得夏景宸,周染濯估计会觉得这是一个被“打进冷宫”的人,旁人苛待他呢。
正想到这儿,周染濯突然听见一声“嘶”,回头一看,是夏景宸的伤口与衣裳粘在一起了,褪去衣服时,夏景宸吃痛叫了一声,周染濯赶紧上去帮着。
“你把那烧酒拿过来,往伤口上倒。”夏景宸趴倒,对周染濯说着。
“啊!直接倒?”周染濯拿着烧酒有些不知所措。
直接倒?那不疼死啊!
“这有什么的?”反倒是夏景宸觉得周染濯这反应很奇怪,像是已经习惯了疼痛似的,“赶紧倒吧。”夏景宸紧紧地抓住一旁的衣裳,闭上眼“认命”。
夏景宸已经这么说了,周染濯也只得照做,他有些不忍的倾斜手腕,烧酒淋在夏景宸的伤口上,连带着鲜血和烂肉一起流到地上,看着都疼。
夏景宸愣是一声没吭,脖颈上,手背处,青筋暴起,脸都憋红了,直至烧酒倒完了,他才吐出一口气,止不住的喘着。
“将军……”周染濯这才带着简直要扭曲的表情坐到夏景宸身边,手在夏景宸身边颤抖着。
“是我疼又不是你疼,你抖个什么劲。”即使疼到极致了,夏景宸还是不忘打趣周染濯一句。
周染濯没说话,而是又在夏景宸的后背上看了一眼,以前不知道,以为夏景宸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谁知他身上竟有这么多的伤。
夏景宸背上,大大小小的都是伤口,简直快没有一点好的地方,有些看着是旧伤的地方还有添的新伤,周染濯看着都揪心,还有一处,是有手掌大的青紫色淤青。
夏景宸才多大啊?他哪来这么多的伤?跟受了虐待一般。
“将军,您这身上怎来的这么多的伤口?”周染濯忍不住问了一句。
夏景宸扭过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大惊小怪,你要是去战场上多打几仗也就是个这样。”
夏景宸的样子,似乎早已是适应了这样的情况。
“今日又多了一个西江进犯,曹顺那个德不配位的,又战败了,真不知王兄说的留着他有什么用,早晚我得把他打下去,只是在这之前,我得准备准备,估计再过不了多久,我又要出征了。”夏景宸念叨着。
“将军有伤在身,怎可现在出征。”周染濯反倒是替夏景宸担心。
“你以为我想啊,这东江能用的武将倒是不少,像且臣哥那样的,只是这一战是两江交战,非同小可,只能我去。”
“那将军的伤?”
“忍忍吧。”夏景宸叹气道,“若真要开战,先让且臣哥去顶一会儿,战他一会儿,我也趁此休养,然后立刻赶赴前线。”
“臣陪您一块儿去吧。”
夏景宸探头看了看,像是觉得周染濯是犯了傻一般,“战场凶险,你确定?”
“将军去得,臣怎就去不得,臣不会畏惧。”周染濯的脸色异常坚定。
“那行吧。”夏景宸扭回头,盯着榻板上刻着的蛐蛐发呆,别说,周染濯这一句他还挺感动,“我这儿没问题,王兄说可以便可以吧。”
“哎对了,将军今日生辰?”
“是啊。”
“可臣听王爷说您的生辰在下月啊?”
夏景宸愣了愣,又低下头去,像是犹豫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才再次开口。
“今日……是我生辰,下月是王兄当年接我回府的日子。”夏景宸低着头,支支吾吾的说着。
“那将军生辰怎如此寂静?王爷又怎会记错日子呢?”周染濯的伤害持续输出,不断揭着夏景宸的旧伤还丝毫不自知。
“王兄没记错,我素来过的是下月的生辰,因为王兄接我回府的日子也是我的重生之日,而今日……是我生辰,可也是我母亲的忌日……”夏景宸的眼睛一瞬红了,当初自卑的心思也似乎被一瞬激发,那么骄傲的人现在都抬不起头来。
周染濯一听这话呆住了,这夏景言没提过呀!完了完了……
“臣不知此事明细,惹将军伤心了,臣愿受责罚。”周染濯赶紧认错。
“无妨,不知者不罪,况且,这事我也不太在意了,我母亲走的早,我连她什么样子都不记得了,后来也是乳母说,她是在我一岁生辰那日被父王下令杖毙的,我才知晓了……”
“那那个乳母呢?”
“因为苛待我,王兄下令发卖了,现下我也不知她在哪儿,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在乎。”夏景宸侧躺着,释怀了似的看着周染濯,周染濯皱着眉头,“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将军实在委屈。”周染濯低声说着。
这一句反倒让夏景宸笑出声来,“我如何委屈了,如今我有王兄照顾,锦衣玉食手握实权的,我都不觉得自己委屈。”
周染濯仍是那副样子看着夏景宸,他知道,夏景宸根本不在乎权势地位,夏景宸想要的只是亲情,这么说只是不想让人担心罢了。
“不过就是一生辰罢了,往日在战场凶险,哪顾得上过什么生辰,这都是常事了。”夏景宸晃了晃周染濯的手臂。
周染濯还是不说话,还是可怜夏景宸。自己是八岁那年失去的家人,一直痛恨夏家人,夏景宸却是一岁便没了母亲,这父亲也简直是一场噩梦,到头来,竟还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替父亲赎罪。
“嗨,你就这么想看人给我过生辰啊?”夏景宸被周染濯那皱着眉头不说话的样子逗笑了,他哪知道周染濯心中所想,还惦念着周染濯是因为没人给自己过生辰,“真是的,又不是委屈了你了……”夏景宸努努嘴,从榻边拿过一个长棍来,避开周染濯,用长棍将窗户顶开。
在窗户打开的那一刻,周染濯听见了熙熙攘攘的人声,他惊异的看了窗边一眼,又看回夏景宸。
夏景宸示意他走到窗边去看远处,周染濯走了过去。
夏景宸的承啸阁与别处不同,它是进门一个大院,两侧边是长廊,长廊旁就是高梯,上了高梯才能进到寝堂,当初建院时,是按照夏景宸喜欢站在高处看远方建的,他一打开窗户,就能看到后阁的一大片密林,郁郁葱葱,还有密林后的护城河,小时是只有风景的,可后来,却突兀的多出一个红房子。
“看那个红房子。”夏景宸示意周染濯。
周染濯向那个红房子看去,原来声音就是从那处传来的。
红墙金丝柱,玉碟银碗筷,绫罗锦缎衣,多少高官的子弟儿女堆积在哪里,熙熙攘攘,谈笑风生,他们哪会在意朝中现在是什么局势?好似袁国灭亡了都与他们无关。
“那不就在哪儿嘛,年年都如此,王兄知晓我们兄弟几个都不爱过生辰,便在王府后院建了一个礼堂,要送礼物的直接送阁里,要走形式的去礼堂走,反正别吵着我们几个即可,我是厌倦去跟人应酬的,所以素来不去,照面都懒得去打。”夏景宸嘟囔着。
周染濯回过头看着他,一言不发。
“我阁中又只有五六个洒扫的下人,多了我嫌吵闹,今日这又是围猎又是生辰宴的,估计都忙去了,这才堆积了礼品没人收拾。”
“原是如此……”周染濯应了句。
“门边的那个箱子里压箱底放着祭品,我是起不来了,你代我到前厅角落里去烧了吧,我母亲唤作陈昕柔,把名字写上。”夏景宸低声说着。
“好。”周染濯看着夏景宸将头埋在了被褥里。
打开那个大箱子,里面放着一个金盆,还有一袋子的祭品,全是陈夫人原本应该享有的锦缎罗衫。
可夏敬之为了保住自己名节打死了她。
周染濯拾着这一袋子祭品出去了,连带着那个金盆,一并带到前厅的角落里烧掉。
那几个洒扫的下人回来了,看着周染濯这一举动躲在一边窃窃私语。
“今年是周先生代替将军祭母?怎还有这样的?”
“嗨,陈夫人是个青楼烟花女子,想必也是将军知晓丢人了,这才让周先生来烧的吧。”
“嗯嗯此话有理,诶,我听说当年先王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打死陈夫人的哎。”
“快别说了怪吓人的。”
“这你们也敢议论!不怕将军听见了,剪了你们的舌头,再发卖了去。”
“行了行了不说了,干活去。”
这一切的一切,周染濯其实都听得到。
陈夫人遭人打死,传来的竟只是流言与谩骂,可怜。
夏景宸年幼失母,得到的竟只是奉承与孤独,可悲。
周染濯烧完了祭品便走了,或许在那高高的承啸阁之上,夏景宸还会在那里无声的哭泣,一叹生来悲苦,二叹生是孤独,不过那都与周染濯无关了。
生在这世上,谁都无奈,活着便是了。
周染濯走在路上,真不知心里是什么滋味,看着此刻的夏景宸,就像是看着幼时的自己。
可怜,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