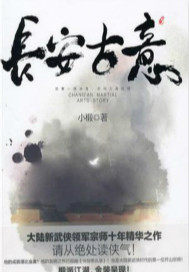“哈哈哈哈”,一阵响亮的笑声在土谷祠前的空场里响了起来,听那声音的欢悦,就可知不是七家村里的人发出的。
——祠堂之会的第二天一早,七家村的人都起得绝早。可能是因为——头天夜里,根本就没几个人睡着过觉。那一夜是格外死寂的一夜,猫狗们似乎也知道主人们的心意,叫得比平时都凄惶了一些。小稚也几乎大半夜没有睡着,他的耳朵一直竖着,听到了小孩儿们的磨牙声,也听到了女人们的低哭声,但那哭声一出嘴,就被旁人打断了,想来是那些人家的男人们出面止住的。但这乍乍出口却没下文的哭声却更有一种别样的悲凉,象一篇文章只起了个头,后续的都沉浸入一片无限的哀苦之中,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那天的睡都是无梦的,因为好象根本就没睡。那种睡眠象在一大块石头中游泳,拚力挣扎却也划不出半步。裴红棂也知道了村里发生的事,她只叹了一口气——年轻时,她生长尚书府,乡村的宁静在她来讲,象一个幽丽的梦。嫁给肖愈铮之初,她发现他最爱念那首《归去来辞》了,也曾取笑他道:“你就是从小州府乡下来的,你即那么喜欢那里,还来长安干什么?索性呆在乡下不出来好了。”
肖愈铮只笑笑,没说什么。好久以后,随着和他生活日长,朝野多事,裴红棂慢慢明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世,也明白了那个所谓故乡、所谓田园到底是个什么——它不是浮离于生活之外的一块飞地,同样也艰难地挣扎在人世所有的争斗磨挫之中,但它其中所蕴藏的那一种美、一种精神却依旧是对这挣扎无已的人生的一种超拨与拯救。肖愈铮说:“我也知道这世上没有一个‘桃花源’,但我入朝为官,就是为了可以让这世上哪怕有一点点象个‘桃花源’,然后你我可以携手,同赋‘归去来兮’。”
愈铮这一生都没跟裴红棂刻意说过什么情话,但有些话,每每让裴红棂事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比情话的滋味更醇更厚。那以后她开始喜欢那个古代的美女西子,也喜欢范蠡。她开始喜欢一句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思回天地入扁舟——可以说,这就是那个支持他夫妇一直相互扶持走下去的梦。
可如今,他的梦被打断了:
她——独归江湖悲白发;
他——天地未回死伏波。
裴红棂心中酸梗无数。
土谷祠里,一早,路阿婆就来了。她还带来了几个女人,也带来了好多好吃的,把土谷祠后面一直没用的大灶烧了起来。
冯三炳和几个老哥们也起得绝早,这时已带了一干青壮年汉子坐在土谷祠正堂屋内议事。他见路阿婆来了,不由站起身搓手道:“老姐姐,你老天拨地的,还来干什么?”
路阿婆笑道:“以前你们出门护镖,哪一次不是我起早准备干粮。难道村居了,你们要保家卫舍,我就要起变化不成?”
她说罢笑着就带了一众女人去入厨了。她的笑给了堂中一干子弟一种说不出的振奋与温暖——有时,女人是最后带有韧性的守护者。当早点飘香时,土谷祠门口就传来了那一阵“哈哈哈哈”的大笑,声音颇老,却很得意。冯三炳一撇嘴,已听出是武候庄吴光祖的声音。只听他在祠堂外笑道:“七家村待客很有礼呀,连早饭都预备上了。孩儿们,你们可想在这儿喝上两钟?”
外面就是一群汉子们的粗声哄笑。那老者吴光祖已走进堂来,淡笑着对冯三炳道:“我说冯三哥,客气就免了,我是送人来的。有两位客人想和贵村商量点事儿,我送到就走,早饭就免领了。”
他口气里全是一种戏谑意味,听得七家村里的人脸色发青。
吴光祖身边立着两个人,都三十出头的年纪,意气风发,颇有不可一世之态。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很高挑,淡青衫子,背后背了把模样奇怪的长刀;女的则很妖娆,一张脸上一双眼睛可恨小了点,嘴可恨大了点儿,皮儿可恨黯了点,所以她的眼神加倍的四处顾盼,以动生姿,人更是打扮得花红柳媚。
只听那吴光祖道:“这两位大侠是为了小庄不平之事,仗义出头的。这位……”
他让了让那位男子:“就是江湖中有名的‘东密’组织中‘永归堂’的左护法郎千郎兄了。”又一让那女子:“——这位姑娘你别看走了眼,却是有名的侠女,也是‘永归堂’的右护法蒋玉茹蒋女侠了。他们可是江湖中有名的‘雌雄杀手背对飞’。”
然后他冲那二人一点头:“二位说要和七家村私谈一下,——是不是我老头子留也无益,也好先走了?”
看来他们是说好了的,那郎千就点点头,吴光祖就带着一干子弟耀武扬威地走了。临走,一个小子还摸了祠堂门口一个女孩儿的胸口一把,口里故做惊愕道:“呀!你偷了我家的小兔子!”
听他一说,一众人就脸上涎笑,杂沓沓地去远了。
他们留下的还有十余人与郎、蒋二人助威。只听郎千咳了一声道:“当面可是旧威正镖局的几位镖头?”
冯三炳黑着脸没有说话。
他没答话,别人自然也不会吭声。
郎千淡淡道:“不知余果老余老人可在?”
冯三炳就缓缓地摇了摇头。——他不知内情如何,但据他听昨日二赶子的话猜想:东密只怕又与余老人结上了什么新梁子,所以才会为村庄械斗派上如此两位高手来。他武功搁下已有多年了,但一双老眼还不差,看着郎千与蒋玉茹站在那儿的气度与双眉间隐现的紫气,就已知:这两人端得称得上高手。
郎千面上就露出了一丝又有些轻蔑又有些失望的神色。看来他顾忌的只是余老人一人,想找的却也是他,所以才会这么又有些轻蔑又有些失望。据‘东密’总堂口传来的消息,余老人的踪迹已出陕西,一定就在这湖北境内,看来、他们这次算扑了个空,只怕难以见功。
想到这儿,他心头就已颇为不耐。淡淡道:“当年余老人刀劈的定基石上,我郎某人不才,也添了一道刀痕助助兴。既然他不在,我只是来问一声,还有没有人对这‘十’字有什么异议。如没有,武候庄和你们那些事也就这么定了。”
他分明对这些乡村争斗不感兴趣。七家村人当然不服,但有什么办法,人人面露怒色,却也说不出话来。昨晚,冯三炳的二儿子曾趁夜去那溪边一探,见到压基石上这男女二人留下的痕迹,就知这一战,自己一方未出手已经败了。
郎千交待了这句话本就要走,却见蒋玉茹忽然笑道:“师哥,我看,余老人不在,咱们不妨倒在这里等两天。咱们在这里混吃混喝,我看旧威正的人也颇小气,只怕会不耐烦。咱们总要去找那余老头儿,他们要不耐烦,派人出去找,总比我们亲手去找来得快些。”
郎千一愕,已知师妹有意以七家村的人胁迫余老人出面,这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只是他一向高傲,自己所思便不及此。他听了蒋玉茹的话,便停下步来。蒋玉茹已拍手笑道:“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我说,旧威正的伙计,姑娘还没吃早饭,你们出去我给杀上三七二十一只鸡来,把鸡舌头拨出来用新尖辣椒给我炒一盘。还有什么好的?对了,窖里藏的有什么老酒,都端出来我闻闻吧。”
她言笑晏晏,分明视七家村人如无物。座中的小伙子冯豹儿早忍不住,怒道:“臭婆娘,你欺人太甚!”他一边骂着,一边就向蒋玉茹扑了过来。
只见蒋玉茹转身对她师兄笑道:“郎哥,这儿可有人叫我是臭婆娘呀。听着新鲜,真新鲜,我好多年没听到过有人这么叫了。”说着,转身冲扑过来的冯豹儿抿唇一笑道:“你叫得真好听,再叫我一声‘臭婆娘’好不好?”
她嘴里笑得甜蜜,出手可极为毒辣,只见她一伸身,在冯豹儿未近身时,就已极快地一正一反、一反一正,转眼间抽了他四个大耳括子。别看她素手纤纤,这手下得可不轻,冯豹儿两个腮帮子登时肿了起来。冯豹儿哪甘如此受辱,一双拳一招‘双风贯耳’,就向蒋玉茹两耳照来。蒋玉茹伸手一拂,冯豹儿的双拳就已走了势,向下一低,蒋玉茹却把双胸一挺,迎向他一双拳头。冯豹儿大惊,他是守礼之人,连忙撤劲,但他功夫本不高,哪里就全收得回来,只听他惨叫一声,一双拳碰到一双绵软软的双峰时,同时觉得尖利一刺,原来蒋玉茹胸前却带了带刺的护甲。只听蒋玉茹娇笑道:“哥儿,我以为你真想打我呢,原来是借着题调戏我。早知道,真该把那件刺马甲脱了的呀!”
口里说着,一只手已拈着一只银钉轻轻钉在了冯豹儿的‘志海穴’上。冯豹儿只觉身上一酸一麻,全身已不能动了,双拳上刺伤之处却一阵阵麻痒传了上来,心里千虫万蚁般地难过,他忍着不肯吭声,一双虎目里泪水却熬不住,滴滴流了下来。他父亲冯克己知道这孩子一向坚强,这时流下泪,可见受的煎熬,怒道:“妖妇,你用毒。”
说着,就已和堂上十几个汉子一齐扑上。蒋玉茹却掠了掠鬓,身形忽然飞起,一飞就跃到扑来的人群之中,一只手里银光飞洒,却是她的独门暗器‘密门钉’。堂中的汉子‘嗯啊’连声,一个一个地跌倒。他们虽都已抛下武功日久,但这么十几个汉子联合出手,声势也颇惊人,郎千却没看到似的在一旁负着手,由蒋玉茹一人料理。只见堂中能站着的人越来越少,连冯克己在三招之后,也被她银钉击中,软倒在地,座上当年威正镖局的老人们也坐不住,一个个就已出手。蒋玉茹百忙之中还不忘掠一掠散下的一绺鬓发,娇声笑道:“唉呀,好凶,好凶。”
她口里娇呼,手下更不迟疑,那些旧日镖师,力不从心,明明知道这一招该那么使,偏偏到不了位,心中连连暗叹,却也一个一个就被她银钉撂倒。最后倒的一个却是独臂用一把九环大刀的刘老者,直到他倒下,堂中登时一寂。除了他们雌雄杀手二人,再就是武候庄的人,堂中除了冯三炳,再也没有能站着的。
后面厨房里的女人听到声音,也出来看,一到侧门口,就愣住了。只听蒋玉茹笑道:“怎么,我点的那道辣子鸡舌你们倒是上还是不上?上完了,乖乖给我传话给那余老头儿,说他要不来陪,我蒋玉茹这一顿酒只怕就要吃得长了。”
那冯豹儿被定在原地不能动弹,口里却骂道:“臭婆娘,休想,你休想!”
蒋玉茹退回他身边,笑道:“骂得真好听,我就爱听你骂,有血性。这么着……”她眼光一辣:“你今儿个要不给我骂到九千九百声‘臭婆娘’,你就别想我松你穴道了,骂呀,骂呀!”
冯豹儿气得双目恨不得滴血,口里一口钢牙紧挫,骂道:“臭婆娘,臭婆娘!”
一直坐在椅上蕴势不动的冯三炳忽一弹而起,他一弹起,一直不动的郎千出手却更快,也立刻弹起,只见两个人影在空中闪电般地交会了下,然后就见冯三炳抚胸而退,一步一步退回椅上,‘扑通’一声坐下,虽强忍着,却终于忍耐不住,一口血咯了出来。
郎千揉了揉自己的拳头:“嘿嘿,老威正,老威正,果然名不虚传”,他的一张脸上气色一时也暗了一暗,看来虽胜,也吃了些苦头。蒋玉茹已双眼一瞪,森然道:“七家村的人听着,你们已一败涂地,那向余老头递话的事,你们到底应也不应。”
冯三炳唇角带血,却不理她。冯豹儿口里叫道:“你做梦!”
蒋玉茹脸色一变:“好呀,七家村的男人果然都是汉子,那我就找那些女人来问问看。”她的一双眼已盯在了路阿婆那瘦小的身子上。堂中七家村的人大惊,地上的刘老者忽然伸手一拨,把肩井处的银钉一拨而落,合身就向蒋玉茹扑去。蒋玉茹没料他还有这一手,自己一根钉子居然没制住他。
刘老人这一招已是搏命的杀手,蒋玉茹一时来不及躲,出掌就向对方肩头劈去,座上的冯三炳忽啐了一口血,也搏命而出。他们老哥俩儿知道今日这败已成定局,这时要拚尽残生,拚掉一个算一个。但郎千却适时出手,一出手就击飞了刘老人,冯三炳的一只铁掌却已掴到了蒋玉茹的脸上,因为被她伸手一挡,这一下劲道已失,但还是‘啪’地一声脆响,只见蒋玉茹颊上就高起一块。冯豹儿虽不能动,却高笑道:“好,三爷爷,这一招漂亮,唉呀……痛快,痛快。”
那一声‘唉呀’却是他的痛楚**。蒋玉茹大怒,一脚向冯三炳裆下踢去,一个六旬老者就被她这一脚踢飞。冯三炳落在地上后,不由双手就抱向下体**。蒋玉茹却已然发狂:“姑娘今天要烧了这个破祠堂。奶奶的,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
她出道以来,被人一掌掴脸可还是第一次,不由不视为平生大辱,只见她拈起一根银钉,就要朝身已倒地的冯三炳眼中刺去。她有意刺得慢慢的,堂上女人们都捂了眼,低声惨叫,不忍再看。其中有一声特别尖细,却是小稚的声音。他可不是光叫,他一早就随了五剩儿来这儿旁观,一直插不上嘴,这时他和五剩两个孩子一齐合身扑上,要拦住那发了疯的母老虎。
蒋玉茹如何会把他俩放在眼里,一侧腿,两个孩子已一一被她踢飞出去,那根银针已缓缓地向冯三炳怒睁的左眼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