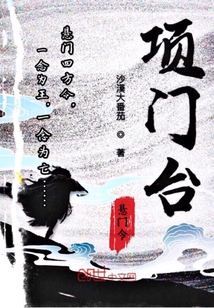话音刚落,他的身后便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魔兽!
它们嘶鸣,它们嚣张,它们席卷项门台的角落,它们张狂绝琅!
荻格·冕悬浮在半空中,他的表情异常严肃!金氓瞳在这杀气冲天的项门台里忽明忽暗。
他用力地握了握手里的特悉司拉姆权杖,声音低沉凶狠:“邪古琅!现命你率全魁煞境魔将;月漓,命你率魔兽全灵,严阵以待!听好,从现在起,凡入我项门台者,非有大用,取灵能外,一个不留!尤其——魔界!”
说到魔界,荻格·冕转过身:“业达目!你去查明真正杀妖茉莉的凶手!”他又慢慢地将头转回来:“断断不可能是雪天央!身型及脾气秉性,全然没有雪天央的样子!哼!魔界里的女人还没有蠢到杀了人还自报家门的!栽赃嫁祸?杀人放火?”
荻格·冕抬起头看了看天:“月黑风高夜?没有月便杀了我女儿,是谁给她的勇气?!啊?谁给的勇气?!”
荻格·冕怒吼一声,举起乌魔镰刀斧冲着项门台的地面便是猛地一记!
顺势乍裂的大地虽没有在深度上取胜,却依旧将地面掀起了两层厚土!
月漓喷出的水柱同卷起的砂石混合成泥浆,澎湃地涌在业达目的视线里,翻滚的暗潮中,是欲望而致的殊死之争!
荻格·冕站定身子:“和我玩儿声东击西?我要让你全魔域的魔灵之种陪葬!”
说话间,荻格·冕落回地面。他再次眯起眼睛看了看令候府:“战术一变再变!既然,我不轻生擒令候孤胁迫他去取灵棺木,但我也不会再走迂回战术!魔界要抢的东西,我又岂有放羊的道理?或许,令候府上,也能为我所用。”
业达目眨眨眼,心下一惊!他看了看,没敢说话。
荻格·冕又抖了抖身上的魔仸战甲:“既然,他令候孤墨黎师祖的身份被唤醒,那就打吧?!唤醒来做什么?不就是让我魁煞境死这项门台里吗?哈哈哈哈哈~看来,我荻格·冕建的这项门台,比将臣的声势大啊!”
说着,他又哈哈笑了起来:“瞧瞧,连墨黎师祖都来助阵!这么多的观众等着看我荻格·冕的好戏,我,一定得卖力演才是!”
他微微低下头,金氓瞳骤闪过一重幽蓝色的光影:“我,只许成功,没有失败!我要杀回魔界!我要搅和的魔界天翻地覆!密切关注令候府,说不定,就会有成为我们下一步计划的诱饵,许是人,许,是事儿~”
荻格·冕说着说着,声音又变小了。每当这个时候,业达目都知道,他是脑中想事!只不过,大部分时候,都是些让业达目匪夷所思的决定。
诸如......
荻格·冕忽然转头:“据说,这令候孤极为重感情?”
业达目一愣:“确实如此。”
荻格·冕勾起嘴角:“那就好办了~说到底,妖茉莉被杀,也是因他而起。那,我掳了他的女儿来我项门台耍耍,我就看看,他令候孤来不来救人!”
“魔王是说......”
荻格·冕没有顺着业达目的话往下说:“明日开四方门,再迎点儿八方客!”
业达目猛地抬头:“迎四方客?魔王是要再纳百姓?”
“能量多点儿是点儿!只是没想到,大家的触觉竟然如此灵敏?!我以为还能多玩儿些时日......”说着,荻格·冕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特悉司拉姆权杖,盯着上头那微弱的灵能指示光亮,他的表情忽然变得“温柔”起来。
他举起魔爪,轻轻地摸了摸权杖,忽然勾起嘴角邪恶地笑笑,声音很轻,像是怕吓到手中这不会说话的小宝贝一样,满眼的怜惜和疼爱。他挑了挑眉:“放心小可爱,我会带你杀回魔界!统领魔界!我会和你一起成为魔界战无不胜的霸主!我会带着你一洗雪耻!”
说到这儿,荻格·冕抬起头,左手横空摊于空气中!突然,乌魔镰刀斧携着七只乌鸦再一次赫然重现在他的手心!
“立地为王!永世为王!”
八个字一出,伴随着浑厚有力的回声,荻格·冕身后那一众魔兽一并仰天长鸣!诸多稀奇古怪的声音夹杂在一起,震得空气中飘散萦绕的黑气都打了旋儿!
【令候府】
项门台里魔兽的齐嘶惊醒了令候孤!
他抬头看了看府门外,眯了眯眼。
蚩鸾探长了脖子,伸出了右侧的龙头贴在门框处嗅了嗅,又抬头望了望天,转过脑袋:“是项门台!呵~真是丑兽多作怪!吓唬谁呢?要我吼,我的嗓门儿可大了去了!”
令候孤垂下头看了看手中的茶碗呆愣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轻轻地说道:“是时候说再见了!想必,这是项门台的欢迎礼?”
蚩鸾挑了挑眉,又撇撇嘴。他刚想开口告诉令候孤想多了,哪来什么欢迎礼之类的话,但后来,还是选择把话茬儿咽回了肚子里。
来到令候府短短两日,蚩鸾便看出,候爷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只不过,眼下的局势和特殊的身份与使命,胁迫着他不得不舍弃一些心里的人和物。加上今日,段坤的突然转性也让令候孤有了感慨。所以,这一句突然有关于离别的话,蚩鸾在分析之后,并没有觉得什么稀奇。
令候孤缓缓抬起头看向远处的地面,有气无力地说:“影子杀手说是来助我,可却不是真的留下。来一个,走一个,呵~老天算得可是够周全的。让它老人家费心了!”
这句话,蚩鸾听懂了。
他眨了眨眼:“呃候爷,看这影子杀手,应该蛮稳重的。所以,候爷应该放心才是。”
令候孤笑笑:“放心不放心的,我能奈他几何?我又能耐天几何?无论怎样,他也不是段坤。倘若说,世人皆可替代,又哪儿来那么多因离别而生的悲欢?为人一世,唯有断舍离,最为痛苦,却又不得不为啊!”
令候孤的语气很是沉重。
没错,一个断舍离的离愁别绪,便已经将令候孤的伤痛勾挑到了极致。而此刻月伴当头的夜晚,盈盈撒在主堂地面的斑驳月影,却是难照出其心中无言的悲戚。
突然,令候孤抬起头:“几时了?”
蚩鸾一愣:“您是想问高氏她......”
“对。”
蚩鸾絮絮叨叨着:“这个叫高氏的,怎么安排的?就那么一个人儿,给弄了三个名儿!又玲兰,又高氏,一会儿又仓山月的,把我都绕糊涂了。不过,谁让我是一头聪明的龙,不出几次,我便窥探了这其中的玄机!”
说到这儿,蚩鸾撇撇嘴,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令候孤看看他:“玄机?什么玄机?”
蚩鸾一挑眉:“我啊,我就是嗖~地一下灵光乍现,开动了一下我的小脑筋,又一下子慧眼辨识出,这三个名字,她就是一个人儿!”
令候孤垂下头,叹了口气。
蚩鸾见有点儿冷场,加上自己想搞活气氛,让令候孤稍微高兴儿点没成功,斜着眼睛悄悄地瞅了瞅后,便悻悻地缩回了脖子:“估计快来了。”
令候孤用鼻子“嗯”了一声,便没有再说话。他就那样呆呆地坐在自己的主榻上看向面前的桌案。
蚩鸾出现后,曾提及了面前的几个泥人。他曾劝说令候孤将泥儿收起来,以免有人会从这泥人儿而窥探到令候孤身上气场的变化,从而知道些不该知道的秘密。
但令候孤一直没有照做。
他之所以选择将那五个泥人继续摆在自己面前,目的就是为了警醒自己,使命在身,凡是以大局为重,要时刻保持理性,切莫因感性而误了大事。
忽然,令候孤笑了笑:“方才那声音,应该是兽吧?!”
蚩鸾转过头一愣。
尽管,此时的令候孤并没有看向他,但这堂上也着实能回答的,只有他自己。所以,蚩鸾龇着牙:“那应该叫魔兽!”
“魔兽?有什么不同?比如,和你?”虽然面前的是个动物,但令候孤依旧在问到“和你”时,语气轻了很多。
这个问题,对蚩鸾来说是又惊又喜。他瞪圆眼睛,两个头颅凑在了一起,一副匪夷所思的样子:“我?我,我和魔兽怎么能相提并论?哦天啊!我可是一头帅气的龙诶!那魔兽都死丑死丑的,哦我的天!就他们的指甲都不能和我比!哦,真是无语!这都什么跟什么嘛!”
令候孤看了看他“激动”得龙鳞都要竖起的样子,急忙拉回了话:“我不知道,随口一问。那,魔兽,究竟是什么样的动物?”
很明显,提到这魔兽,蚩鸾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也不知道是因为同类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想调节一下这府内尴尬的气氛,总之,在形容起魔兽时,蚩鸾眉飞色舞的,那白眼儿翻的,让令候孤瞅着都揪心。。
“呃......魔兽,我和你说侯爷,那魔兽长得都是巨丑无比的!根本就没有像我们龙族这般帅气!他们有可能会有长长的触角,或者粗壮的大腿,身体上挂满褐绿色的黏液,无数只眼睛,多出的,且不知名的什么器官,变异了的鳞片等等1”
说到这儿,蚩鸾顿了顿。为了配合这魔兽颜值碎了一地的说辞,蚩鸾更是浑身一个激灵!也不知道这激灵是为了演说效果,还是真的就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皱着眉头撇撇嘴:“咦~总之,恐怖得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