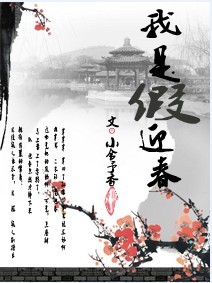这几天,迎春过得很悠闲,姨娘们都来立规矩,大家对迎春都是低眉顺眼的,表面上都很恭敬。迎春也懒得理她们心里到底怎么想,走过场一样的和她们周旋。迎春心里想,其实只要姨娘们不找她的茬,她乐得不和她们多话。
此时,迎春穿着轻便的短衣粗布裤子,和几个丫头在院子里踢毽子。泽兰忽然跑进来,欣喜的叫道:“夫人,快看看是谁回来了?”
迎春抬起头,只见绣橘慢慢的走进来。迎春马上扔了毽子,跑到绣橘跟前,迎春不等绣橘施礼,先怒喝道:“你怎么能下床呢?我不是让你好生养着么?”
绣橘眼里含泪,笑着说:“夫人,奴婢已大好,奴婢想夫人,想和大家热热闹闹的生活在一个大院子里。”说着,绣橘的泪滚落下来,缓缓的服下身子,给迎春施了礼。
迎春拉起绣橘,眼里也涌出了泪。
司竹在身后笑道:“绣橘姐姐回来就好,正好御了些我肩上的担子,我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呢。”
司竹的一句话,迎春和绣橘都禁不住笑出声了,满院子的人都笑了起来,院子里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气氛。
主仆正在欢天喜地之时,一个小丫头子来回道,说孙荣家的求见夫人。
“她来做什么?”迎春不禁皱起了眉头,让小丫头把孙荣家的带进来。
孙荣家的进来见迎春的打扮,先是一愣,马上又敛起惊异的神情,低着头,给迎春施了礼。
迎春也不和孙荣家的兜圈子:“什么事?”
孙荣家的回道:“夫人,陈姨娘让奴婢来禀夫人,大姑娘病倒了。”
“什么?!”迎春大吃一惊,问道:“大姑娘现在如何了?”
“大姑娘现在自己房中。”
迎春也不再理会孙荣家的,带着绣橘和司竹急冲冲的朝雨凌的院子里快步走去。
迎春进了雨凌的房间,早有小丫头为迎春挑起帘子。迎春进了里间,只见陈姨娘坐在床边上,用帕子擦着眼睛。雨凌躺在床上,双目紧闭着,沉沉睡着。
陈姨娘见迎春进来,马上站起身,给迎春施礼。迎春只是摆摆手。
迎春急切的问:“大姑娘到底怎么样?请了大夫没有?”
陈姨娘双眼通红的说:“大夫刚来过,夫人有所不知,这是大媳妇的旧病。大夫给大姑娘吃了定神的药,让她睡一会儿子。”
迎春走到雨凌床旁边,见雨凌的脸上起了豆粒般大小的红色疹子,这样艳红色的疹子,在雨凌白晰的脸上显得很刺目。迎春放下帐子,把众人带出雨凌的内间。
雨凌身边的大丫头锦纹双眼哭得通红,上前给迎春跪下,泪如雨下,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迎春急急问:“好糊涂的丫头,哭什么,大姑娘到底是怎样得的病,还不快点说出来?”
锦纹哭得抽抽搭搭的说:“夫人,是这样,中午大姑娘想吃清笋煲,我亲去告诉了厨房,结果,大姑娘吃完清笋煲后不久,全身就发出了疹子。奴婢大惊,夫人不知,大姑娘小时候有次吃了海参汤后,全身就是起了这样的疹子,奇痒无比,大姑娘当时把身上抓得伤痕累累,这病足折磨了大姑娘五天。”
锦纹擦了擦眼角,继续说道:“那次请了大夫,大夫说,大姑娘不能食海物。自那次后,老爷就告诉厨房里,大姑娘的饭食里全不许加海物。并让我们这个院子里的人都仔细着。这次不想,厨房里又弄错,大姑娘现在全身又起了这样的疹子。奴婢没照顾好大姑娘,还请夫人治罪。”说完,锦纹哭倒在地。
司竹把迎春扶到椅子上,迎春看向锦纹:“锦纹,你先起来,大夫现在是什么意思?”
锦纹哭道:“大夫开的安神的药就是为了让大姑娘先睡,免得再抓伤自己。但是大姑娘恐怕还要吃些苦头,因为药物只是缓解疹子,但不能根除,只能等身体内的海物余力慢慢散尽后,大姑娘方能大好。”
迎春沉思一下,叫孙荣家的:“把厨房管事给我叫来。”
孙荣家的应了声,就出去了。
孙荣家的刚出去,院里传来“老爷来了”,帘子一挑,孙绍祖大步走进来,一进屋理也不理旁人,急急问锦纹:“大姑娘现在到底如何?你是怎么服侍大姑娘的?如果大姑娘有个一差二错,可仔细了你的皮!”
锦纹又跪倒,哭着讲了事情的始末。孙绍祖始终皱着眉头,听完后,站起身大喝道:“孙荣家的怎么还不带厨房管事的来?!派人去催了!”
小丫头应着刚要出去,孙荣家的带着张财家的急急走进来,张财家的进门就跪倒。
孙绍祖冷冷的问:“大姑娘不能吃海物,你可知道?”
张财家的回道:“奴婢知道。”
“那为什么大姑娘会全身起疹子?你倒给我好好说说。”
张财家的犹豫的回道:“大姑娘要的清笋煲是奴婢吩咐木香做的,而且,奴婢还特意吩咐她,大姑娘是不能进食海物的,此事与奴婢并无干系。”
木香!迎春靠着椅背的身子,直了起来,怎么可能?!
陈姨娘此时忽然放声大哭起来,孙绍祖听见陈姨娘肝肠寸断的哭声,眉头皱得更紧,腾的从椅子上跃起:“还不快拿木香来!”
不多时,绑着的木香被两个婆子推了进来。一进屋,木香看见迎春,却没再看迎春第二眼,直直跪在孙绍祖面前,口称冤枉。
“冤枉?”孙绍祖头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我来问你,大姑娘的清笋煲是不是你做的?”
木香抽泣着:“是奴婢做的。”
“管事有没有告诉你,大姑娘不能食海物?”
“有。”
“那你还有什么冤枉的?明知故犯,妄想害主!你这个奴才都是不知道长了几个胆子了!来人,把木香拖出去,重打三十大板,打完送官!”
木香大喊着冤枉。
迎春叫道:“慢着!”
所有的人目光都集在迎春身上,连木香也哭着对迎春轻摇了摇头,眼中集着千言万语,有感动、有沉重、更有视死如归的决绝。
迎春却目光坚定的看向木香,意思很明显——我救定了你了。
孙绍祖像刚看到迎春一样:“哦?你有什么话要说?”
“话没问清楚就这样拉人去打,恐怕难以服众罢。”
陈姨娘上前跪倒在孙绍祖面前:“老爷,木香从前是夫人的人,夫人现在已经把她罚去厨房了。老爷就看在夫人的面子上,饶她这一回罢。”
饶了木香?还要看在自己的面子上。迎春柳眉倒竖,陈姨娘这样的话真可谓火上浇油,她哪里是为木香求情啊?!陈姨娘当着孙绍祖说出这样的话,孙绍祖定以为木香所做一切,都是自己指使的。
孙绍祖听见陈姨娘的话,果然眼睛瞪得滚圆,血丝布满整个眼睛,孙绍祖逼视着迎春:“木香是你的丫头?一切其实都是你暗中指使的罢?”
迎春也站起身来:“我没有!不但我没有,我还敢保证木香绝对不会是那种害人的人!”
孙绍祖眼睛忽然眯起一条缝:“保证她?哼哼,笑话,你凭什么来保证她?现在连你自己都保证不了自己是不是幕后指使!”
迎春大怒:“我没有!”
“既然你没有,你又为何拦着我打木香?你怕的是什么?”
“我刚才说了,话不问明白就打人,说出去,哪个能服?”
“那么,你说得这样的道理,哪个会信?”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没设计害雨凌,我也犯不着害雨凌。”
陈姨娘深深的看着迎春,嘴角显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夫人,如果木香真只是你无心之举,你定不会担了此虚罪。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今天在老爷面前,也绝对脱不了干系。
孙绍祖冷冷的哼了两声:“事情已经很明显了,你也没什么可是狡辩的了。木香害雨凌是事实,如果你不是指使,你就没必要拦着我打她,让我打完自去送她见官,如果是你指使的,你就趁早说明了。”
“我已经说过了,没害雨凌,木香也没害雨凌!”
“就算你说得通,木香会不会害别人,你怎么会知道?难道,木香真是你派在厨房里的作细?她只听命于你一人不成?贾迎春,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要对我孙府上下人等下手了?”
迎春大骂道:“你放屁!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卑鄙么?”
迎春和孙绍祖都怒目相视,空气中都弥漫着剑拔弩张的气息。
陈姨娘在旁边轻轻道:“老爷,您也莫冤枉了夫人,木香害大姑娘的事已在这摆着,不如让婆子们狠狠的打木香,难道还怕她不招,是谁指使她要害老爷的骨肉?”
孙绍祖思量后说道:“这个主意倒是不错。”
迎春眼里闪出利剑一般的光,直逼向陈姨娘。陈姨娘迎上迎春的目光,眼里除了冷外,再无其他。
陈姨娘原来就是要用丫头来逼自己,救木香,就要背上害雨凌的罪名;不救木香,就必须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人被打得死去活来,而且还要看着她被送去见官。
陈姨娘饶有兴趣的看着迎春,只等下好戏上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