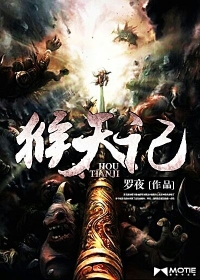两人启程回家。
机场,微风和煦,白岑看向对面的男人,没有开口,挺直的脊背犹如优雅的天鹅,一如既往的美丽。
不经意间转视,两人四目相对,此刻,她眼底似乎只有他。
“我们以后能经常见面吗?”
半晌,展昭辰心里憋了很久的话,此刻终于忍不住问了出来。
他悄悄攥紧了拳头,克制住了内心的激动,依旧淡然。
还会再见面吗?
闻言,白岑笑了笑,她开口说道:“有机会的话,是可以,好了,我要先走了。”
她摆了摆手,就如同对着普通至极的朋友,没有半分的奇特。
展昭辰苦笑了一声,很快掩下了那点异常,沉声开口:“好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就当是我欠你的,不必有负担。”
女人的眼睛微眯了起来,过了许久,薄唇才动了起来,“你不欠我什么,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还没有等展昭辰再说话,白岑就拉着行李箱转身,给了男人一个背影。
展昭辰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了一抹苦笑。
他早就已经没有资格去竞争她了,他早就应该知道的。
展昭辰在机场站了许久,天色黑了下来他才迈着酥麻的腿朝着外面走去。
白岑站在别墅,深吸了口气,过了许久才缓缓上前,敲了敲门。
“夫人回来了。”开门的人看见是白岑,礼貌的点了点头。
白岑没有让她声张,肚子拉着行李箱上了楼,其中,她尽量放轻了脚步,发出的声音,几乎可以称为低不可闻。
谁知道,才刚刚走到门口,里面的传来的交谈声便成功让她的脸色黑了下来,她手一紧,却也没有立马推开门,
“经年,你觉得你真的了解白岑吗?这么久不回来,在外面在做什么……”
她话没有说完,但其中隐藏的含义不言而喻,几乎快要摆到明面上,即使隔着木门,依旧清晰地传入她耳中。
白岑的脸色越发的难看,她是什么人,不带别人费心,只有心思龌龊的人,才会把别人也想成那个样子,不是吗?
她勾出一个冷笑,正准备推门而入,但在那一刻,她忽而鬼使神差的停了下来,急促跳动的心脏更快。
她,想要知道,陆经年到底会怎么回答。
里面,洛可还在继续,“大周末的,你放下公司的事情都愿意来陪她,可是她人都不见了,压根没有把我们家放在眼里。”
陆经年处理着手里的文件,裸露在外的半张脸上露出了不耐烦,他低头,一言不发,像是面对一团空气。
洛可咬牙,就在她以为他不会回答时,男人蓦地开了口,语气沉沉,“她的事情,与你无关。”
陆经年的话瞬间让洛可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但,她很快就反应过来,“经年,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她毕竟是进过监狱的人,跟普通人不一样!”
男人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了眼前的女人,黝黑的眼底,深不可测。
“不一样?”陆经年清冽的语气传入了洛可的耳朵里面浑身一个冷颤。
不过,很快洛可便恢复了正常,颇为语重心长,“你想想一个从监狱里面出来的女人,万一……万一想要家产,下手了可怎么办才好?”
洛可说话时语气里面似乎带了些许的哭腔,满是真情实意。
陆经年身上散发着寒气,眼神微眯的看向了洛可。
他知道这女人心里再想什么小伎俩,不过他可不是陆经年,这么容易就会被骗。
白岑怎么样他自己会看的。
陆经年刚刚想要开口说话,却被进来的白岑打断了。
“我当是谁说话呢,声音那么大整个别墅的人都快听见了吧。”
洛可听到声音朝着门口看了过去,脸上闪过了一抹尴尬的神色。
一瞬间便恢复了正常,反正她说的都是事实,而且,她什么时候又怕过她?
白岑犀利的语气冲着洛可说道,可是洛可的脸上却没有一点尴尬的神色。
反而觉得自己说的很有理,不屑的看着白岑。
反正在这里家她的地位总归是比白岑的大。
“昨天晚上你去那里了?一晚上不回家难道你是有别的落脚处了?”
洛可还的语气阴阳怪气处处都透漏着白岑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去旅游了,免得有些人说了不好听的话脏了耳朵”
洛可紧紧的握紧了拳头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一肚子的气。
女人勾起了嘴角,在等着她回来吗?这阵仗看起来倒是不小。
闻言,洛可飞快的掠过不快,她挑了挑眉,忽而冷嗤了声,训斥道,“去旅游,你的闲情逸致倒是挺多的。”
语句微顿,她蓦地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清脆的声音响彻,这才慢慢接了下去,“你到底有没有看清自己身份的自觉?你的首要任务是照顾好经年,而且,妈说过下周要去爬山,这段时间,他离不了你。”
最后一句话,她淡淡看了眼旁侧的男人,眼中含义意义不明。
男人微抬了抬头,白岑却像是听到了极为不可思议的事。
她抬眸,红唇微抿,克制住了激动的情绪,只眼角稍稍上扬。
爬山?是要她全程推着轮椅以送他上去吗,呵,真是个好想法,但凡是个正常人,都知道是刻意刁难。
更何况,她又不蠢,只是听出来是一回事,但是,现在并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
很快,白岑就将浮现在表面的情绪尽数遮掩,反而低低的应了一声,“我知道了。”
话音刚落,她放下手中的行李箱,来到了男人面前,单手用力,轮椅滚动着向前而去,路过洛可时,她方才开口,“我们先回房。”
陆经年默认,两人来到房间,白岑这才松了口气,她沉默了会,开了口,“其实…”
男人扭头看向了她,她滞了滞,还是面色如常的接了下去,“我这两天,都和展昭辰在一起。”
展昭辰?
陆经年的脸色骤然沉了下去,黑的仿佛能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