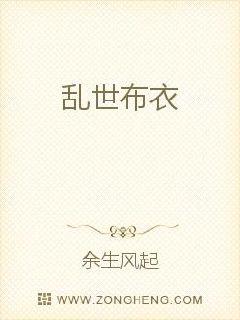荆晓伟的妻子是刚烈人。她把过来嚼舌根的娘家人赶走,想到看自己色眯眯的阎家老四,无奈之下吊死在房梁上。
家里买不到盐,买不到粮食,买不到柴炭。荆晓伟遣散了所有雇工和佣妇,关门过了小半年。
新县令到任了,但阎家联合了好几户在当地说了算的人家,有钱有人有势力,根本不怕荆晓伟翻得了天。
米面盐酱耗尽,荆晓伟通过地道离开,消失不见。
荆晓伟家的油坊易主,田地被瓜分,家里人不剩一个。
不到一年时间,荆晓伟引着上万方腊军杀回了胥口镇,身边还跟着当年乡社里几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弟兄。
除夕佳节,胥口镇在燃烧。
“你个贼配军,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引得方腊大逆祸乱乡里,阎王爷须也不收你!”
阎家辈份儿最高的那位老人,一位老秀才用颤抖的手指着荆晓伟,破口大骂道。
“还敢应口!”
荆晓伟身边,一个矮状的年轻糙汉一棒打来,打碎了阎老秀才满口老牙。
阎家老宅火光冲天。妇人在尖叫、哭骂、求饶,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倒在血泊中。
上了年纪的人被集中到一起,偏头不语的荆晓伟终于说话了。
“目前都是牵头的老狗,活该剜口割舌、断子绝孙的老畜生,真有脸说甚报应!”
荆晓伟说了一句话,内里蕴藏的无边恨意让阎家的老家伙们打了个哆嗦,“家里只剩我一个,也该教尔等老猪狗,尝尝甚么叫断子绝孙!”
一个接一个,满头是血、神色狰狞的荆晓伟,在阎家的老人面前摔死了阎家全部婴儿。而后带着几十人四下辨认,把见到的所有阎家人全部杀死,连阎家的雇工和佃户都没放过。
阎家上了年纪的老人,大部分死于心肌梗塞,有几人的眼角哭出了血泪。
剩下的几个阎家老人被活活烧死,临死之前有人喃喃道:“为何要惹这个杀才?!当初该是给荆家留条活路,或者将荆晓伟一并杀死……”
孩童被杀光,妇人和闺女沦为营妓,阎家几无人漏网。
荆晓伟犹嫌不足,带着数十好手星夜出发,在阎家被屠的消息传播开前,杀死了在外地做官的一个阎家后辈全家。之后奔袭三百里,杀死了在外地经商的一个阎家后辈全家。
“不在胥口镇的那两户,老子也不会放过,定要叫阎家断子绝孙!”
火烧胥口镇的当天夜里,荆晓伟把阎家老四的双眼和下体废掉之后,笑着对阎家的几个老人说道。
阎家断子绝孙,彻底消失在大周。
荆晓伟不听命令,执意脱离大部队去报私仇,恶了上官。
尽管立功不少,但直到今天的江滩血战,荆晓伟一直是带兵百人,没有升为小校。
带着手下弟兄连破两道羊马墙,荆晓伟看到一个手执亮闪闪手刀的投石车军士,再看看自己手里接近报废的尖刀,直接追了过去。
那个混沌的大周军士兵,竟然把手刀丢掉,一味奔逃。荆晓伟见状哭笑不得,手下却没有丝毫留情,捡起手刀捅穿了那厮。
没本事的人,却把刀磨得亮闪闪,这种行为太过不智。
荆晓伟不认识奚培盛,砍掉奚培盛的人头之后,直接奔向大周军的最后一道屏障。
此刻大周军和方腊军已经混战在一起,喊杀声震天。
大周军的优势军械已经起不到太大作用,除了床子弩和放置在后方的少量五哨炮外,其它的军械被方腊军缴获了小半,剩下的大半军械也是岌岌可危。
尽管知道不大可能,虞允文还是把希望寄托到了牛气哄哄的随州投矛营身上,指望他们堵住最大的缺口,为大部队撤入最后一道羊马墙争取时间。
随州投矛营辅一上阵,便震惊全场。果不其然,又是一个巨坑!
随州投矛营在南阳城外演练之时,排成五行,投掷之余交替前进,可谓是霸气十足。在襄阳和芜湖训练之时,也是可圈可点,一旦行进便视前方阻碍于无物。
然而到了战场之上,投矛营的五百军士居然缩成了一团,谁都不敢上前。
投矛营的指挥擦了把汗,也顾不得方腊军士兵还有多远,直接下令投掷。先找回士气再说!
挤成一团的投矛营士兵打着哆嗦,还如何保证投掷动作不失标准?
灾难发生了。三成的短矛命中前方、左前方或者右前方的自己人,三成投矛没有飞几米便扎在地上,三成投矛没有接触到距离较远的方腊军,只有十七支投矛插到了方腊军士兵。
成功杀伤方腊军士兵的十七支投矛,有大半都是蒙的。若是所有军士动作标准,以此时投矛营和方腊军的距离来看,应该伤不到一个人。
被吓了一跳的方腊军杂兵退开,紧跟其后的方腊军披甲精锐上前。
投矛营的下场已经注定。
虞允文双耳嗡鸣,眼中一片迷茫,呼吸都觉得困难。身形一个不稳,虞允文就要倒下。
部下死伤惨重,张天垒心急如焚。
见虞大人嘴角流下血丝,头往后一偏就要摔倒,张天垒和虞允文身边的一个护卫急忙左右扶住。
虞允文知道自己不能倒下,至少现在绝对不能倒下,不然两万多大军全完了。他咽下一口逆血,问张天垒道:“张将军曾告诫本官,不要同时在南北两岸登陆。”
“张将军不是觉得兵力不足,而是觉得身边的将领靠不住,是也不是?”
张天垒闭上双眼,咧开嘴角,露出难看无比的苦笑神情,狠狠点头:虞大人呐,你终于明白了!
虞允文深呼吸几口气,接着问道:“像投矛营的陈指挥,还有其他几个,多少都提过谨慎行军的问题,一点都不想出营作战。”
“这是因为他们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和其他人是什么货色,根本没有正面对阵方腊军的底气,是也不是?”
张天垒不想成为公敌,低头不再说话,但意思很明确。
虞允文再次软倒,张天垒及时扶住。
虞允文没有了一点力气。他勉强抓住张天垒的胳膊,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逆贼方腊亲临此地,我军能够支撑到现在,全赖张将军的两千部下拼命。”
“眼下战局危急,张将军何以教我?”
“本官高看了自己,小看了方腊军,有负国朝重托。张将军但有良策,一定讲来,本官必定全力支持。”
张天垒眼神闪烁,犹豫思考了三分之一炷香时间,狠狠一咬牙,“标下确有一策,如无意外,可保大部分兵马撤到南岸。”
虞允文先是松了一口气,恢复一些精神,接着却稍有犹豫,“只能弃北保南,保不住江北的阵地?江北阵地才能直接威胁杭州城……”
张天垒第一次打断虞大人的话,“虞帅,不可小瞧方腊军啊。战情至此,若我军勉强留在北岸,只能被方腊军压缩到江边一个小角落。”
“而后方腊军将我军的三哨炮、床子弩、投石车等军械倒转,我军只能徒增伤亡。”
“到时留在北岸的将士,就是任由宰杀的活靶子,很有可能全军覆没!”
虞允文几乎没力气思考,只是勉强撑着身体,权衡利弊。在内心深处,虞允文已经认可了张天垒的方案。
张天垒知道虞允文担忧的是什么,机智地添了一把火,“我军撤到南岸,也不能说是兵败,只能说我军的谋划成功了一半。”
“我军还是在钱塘江占据了一处阵地,永乐伪朝依旧是被我军切成了两半,只是打了些折扣而已。”
虞允文双眼一亮,竭力提起精神道:“从现在开始,大军一切行动,全赖张将军做主!”
两个时辰后,张天垒带着一万四千残兵,退到钱塘江南岸。
因为有一部分勋阳步卒拼命,一部分番兵死战,虞允文还及时发出了鼓舞大军奋战的手书,彼时的南岸阵地还没有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