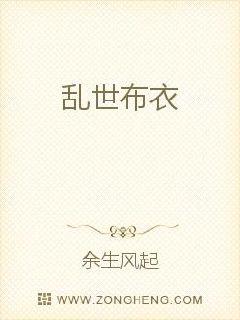决战方起,大周和永乐朝迎来最惨烈的一战。
几位宰执很清楚,调集一部分京西南路士兵回援,能够极大地鼓舞留守京西南路部队的士气。但他们不会让刘成栋从战场上抽走太多人。
在芜湖-建康-镇江一线养伤的大周士兵已经超过两万人。
除却刘成栋本部,以及挑选出的、来自京西南路各地的几百士兵外,其他回援士兵只能从伤兵中挑选。
刘成栋在山林内交接防务,等到两千多兵马全部交接防务后撤,便会直奔长江。
供李响驱使的人手接近千人,分得很散。
为节省时间,李响命令刘盛、雷达、张老头、王晓晨等人,带着鱼家岭和山林内的人经老虎潭北撤,到芜湖乘船西行。
李响自己从杭州城下出发,带着杨营东、大牛等几百人到湖州城坐船,直奔建康城和刘成栋汇合。
作为交易条件的一部分,方维良被永乐朝扣在杭州城中。
不仅是方维良要暂时留在江南,成吏员、张清平、丁史航和张永年也要留下。
成吏员将会主导和江南工商势力的对抗,他必须确保完成虞大人的条件。
张清平负责保护成吏员等重要人物的安全,丁史航带着一百多人充当必要时候的打手。张永年善于操船,还能打仗,负责节制在江南办事的船队。
尽管暂时不能回山,还要继续打仗,但听说要回到京西南路,还活着的人都兴奋了。
在京西南路作战,总归是在家门口厮杀,能够保留全尸回到山里。
然而有些人能够回去,有些人再也回不去了。
丁家老三蹲在木板床前,看着身受重伤、处于弥留之际的二驴,心神失守。
前几天在山林中打仗,二驴挡在丁家老三前面,被一根锈迹斑斑的长枪刺中肩头。天气炎热,伤口感染,他能够活到现在,在大周已是奇迹。
二驴发着高烧。他突然觉得身体活泛了一些,用力睁开眼睛。
半炷香之后,视野清晰了些。二驴露出一嘴难看的牙齿,声音好似破风箱,“有劳诸位哥哥看顾,二驴感激不尽。”
“我想,想和丁家哥哥单独说几句话。”
过来照看的庄内子弟以为二驴要说遗言,抱拳道声珍重,先后转身离去。
丁家老三形容枯槁,支撑不住身体。他擦擦脸上的污垢和泪痕,急速膝行到二驴身边,握着二驴的手,声音颤抖道:
“三哥听着呢,兄弟慢点说。哥哥听着呢,听着呢……”
惨白的面容上,忽地浮现几丝血色。
二驴情知自己没多少时间,勉强笑了笑道:
“寨主和老寨主都是厚道人,公中的几位先生从来不欺负人。有哥哥照看家里,俺心里很放心,哥哥一定要给我妹子找个好婆家。”
二驴压低声音,气若游丝地说道:
“咳咳……哥哥当时急着立功,带着俺和另两位兄弟查探德清县城的危局。后退的时候被方腊军发现了,于是哥哥将两位弟兄丢给方腊军。”
“之后见到了庄主,哥哥便说两位兄弟是主动保护咱俩而死。”
丁家老三身体一震,不敢看二驴的眼睛。
二驴回了几口气,流着泪说道:
“寨主大人在山里不止一次说过,使用下作手段害自己人的,是狗!”
“哥哥和我得到了寨主大人的看重。可俺梦里总是,总是梦到死去的那两位兄弟。他们是被哥哥害死的,俺也有份!”
“俺要去了,俺会在下面跪着,让两位兄弟原谅哥哥。二驴愿受阴间的任何刑罚,只盼哥哥能好好活下去。”
“哥哥可否答应二驴,好生照看那两位弟兄的家小。还有,以后不要再害自己人!”
丁家老三抬起头,通红的眼珠子一颤一颤的,泪如泉涌。
五息时间过去,丁家老三忽地抽出尖刀,从手掌上划过。
“佛眼相看,我丁家老三在此立誓……但有违背,管教我目中流血,子孙难以保全!”
二驴含笑而逝,丁家老三嚎啕大哭。
柴薪熊熊燃烧,数千人静静地为近千具尸体送行。
回程数千里路途,况且天气炎热,更兼士兵地位低下,所以一律带回骨灰。
被丁家老三救下的袁韧语戴着面巾,问同样是江南出身,刚刚升任什长的尚云飞道:
“二驴死了,丁三哥竟然悲痛到无法站立的地步。不愧是从小一起张大的弟兄。”
“奴家将留在成夫子身边,安抚寨主大人救下的妇人女童,让她们安心。”
“尚家兄长此番到京西南路,还要在战场上珍惜自家性命才是。”
尚云飞看着手中针脚细密的平安符,再看看双颊绯红、快步离去的袁韧语,怅然若失。
大战之中,底层小民最无奈。活下来的人在性格上总有大变化。
身高体健的袁韧语,对有着类似经历的尚云飞天然亲近。相处不过月余,已有一起成家的意思。
尚云飞却带着几个小拖油瓶。前路扑朔迷离,他不想耽误袁韧语,打算再等等看。
到达广德县城后,正逢一批方腊军俘虏被带到这里斩首示众,人手紧缺的县令要求刘盛派兵协助。
左右不过一刻钟的时间,刘盛答应了。
江南的官府之所以要将一些俘虏分送各地处决,主要是为了提振军心士气,抚慰损失惨重的士绅,以及失去一切的百姓。
十名遍体鳞伤的方腊军被带上台,台下百姓用烂菜根、泥巴,甚至粪便、石头和泥块儿表达自己的愤怒。
围观百姓有哭喊方腊军作孽的,有揭示方腊军罪行的,情绪非常激动。
尚云飞拿上衙役常用的杀威棒一顿敲打,把手执粪便、石头和泥块儿的百姓赶到一处,再把人交给官差。
转身回返,很自然地朝台上一撇,尚云飞突然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愣怔在原地。
“荆晓伟?!是你吗?荆晓伟!”
尚云飞甩开身边两位弟兄的手,抓住一个披头散发的方腊军俘虏,大声喝问。
还好尚云飞保持着理智,向高处的主座弯腰抱拳,请求问几句话。
县令大人眯眼看了看日晷,发现时间还充足,朝坐在左手边的刘盛点点头。
刘盛摆摆手,让尚云飞快些说话。旁人巴不得躲得远远的,这个尚云飞倒是讲情义,在这个时候也不忘旧识!
荆晓伟因功升职,带着五百方腊军转战杭州以北,被击溃石宝大军的韩世忠部挟威所擒。
双眼重拾焦距,麻木的脸上露出别扭的笑容。
荆晓伟眯起肿胀的双眼,花了十几息时间才搞明白状况。
眼前竟是四年前在杭州城结识的尚家哥哥!
“尚家哥哥,你为何在这里?哦,也是了,小弟投身方腊军,哥哥当然可以投身大周军。”
尚云飞又急又气,猛地摇晃荆晓伟,喷着唾沫道:
“你不是返乡经营家中生意了么?还控制着团社,如何被方腊军捉了?”
荆晓伟没有一点力气,任由尚云飞晃动身体。
他身上的麻衣破烂如缕,黄白色流脓的伤口招引苍蝇。浑身上下脏污一片,恶臭难闻。
荆晓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猛地推开尚云飞,摇摇晃晃地直身而起。
他低头抖肩,发出“嘿嘿嘿”的诡异笑声,牵动了脸上三处深可见骨的伤口。
“尚家哥哥也以为,我荆晓伟是受不过方腊军的折磨,才投靠了他们?”
“哈哈哈!你也和其他人一样,以为我是那天不盖、地不载、该剐的贼!”
“狗官和狗士绅夺我家业,害我爹娘,逼死我息妇,还要赶尽杀绝。我拿大斧头砍他娘,砍得几家人肉片片儿飞,立时绝灭了一户。”
“投身永乐朝,老子是自愿的!”
“老子见到穿儒袍的老头儿就杀,见到大户的女儿就奸,见到狗官就砍下他们的头当夜壶,刀下人命何止过百……”
多大仇,便有多大恨。
刑场前的百姓噤声不语,人群中弥漫着一股寒气。
广德县令即使修养再好,想到某些官绅的下场,也免不了头皮发炸。他不容荆晓伟再说下去,扔下来一支火签牌,拍案而起,大声道:
“如此猖狂,不知悔悟,你拖谁的势要!”
“不必等午时,先斩了这厮!”
头颅滚到人群里。
百姓立即忘掉了荆晓伟话中的惊天恶行,不再思考荆晓伟的悲剧因何而生,再度哭骂叫喊起来。
炊饼蘸着人头血吃,治痨病啊!
听闻荆晓伟家中剧变、陷入呆滞的尚云飞,在广德县令动怒的第一时间被弟兄们抬走。
尚云飞被众人抬着后退时,分明看到刀落之前,荆晓伟眨了眨右眼。
心照不宣的小动作,被荆晓伟再次使出来。之后便是永别。
尚家哥哥,我荆晓伟不想连累你……
尚云飞知晓荆晓伟的意思,情绪陷入低沉。
队伍从广德县再次出发,急行军到了宣城后,换乘十几只漕船赶往芜湖。
“人血炊饼是假的。”
此时尚云飞正靠着船帮,叉开腿休息。听到有陌生的声音似乎在和自己说话,他疑惑地睁开眼睛。
眼前是身穿青色对襟窄袍的一位年轻人。
年轻人五官匀称,肤色较白,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手脚、脸面和衣衫却收拾得很干净。
盘起腿,直起上身。尚云飞抱拳,低声问道:
“在下尚云飞,小哥是救死扶伤的大夫?为何有此说法,人血炊饼还能有假的?”
“什么大夫,我只能算郎中,离大夫差得远呢。我叫渠正言,没你大,称我云飞便可。”
渠正言这种学医的年轻人,平日里说话的机会便少。除朋友外,学医的年轻人很少彼此交谈,因为很容易扯到医术上面,使自己更累。
紧张的江南战场带来巨大精神压力。如今暂时离开危险之地,渠正言便找上旁边看着顺眼的厮杀汉说话,舒缓心神。
渠正言张口便是医术。见尚云飞一副求知欲,他心中稍有得意,从椅子上坐到船板上,凑近说道:
“我跟你讲,人血炊饼治痨病的说法啊,也不知是哪个倒街卧巷的浑人胡说。”
“毫无根由可言。即使有那么几例治好的,也属巧合,或是其它物事起作用。”
“便如前日,那荆晓……咳咳,反正那些人多有病在身,创口都流脓了。都是活不久的人,吃下他们的血,简直是嫌命长!”
“还不听劝……”
沿途不断和运送物资到杭州城下的船队错身而过,很快到达了芜湖码头。
渠正言下船没多久,正和王晓晨等人站成一圈,听张老头大讲之前几日的防疫工作和医治情况,便听到一个爽朗的声音在叫他。
“渠贤侄,渠小子!”
回头一看,渠正言眼睛瞬间睁大,惊喜莫名。
渠正言朝张老头行礼,在张老头针扎般的目光中,在王晓晨等人幸灾乐祸的目光中奔向呼唤他的那位绢袍中年人。
作揖行礼后,渠正言一脸兴奋,笑道:
“邝叔叔,您不是在虞大人身边做事么?为何到了这里?”
渠正言口中的邝叔叔,自然便是照料虞允文从汴京南下的邝医官,只是此时没穿官服。
邝医官用力拍拍渠正言的肩膀,笑容满面道:
“不错不错,你小子身子骨挺壮实!”
然后邝医官压低声音,在渠正言耳边说道:
“自然是虞大人有差事交给我。此事还与李指挥有关,此时他应已到建康了吧?”
“算算时间,寨主,哦不,指挥应该到了建康城。”
……
邝医官和渠正言叙旧的时候,李响正在建康城的春风楼大宴宾客。
西门博代表和李响合作的江南本地大户,韩彦璋的大表哥代表武人群体。赵志强也派了一个管事过来,想在李响接下来的大计中分一杯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