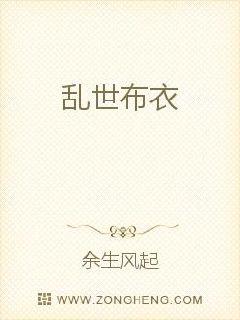申老鹰郁闷地回到家中的时候,李响刚从知州衙门后宅出来,和方维良、亲卫汇合,到驿馆休息。
大周的邮递驿馆体系,由太祖柴荣和众多通实务、明疾苦、广博学的臣子定下。两百年倏忽而过,这套体系出了好多小毛病,还有几次运转不灵,但仍旧是这个时代最科学、最好用、最可靠的邮驿系统,没有之一。
前朝的邮递系统耗费了大量民力。有鉴于此,从乱世中挣扎而出的重臣和站在金字塔顶尖的士大夫们开动脑筋,把传送官方文书、军情急报的活计交给数量庞大的厢军。
大周攻灭四川政权和江南政权后,开始对全国的驿站进行整理。在驿站递铺的设置上,学识广博的士大夫们讲究因地制宜。
甘凉和关中时刻面临着吐蕃、回鹘和西夏的进犯,在主要的军事要道上,每隔十到二十里便有驿站,供骑马的驿卒换马、休息,或直接换人。
河东路和京东路,尤其是靠北的地方,驿站多种多样。有位于道路关口的驿站,结构坚固,几百厢军进驻其中,可以节节抵抗辽国的攻击。有靠近大城的驿站,可以起到预警的作用。有关口附近的大型驿站,本身便是小型堡垒,可以和大周的关口要塞形成犄角之势。
水路通达的地方,“水递”的形式应运而生。黄河里有快舟和皮筏子,长江里有不断改进的桨帆船,汉江和淮河里有转向灵活的木轮船。
四川路、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岭南两路,以及大周西南的几个番部和羁縻州,山陡难行。这些地方的官府驻军只能依靠当地山民,翻山越岭地传递一些消息、命令和急信,俗称“登山递”或“过岭递”。
大周腹地在一般情况下安享太平。依照朝堂的规定,大周官府在没有兵患的地方,每隔二十到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十里左右设置一个邮递铺子。
繁华不期而至。好些驿站递铺的厢军乡兵之流,开始接一些民间的急信和物件儿,赚些外快。大周也免不了军队崩坏、吏治腐化等问题,在某些方面还更严重些。好些充当“铺兵”、“递夫”的厢军乡兵,也就是民间称为“驿卒”的家伙,拿着七扣八扣的当差钱根本养不了家,自然要想办法求活。
大周相比历朝,最难得的地方在于,顶层的士大夫更加灵活,在缝缝补补、维持民生稳定的大事上更见功力。眼见逃亡的铺兵递夫越来越多,大周朝堂的宰执开始行动。
邮递驿馆。“邮”跟“递”从整个大体系中被分割,不论官绅商户,只要掏钱就可以利用邮递铺传送消息。当然了,距离越远,邮寄之物丢失的可能性越大。想要赔偿?一般情况下没戏。
能够提供住宿饭食的驿站也进行了一定改革。以往只有五品以上的高官凭借兵部印信和枢密院发放的驿券,才可以使用驿站。时间流逝,私相授受、薅大周羊毛、贪污钱粮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朝堂干脆放开了一些驿站的使用权,底层官员、士绅商户只要手里有驿券便可使用驿站,高官和高级将领依然优先。
为大周急递铺、驿站流血流汗的驿卒、铺兵和递夫,有靠着外快和福利活得不错的,也有担心自己会饿死的。总有人不甘心活得不如狗,这些人会啸聚为盗,成为神出鬼没的绿林强人。方腊起兵之后,便有很多有着驿卒铺兵过往的团伙投靠,在方腊军的定计中贡献了很多情报。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就别指望更夫能说第二句话。
听见更夫敲锣,湖州城的兵房民屋陆续点起了灯盏灯笼,城墙上、军营中也燃起了火把火盆。一片片或大或小、或分散或密集的烛火明暗闪烁,呼吸也似地在赌气,挑衅天上的银河。
湿寒的空气被微风抱走,空气澄净了一些。
湖州城内,被断壁残垣分开的片片灯火不敌璀璨星光,却不服气,向太湖上官军船队亮起的灯火群求援。巨湖大城被各式灯火联结一处,想凭此人间盛景对抗高冷夜空。
小风袭来,气势全消。
万千灯笼、火盏、火盆同时摇曳,如同几十群被惊扰的萤火虫,很快散而复聚,安静下来。
群星眨眼,好似在嘲笑,“小样,跟我斗……”
湖州城内的两个驿舍曾被石宝军使用。方腊军撤离仓促,没有多加破坏,除了脏乱一些外,两个驿舍居然位列湖州城保存最好的建筑之二。
城西驿舍,李响的房间。大牛把灯盏挑亮,带着两个亲卫守住门口。
方维良拱拱手,“韩招讨果真讲情义,有古风。庄主得到了附属民团首领的名义,便不怕在江南受太多刁难了。”
李响沉吟许久,缓缓摇头,“没这么简单。”
涉及到官府、军队和地方势力的事情,还是成吏员更擅长。如今成吏员正没日没夜地在荆州忙活,李响只能靠自己了。
庄主大人嚼了几颗果干,咽下后继续道:“大周历来有乡兵弓手和民间会社的存在。韩招讨给我一块民团首领的牌子,办起事来确实方便,带着几百庄丁也不怕犯忌讳。”
“但……你俩没在场。当时韩招讨使说让我随军参战的时候,有两个指挥使看我的眼神就很不对。当时没多想,现在本庄主仔细琢磨,这是有人怕韩将军念在我岳父的面子上,分战功给我啊。”
“湖州不能待。人情是有限的,若是留在韩招讨使身边,韩招讨使当然会更加在意岳父大人的安全。但人情消磨,某些指挥使、营指挥又防范着本庄主。本庄主留在这里,对岳父而言,还真不知道是好是坏。”
机智灵活却行事跳脱的丁史航被李响提点了一路,已经开始收束性子,不会张口就来。像他这样的庄内年轻人,非常缺乏对大周行事规则的了解,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夫子说话的重点在哪里,只好低头不语。
方维良盘算着李响说的战功问题:庄主说的很明确,有人担心明月庄的“庄丁”分走功劳。但庄主只带着两百多人,什么情况下才能分走那些人的功劳呢?等等,太湖上的船队未免太多了,难道……
等了十几息。方维良见身侧的庄主门生没有答话的意思,这才拱手问道:“庄主是怀疑,会有大量官军赶到江南,对永乐伪朝发起致命一击?”
李响摊摊手,“除了永乐朝大溃,本庄主想不到有其他可能,能让本庄主带着几百人浑水摸鱼,分走一些战功了。那些船队你们也看到了,什么船都有,连海船都派来了,说明什么?方腊在这个节骨眼上称帝,糜烂江南,触及了国朝的逆鳞。”
能够猜测到官军很快大举南下,并不是李响在战阵之道上造诣很深,而是原时空便有很多水陆联合运兵的例子。太湖上摇晃着的几百艘空船用途各异,除了配合两腿跑的大军反攻永乐伪朝,还能有什么用途?
丁史航眼睛亮亮的,“庄主,真不能分一杯战功?”
方维良非常佩服庄主的大局观,拱手请教,“那庄主的意思是?”
“咱们去安吉。”显然是考虑了很久,李响用茶水在桌上画出湖州城、安吉县城和德清县城的位置,“安吉四面环山,只有北部有大路、河流通往外界,向东通过小路,可以到达德清县城。咱们以民团的名义进驻安吉,除就近援助岳父外,好处有三。”
“第一。安吉几乎隔离于战场之外,到那里去,湖州这里的将官总不会怀疑,本庄主还会分走他们的战功吧?救岳父要紧,战功什么的不要也罢,本庄主又无意当官,拿来作甚?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
“第二。据闻江南的很多百姓躲避方腊军不及,穿过山岭溪河逃到了安吉。既然有民团首领的招牌,不用太可惜了,咱们便在那里招些好手。”
“第三。安吉西北通广德,东北通湖州,依靠江南的运河水道,咱们可以方便地买进卖出。公中吃紧,岳父要救,生意也要做起来!”
写完几封密信,仔细地用蜡油封好,锁进书桌里。站起来活动了几下臂膀,韩世忠感叹了几句写字不容易之类的,便吩咐李响白日里见过的那位韩姓小将去请子安先生。
韩世忠先问子安先生最近有什么麻烦事情,听完后不屑道:“辛苦先生。整日里和士子、绅民、掌柜之类的打交道,本招讨看着都累。”
“那些人家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战事正紧,他们还有脸让本招讨分兵,好夺回他们的桑园、宅院和作坊,还大肆买地……”
子安先生身子骨弱,最怕湿气,袍子里裹得很厚。这位年轻时得罪过太多人的老举人心说:哪里只有士绅在圈地啊,中军大营的那些将官都被拉下水了,在趁机攒家业呢。不然那些士绅哪里会有恃无恐,伪造文书、圈占田产、打压小民……其中还有几个姓韩的年轻人,咳咳。
韩世忠骂完之后,喝了几大口茶,理了一下胡子道:“以先生之见,那李响小子如何?”
正题来了。
子安先生眯眼细思,缓缓说道:“这位年轻人应变机智,处事不惊,见闻广博,倒也当得青石先生的弟子,刘成栋的女婿。只是……”
“总感觉他身上好似蒙着纱幔,看不清其根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