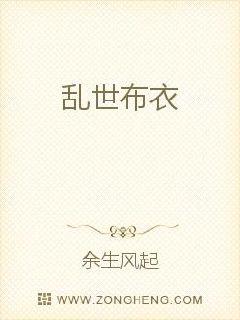鸡鸣声响起。
李响感叹了一下公鸡这种生物的粗大神经,听完李梦空等人的讲述后闭上眼睛,靠上枕头思考着什么。
李响中箭时,衣袍下有细麟甲,还贴身穿着锁子甲,衣甲间用丝绸衫相隔。戴的铁盔更是三层防护,从外到里分别是熟铁、锁子甲和皮甲,并与上身甲牢牢地结合在一起。爱惜小命的李响,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其实,李响的铁盔还有鬼面钢甲,中箭时没有戴罢了……
事实证明,李响的担心没有多余,“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桥段还是发生了。黄立仁联合其他士绅大户凑出的死士,挑准了庄内人心不稳的空挡,使用强弓硬弩射中李响三箭,分别命中了头部、胸口和小腹。
然而并没有用,李响同志的甲太厚,明月庄在外科手术上进步很快。
命中李响的三支箭都涂有剧毒没错,但穿透双层甚至三层甲后,箭矢已没几分力气,只是靠锋利的尖端才入肉半分。医卫处的五位领头人取箭、清创、缝合、施药……李响只是沾了一丁点儿毒素,不到一天便醒了过来。
成吏员作揖,慢慢道:“庄主,是不是要通知汉江边的三位,以及明月集的王家兄弟采取一些行动?属下以为,官军如此做法,已是彻底破掉了黄家的谋算,没准还会惊动朝堂。”
“在形势未明前,庄主自可称病不出,等十堰知州那里拿出章程,再现身不迟。”
议事堂的庄主卧房结构严密,又与外面隔着好几道厚墙。外面的哭喊传进来,只剩嘈杂。
李响却不难想象外面的惨况。刘氏亲族自食其果,但想到往日里称呼自己“庄主”的庄民遭遇如此悲惨事,李响难免恻隐之心。
摸了摸头上的绷带,李响慢悠悠道:“既然官军已经把事情搅乱,那不如更乱一些,给知州大人出面说和增加一些筹码。”
“传令,让曽老、雷伯、吴小玲冲击一下明月集,把暗中使绊子的大商户给本庄主砸个干净。但不能杀人,提前通知王三,让他把商户的人员接走。还有……”
议事堂外涌来了几十个叛变庄民,为首的老者跪下哭诉,“刘当家,小老儿知道错了,请看在往日情分上,庇护我等一二。小老儿的大儿子和一个孙女已经被官军害了,小老儿不想断子绝孙呐。”
刘盛感觉头大,看向庄主亲卫和哥老营士兵。他却失算了,一个人的目光,如何抵抗近百人的目光?
出于某种考虑,李响选拔亲卫的时候,优先挑选与庄内人家牵扯不大的年轻人,或者直接从新流民中挑选。哥老营留在庄内的一个牌,倒有不少士兵和前来求救的叛变庄民相识,顿时窃窃私语,战心不稳。
刘盛正纠结时,张展郡出现在议事堂门口,递过来一张纸条。
左右的庄主亲卫识趣地扭转身体,刘盛打开纸条。虽然不怎么识字,但几个简体汉文,刘盛还是对付得了的。纸条上只写着十二个字:庄主未醒,死守议事堂与河岸。
纸条最后是李梦空、张万里、赵伯,还有刘素素的名字和印信!
庄主已经苏醒,为何纸上写着庄主没醒?
刘盛心里打鼓间,发现面前的张展郡眼神闪烁,心里咯噔一下,感觉冬日又严寒了几分,小河南岸的火场也带不来太多温暖。连素素都不想救七户刘家一把,他刘盛又能如何?
官军和官差既已开始打砸抢烧,便再也没有战力,议事堂很安全。刘盛一句话没说,带着和七户刘家有些交情的年轻人离开,把防守的任务交给剩下的庄主亲卫和哥老营士兵。
跪在地上哀求的老人家眼见此景,哪里不明白刘盛的意思?老人家痛悔投附刘夏都,却没有说更多,带着哭哭啼啼的几十人,找坚固的宅院死守去了。
老人家刚走,七户刘家便带着百十号人,乌泱泱地来到议事堂前。
刘家这拨人里,为首的是刘夏都表弟,只听这位身形干瘦的士子模样年轻人大声道:“叫李响出来。我们刘家答应他的条件,只取一半的明月庄,赶紧让他把官军撵走,夺回我们刘家人的财产,保护我们的安全。”
议事堂前,一片静默。
空气里只有木头燃烧的噼啪声、庄主亲卫和哥老营士兵的呼吸声,以及七户刘家妇孺的啜泣声。
见没人理会自己,刘家的那位年轻人大喊大叫,“庄主之位,还有整个明月庄都是俺们刘家的,他李响窃占多年,凭什么不还?我们只不过是闹分家罢了,如今遭难,你们竟然见死不救?!”
“刘素素,你出来啊。我知道你在里面,都是刘家人,你竟然帮着李响对付自家人。你小小女子,对自己的亲人见死不救,哪里来的狠毒心肠?!”
“刘盛,你是我伯父呢,为何如此狠心……呃!”
一把斧刺、一根短矛和一柄单刀同时刺中那位刘姓年轻人。那位年轻人捂着肚子,似是不敢相信,终于还是缓缓倒下了。
刘姓年轻人的母亲冲上来,拿着棍子乱打,不知被谁的骨朵击中腰腹。那位妇人爬到将死的儿子身旁,口中淌血,“你们杀了我儿子,你们这帮贱民竟敢杀我儿子!”
“明月庄的一切,就该全部是刘家的,你们这些贱民居然敢反抗?!天理不存,大周律法何在,为何不惩治明月庄的贱民……”
陷入疯癫的这对母子死去后,一位庄主亲卫受不了了,“都是你们刘家的,凭什么?!只凭大统制当过寨主,明月庄就是你们几户的?!”
“老子全家自从来到明月庄,不要命地干活,省吃俭用,才刚刚在一家石灰窑里有了份子。”这位庄主亲卫眼泪直流,大吼道:“尔等家里没有一个举人,居然敢自称高贵?尔等勾结外敌,抢夺明月庄不成,如今被官军劫掠,还想着占便宜,哪有这么好的事!”
冷风乍起。
一个哥老营士兵也忍不住了,“兄弟们,睁开眼睛看看。得亏咱们把官军打败,不然官军、官差和七户刘家攻下整个明月庄,受到劫掠欺负的,就是咱们的父母姊妹啊!”
“没错,真要让七户刘家得势,咱们都没好下场。”另一名哥老营士兵也高喊。
“把这些人赶走,谁知道他们里面有没有官军的奸细!”
“没错,赶得远远的。他们既然投靠了大户和官府,就不能再管他们。没准哪天庄里再有麻烦,咱们还会被他们卖了。”
庄主亲卫和哥老营士兵自觉排成人墙,手执兵器一步步逼过去。
又死了两个老弱,七户刘家才哭喊着跑远。官军倒也不再为难他们,毕竟财货也抢了,姑娘也在玩着,总要给黄成两家留点脸面。
林光远的尸体还倒在冰凉的地上,不知被多少人踩踏过。他的妻女没能拿到刘夏都的赔偿,正在被官军玩弄……
除了少数几个砖石小院还有叛变庄民抵抗官军外,整个小河南岸的小半明月庄已落入官军官差之手。机灵的官军和官差四处搜罗鸡公车、两轮推车,准备把抢来的东西运走。偶尔有妇女和少女的惨叫声传来,却是长久没见荤腥的官军还没尽兴。
“七户刘家的好东西真不少,那个死老头,居然到死也把着地窖的门,憨货!”一个官军老油子感叹道。
勋阳总捕头和十堰州两个营指挥站在一座小院的屋顶上,目睹了七户刘家被议事堂的百十号人驱逐的全过程。
勋阳总捕头感叹道:“真不知七户刘家怎么想的。他们要卖掉大多数的庄民,求自家富贵。如今事败,居然还有脸过去寻求庇护。啧啧,长见识了。”
实际掌管近千官军的那位营指挥道:“听说明月庄首重规矩。估计是七户刘家仗着是刘成栋的亲族,日子过得太舒坦,总以为哪里都像明月庄一样吧?”
营指挥左右瞄了瞄,压低声音,“七户刘家真是有钱,从他们家里搜到的东西,顶上所有收成的四成。咱们要上报手下的厮杀汉全部死于庄民骚乱,除了上下打点,还要抚恤那些厮杀汉的家眷。如今不仅够用,还剩不少……”
刘婷婷的身体在小河冰水中重回光洁。
天光大亮,少女的身子顺着河水,在几百名守兵的注视下飘远。
大嗓门儿除去头盔,披头散发地跪在小河边。与大嗓门儿相熟的牌子头、什长之流,也不知如何安慰,只好拍拍他的肩膀,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某一刻,似是从肚子里呼出一口气,大嗓门儿转身,跪在刚才射杀刘婷婷的八十三名直弓手面前,声音似磨刀石,“谢过了。”
不时有叛变庄民跑到小河南岸。或是哭诉恳求,或是哀求旧日相识,或是破口大骂,想让守兵庇护他们。
诸如“悔不当初,还请看在往日情面上……”、“宽家兄弟,你便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等也是庄民,为何见死不救……”之类的说辞,没有让数百守兵动摇。
小娃娃的哭嚎倒是换来了木筏。叛变庄民什么都顾不得,死命朝上挤,木筏上的庄民死命地往下推人。襁褓中的婴儿被推搡到河里,很快没了声息。
年轻的母亲投了河。
在数百名守兵惊恐的眼神中,叛变庄民渡河到达北岸。他们开始要求更多,食物、衣物、屋子……最好是守兵现在便过去,把他们的家产夺回来,有两人开始琢磨,如何才能让公中赔偿自家的损失。
大牛嘴唇哆嗦着,看着刚刚渡河的叛变庄民,如同看到了怪物。
直弓手阵列后面,张清平和杨营东察觉气氛有异,正要亲自过来查看。
大嗓门儿戴上头盔,以单刀劈开空气,“直弓手准备,搭箭!”
“松!”
刚刚渡河的叛变庄民,男女老弱都有,全部被钉死在岸边,此后再无叛变庄民渡河。
有些病,会传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