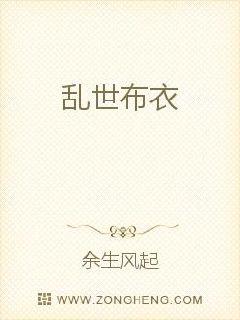马家后宅,商议大事的族屋,窃窃私语声低了下去,并随着马家太爷的叹气声,消弭干净。
场中一片安静,几个年轻的马家后辈咽口唾沫。有十几人出汗不止,不知是炭炉烧得太热,还是身上穿得太多,或者是家主的目光太有压迫力。
接近六十人坐着,都不敢说话,石炭燃烧的声音弥漫在场中。
马家家主,马家太爷终于发话了,小半的马家人松了口气。
“把那几个小辈带上来。”马家太爷发话,双拳平放膝上,坐如铜钟,目似铜铃。
桑老太君和几个族老在后屋说话。
老太君情商很高,虽然她留下也没人敢说什么,但老太君照顾儿子的面子,拉着几个族老退出了大屋。
五位屁股稀烂的马家后辈,被放到木板上抬了进来。
呻吟声传来,座位上的马家人,有的神色戚戚,有的幸灾乐祸,还有的不明觉厉。
“祖训!”马家太爷大声说道。
坐着的马家人挺直腰板,低头听训,没人敢在这时候捣乱。门口处哭泣的几个马家后辈,急忙堵上嘴巴,不敢亵渎祖先。
马家太爷的堂弟负责家法。他走到供桌前,上了炷香,才拿起黑黄的祖训,读起将近两百年前写下的文字。
抑扬顿挫、字字可辨的声音响起,在古老的房屋内,似有净化心灵的力量。
趴在木板上的马家后辈,眼中蓄满泪水,觉得屁股也不是很疼。座位上的马家人,似乎感受到马家先祖征战沙场、提点后辈的奋力拼搏、良苦用心,他们暂时忘了族中的蝇营狗苟,只把自己当成马家一员。
声音结束,场中落针可闻。
马家太爷起身,动作惊醒了陷入迷思的几个马家人,他用粗糙宽大的手掌,轻轻拍着旁边的太师椅,目视墙上历代先祖的画像,“这把椅子,坐着很难受,面上有几根木刺,椅背上还有铁刺。”
靠近中央的马家人伸长脖子,果然看到椅子上面的刺,椅背上的铁刺更是触目惊心。
马家太爷苦笑一声,“老子刚当上家主那会儿,总想换把椅子,谁知道椅子下面的砖石是活的。里面有一块玉牌,上面只刻着两个字:勿动!”
有几位马家人差点惊呼出声。这样的秘闻,之前只有家主和几位族老知道。脑子活泛的马家人开始想:家祖留下这么一把折磨人的椅子,又不让动,到底是什么用意?
马家太爷没有停顿太久,继续说道:“老子是个粗人,年轻的时候上过战场,想不明白家祖的用意。但既然家主不让动,那就不动吧。”
“你们知道,这把椅子的来历吗?”马家太爷忽然转身,瞧着在座的马家人,直到所有人凝神危坐,才继续道:“立国之后,很多将门倒下了,终于有一天,马家遇难。家祖赤袒上身,披着荆条直入皇宫,跪请官家放马家一马。”
“官家数着先祖身上的刀伤、箭伤和枪伤,没数完便流泪说:皇周即大,可容马家安身。”
当年的马家先祖,把荆条刺入肉身,在御街上流血三里才见到皇帝。自那以后的大周历代皇帝,对士大夫阶层抱有一定警惕,大搞平衡之余,不时安抚几家将门。
“家祖在马车内昏迷,八天后才醒过来。”马家太爷虎目含泪,为自家先祖的铁血激愤不已,“醒来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紧闭房门不接外客,然后亲手打造了这把椅子。”
在座的马家人,胸膛热烘烘的,将门武勇好似要在体内复苏。
马家太爷用遍布老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一根铁刺,“老子原以为,家祖的用意是提醒后来的家主,要时刻警惕宰执,毕竟马家狠狠地得罪了文官一把。”
在场的大多数马家人心想:难怪先祖回家后,要闭门谢客,原来是自保啊!但听家主的意思,先祖还有其他的用意?
“当了十几年家主,直到五年前,老子才知道这把椅子的用意。”马家太爷一下坐到了椅子上,看得好些后辈倒抽凉气,那上面都是刺啊!
马家太爷似毫无所觉,“先祖的意思,是要每代的马家家主不得安逸,不能放松警惕,否则稍微懈怠,便有大祸!”
马家太爷指着门口的几个马家后辈,“可能有人觉得老子小题大做,以为这几个去找马如兰的麻烦,没什么大不了。”目光扫过屋内的人,马家太爷分明看到了好些人躲躲闪闪,不敢和自己对视。
“年节将近,各房的人都来了,都是一家人,也没什么家丑不可外扬的。”马家太爷捂着眼,声音冷漠,“如何与王家的人勾连,如何威逼李武两家,都做了哪些小动作,自己说吧。”
末了,马家太爷一字一顿地补充道:“旦有一句不实,除籍。”
马家太爷的声音没有愤怒,没有任何感情。
犯事马家后辈的父兄心堕冰窖,感觉外面的冷风直灌入腹。他们疯狂地给门口趴着的几位使眼色,“既然家主说到这个份上,照着他的脾气就一定做得到,不能犯浑呐,赶紧招了吧。”
四个年轻人和一个中年人,当然知道好歹。全招了很丢人,但不招,会被赶出去!
趴着的几位开始详细地讲出因由,碰到有争议或者记忆不清的地方,还会互相补充。
在座的马家人听着,有时鄙夷,有时也在问自己:碰到一样的事情,自己会如何做呢?
为难马如兰的几个马家后辈,足足说了小半时辰,才把所有的细节说完。
冬日西斜,屋内点起了大蜡,蜡烛特有的油烟气和香气刺激着几十人的鼻尖。
马甲太爷站起身,厚实的双肩和隆起的胳膊,在烛光的照应下极具压迫性,他慢慢说道:“知道老子最痛心的是什么?”
“不是你们几个贪心,不是你们几个联合王家几人对付马家人,不是你们欺负李武两家,而是你们想当老鼠!”
“想让马如兰屈服,你们干了什么?居然往人家店前泼脏水,泼狗血,泼狗屎,雇乞丐过去捣乱,赶走人家的客官。你们是将门子弟!”马家太爷身子摇晃,在座众人一片惊呼。
马家太爷推开堂弟的手,高喝:“大周与士大夫共天下,于宫门唱名者为真好汉。好些书香门第看不上将门,在很多汴京百姓的口中,将门只会飞鹰走马、不学无术、寻衅滋事,可将门不能看不起自己。”
“将门子弟,宁抢不偷!”
“看看你们的德性,哈啊,泼狗屎的主意都能想出来!还以为人家会怕,你们想吓死人啊?!”
“你们几个,跟那种想喝肉汤却没有本事,只好在肉汤里拉屎的老鼠有什么分别?老鼠坏了一锅肉汤,人只能倒掉,老鼠便上去美滋滋地喝着,还以为自己多有本事……”马家太爷朝前走了几步,身体又开始摇晃,脸色涨红,他指着门口的几人,“老天爷。先祖啊,我没教好子孙,他们竟想当老鼠,呃呃呃……”
口中溢出黑血,马家太爷软倒在地。
负责家训家规的堂弟张大嘴巴,朝这里跑来,靠近马家太爷的马家人,在惊呼中伸出双臂。暖屋里的桑老太君手足无措,差点摔倒在地,幸好有几位族老照看。
马如兰回到家中,公婆担忧地问:“马家……家主没有为难你吧?”
马如兰一边拉动风箱,一边笑着说:“家主挺和气的,老是问咱家这些年怎么过的,还把十几年的月例全拿出来,我放到右厢房的便是。”
公婆没什么本事,胆小怕事,唯独在意马朝北,“他不会是想把北儿要回去吧?”
马如兰添上水,放好木盖,“咱们毕竟没有彻底脱离马家,朝北的名字还在家谱里呢。马家太爷添了几个孙子,不会抓着小北不放,但家主说……”
“说啥?”公婆异口同声地问,紧张地不得了。
“说小北必须到族学读书,每月去向他问安最少一次,族里的月例也要领上。就是这些。”
马家后宅,家主大院。
丫鬟和仆人忙成一团,几位名医在厢房争吵疗养的方子。
桑老太君把其他人都赶了出去,连马家主母都不放过,自己守着儿子,不断抹泪。
马家太爷睁开眼睛,想要坐起来,桑老太君让他躺下。
“没事。”马家太爷坐起来,靠着枕头,“吐口血,轻松多了。儿子可是能开两石弓的猛将,没那么娇贵。”
见老母神色郁郁,马家太爷扶着额头,“娘啊,你不会又怪上马如兰一家了吧?咳咳,儿子吐血,又不是我那弟媳妇的错。”
桑老太君年过七十,有时爱发小孩脾气,闻言神色有些不自然,却不说话。
马家太爷叹口气,“娘啊,当年你怕别人夺走儿子的家主之位,把人赶走。这么多年过去了,人都不在了,不能放过?”
桑老太君只好不情不愿地说:“太便宜那家了,那家烧肉馆虽不起眼,但挺赚钱的。要不抢过来,或者咱们多开几家?”
四十五岁的马家太爷哭笑不得,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呐,娘啊,这就是马家红烧肉的秘方,拿去试试,想开几家开几家。”
“我那弟媳从头至尾,就没说几个不孝子一句坏话,还把秘方送了过来。人家只想过小富即安的日子,咱就不能大度点?”
马家主母要带着名医进来了,桑老太君飞快地拿走秘方,藏到袖子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那就,便宜他们家了。”马家太爷闻言,喷出一口水。
马如兰的亡夫,小马家太爷十岁。汴京一只马智勇双全,虽然是旁支,却被当年的很多族老视为家主不二人选。
桑家太君为了保住独子的家主位置,上演了诸般手段,终于把马如兰一家赶了出去,桑家太君当年的生猛可见一斑。
为难马如兰的几个马家后辈,等屁股结痂后,将前往河东军中历练,手上没有十个人头,不可返回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