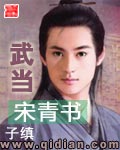封常清进入帐中,看到燕小四和田珍后并不意外,微微点头之后向李嗣业叉手说道:“太尉,监军邢延恩刚刚去找了末将,其言下之意是让我投靠元帅府行军司马李辅国,还送给了末将三百两的猪腰金。值此大战临敌的关头,为了不使这些阉人从中作梗,末将只好暂时应承了下来,但末将深知此事轻重,特来先禀报太尉以表明心迹。”
李嗣业点点头道:“你做的很对,太过刚硬不是最好的选择,能够虚与委蛇更好。你先下去吧,莫要让邢延恩起疑。”
封常清离去后,田珍站在帘幕后面望着他的背影疑心道:“如果他是个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企图两面通吃,等到危急关头时再选择站队,主公我们岂不是很危险。”
李嗣业笑了笑:“用理智来选择的话,骑墙派确实是当前最好的态度,但我在安西军中经营的时日远比封常清漫长,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做出危险选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他转过身来对两人说道:“你们下去之后要时刻留意鱼朝恩和邢延恩两人,时刻提防他们给臧希液和封常清下绊子。”
“喏!”两人齐声叉手之后,缓缓退出了大帐。
李嗣业坐回到案几前,惆怅轻轻地叩击着自己的额头,这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忠心可言,每个人的选择都与目前的境遇有关,他自然要随时保持警惕,给予他们希望的同时,也不可以让他们太过于产生希望。
一旦洛阳之战过后,李亨把他老子从蜀中接回,他对武将的猜疑很快就会浮现在表面,自己当然是首当其冲的被针对者,就连郭子仪李光弼这些人,也无法在这样的信任危机中脱身。
此时夜色正浓,万籁俱寂,天边偶尔响起狼嚎声。他正准备掩盖了衾被入睡,卫士突然在帐外说道:“主公,有人求见,他自称是从蜀中来的。”
李嗣业精神一振,双手撑着从地铺上坐起来,立刻回应道:“请客人进来。”
一人掀开帘幕进入帐中,瞧打扮是个穿着蓑衣的渔夫,头上戴着斗笠看不清面目,李嗣业颦起眉头疑心地问道:“阁下深夜打鱼迷了路吗?为何会深夜跑到我这中军大帐中来?”
来人将自己头上的斗笠摘下来扔在了地上,露出一张线条坚硬如石刻般的脸,左眼上的伤疤依然明显。
“张小敬?”李嗣业吃了一惊:“你从蜀中来?”
张小敬缄默地点了点头,转身对帐外说道:“韦公子,可以进来了。”
掀开帘幕进门的是一个穿着襕袍的书生,只是眼圈色有些重,一看就是位经常熬夜伤神的兄弟。
张小敬这才对李嗣业叉手道:“我是从蜀中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麾下而来,特地前来投奔李大夫。只是陈玄礼本来不肯放人,但后来同意了,交换条件就是我带这位韦应物公子前来见你。”
李嗣业高兴地说道:“你能来我就很高兴,我身边正好缺少一个参军。”
张小敬却直接单膝跪地拒绝道:“我来投奔大夫,不是为了官位,而是为了能够在战场上亲手斩杀叛逆。请求大夫能让我到安西军中,我可以做一个跳荡兵,也可以做一个弩手,但千万别让我当官。”
李嗣业也晓得此人的性子,心平气和地说道:“俗话说人尽其才,你昔日做过参军,做过不良帅,也做过龙武军的中侯,就算是平级调动,做个校尉并不过分。今夜暂且歇下,明日我差人送你到安西行营节度使封常清那里去,现在暂且休息下吧。”
张小敬没有再坚持自己的要求,只叉手说道:“多谢李大夫。”
他立刻吩咐外面的亲卫,让他给张小敬安顿一个可歇息的军帐。张小敬站起来,又朝李嗣业行了一礼,转身跟随亲卫而去。这么多年不见,两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了很多,造成这种疏远的更是因为两人身份上差距的变幻。张小敬身上的游侠气质更多一些,他对官阶地位这些东西也是随缘态度,不然天宝三载上元夜的那一场拼命,早就该换来飞黄腾达了。
直至张小敬出门后,这位韦应物公子始终安静地侧立在一旁,没有额外的表情。直到李嗣业主动向他问起:“公子从蜀中来?可是来送信的?”
“卑职从十五岁起便是太上皇的侍卫,如今太上皇恐有不虞之变,特派我来联络大夫。”
李嗣业穿着中单从毡席上站起来,来回踱步说道:“人生本来就多变难测,就算天子也不例外,你所说的不虞之变,其实早已经发生,自从上皇从长安临幸蜀中之后,天下都处在危难之中,何况上皇乎。如今世事迁移,上皇又有何能为?“
韦应物将双手负于身后,一副传统说客的从容淡定架势,侃侃而谈道:“上皇脱逃长安,虽为世人诟病,但他做了四十年的太平天子,也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开元盛世。他执政多年,其经验见地岂不高出如今的陛下数倍。大夫为人正直赤诚,可曾记得上皇旧日恩情,他对你善加任用,才能有今日大夫麾下的三镇十万士卒南下征战。”
“而且上皇所料不错的话,当今天子对大夫当是颇为忌惮,他能容您一时,安能容您一世,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古人皆知的道理。况且上皇在位之时,已经封你为郡王,新君又能拿什么来示恩与你,顶多是一个只有虚名的三公,仅此而已。而上皇对你何等恩厚,昔日加封你为西凉郡王,又在长安城中修建了豪奢的王府,就算如今他已避居西川,但对你们这些武将的信任,难道是如今的陛下可比?”
李嗣业回过头来突然笑了:“安禄山造反是一个分水岭,从那一刻开始,无论是太上皇,还是皇帝,他们的心态都已经变了,已不可用昨日来等量。太上皇昔日对高仙芝也是相当恩厚,却听信一个阉宦小人之言,把他问斩在潼关城头上。”
“不,终究是不一样的。”韦应物声音有些激动地说道:“今日的皇帝与今日的太上皇也决然不同,我觉得李大夫你仍然不能面带现实。”
李嗣业负手道:“好,既然你要谈现实,我就与你谈一点现实的,你觉得太上皇能够活的过皇帝吗?”
韦应物的脸上浮现出怒色,却沉默不语。不料李嗣业竟然是自问自答:“能活得过。”
他继续说道:“但如果想得再长远一点,太上皇和皇帝百年之后,会选择谁来继承大唐的摊子,那时候诸王都已经年暮,第三代已经脱颖而出,谁是第三代中的佼佼者?昔日在兴庆宫中时,上皇最宠爱的孙子是谁?是永王的儿子?还是寿王的儿子?都不是。他也许对自己的儿子心怀怨恨耿耿于怀,但隔辈亲让他对皇长孙万分喜爱。两代帝王会选择同一个继承人,他们之间的裂痕,对于我们这些武将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韦应物满脸愕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李嗣业要说的话还没完:“自古疏不间亲,主动参与皇家内部斗争的人,大多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远的譬如长孙无忌,来俊臣,近的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况且太上皇和陛下无论谁占上风,承接帝位的必然是楚王李豫,对于一个在他父亲和祖父中间左右摇摆,反复横跳的人,他将来成为皇帝后会怎么做?难道还能再容他横跳吗?”
韦应物听完这番话后,深深地凝视地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便转身往帐外走去,李嗣业在瞬间权衡之后,突然对他的背影说道:“皇帝马上就要派人到蜀中接太上皇回长安,如果太上皇能够以抱病为由逗留蜀中,对他自己对天下都有好处。但若入了长安,就等于入了囚笼。”
韦应物没有回头,说道:“太上皇十分思念长安,你希望他能够逗留多久?”
“如果能等到平叛结束,最好。”
“这对太上皇有何助益?介时皇帝势力固若金汤,回长安岂不是更如入囚笼,这才是太上皇最关心的。”
李嗣业遥对蜀中方向叉手道:“太上皇若能够等到平叛结束回长安,臣下自有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