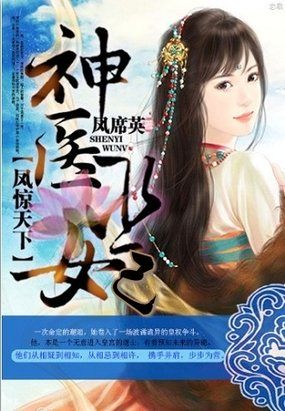“公爷,采访新兵营的记者来交稿了。”黄杰明从办公室外头进来通报。
“那就请几位先生进来吧。”沐忠亮放下手中的毛笔,等梁梿他们三个进来,掏出一盒卷好的黔烟,一人发了一根。
报社在沐忠亮的传染下,几乎个个都是烟枪,谁叫这帮人天天要苦熬赶稿,久而久之就染上了这种恶习。
把桌上差不多砖头大的火绒盒点着,几个人轮流凑上去就着点着,深吸两口,几个形容枯槁的文人看起来才精神了一些。
“行了,你们谁先来?”
不知不觉,几人的目光就聚集到梁梿的身上,谁叫他的文名最响呢?毕竟这个年代,学问好的人都跑去当官了,来报社应聘的人一般都是一些落魄秀才之类的,好不容易有几个成了名而又不愿当官的,待了没几天,受不了沐忠亮对他们的文章指手画脚,都辞职不干了。
对此沐忠亮也是礼送他们,还和颜悦色地让他们到了社会上有空也可以投稿,还弄了个特约专栏给他们,润笔费从优,大改他们在职时的苛刻模样。
是以这些人都很开心地走了,到最后留下来的,成为首任社长可能性最高的人物就是梁梿。自然而然,头一个挨喷的当然只能是他。
“大人,先看我的吧。”梁梿把手里一沓稿交给沐忠亮。
“很好,有勇气,那我就最后再看你的。”见他一副坦然的样子,沐忠亮反倒来了点兴趣,偏偏不按牌理出牌。
把稿件都接过来略略扫了两眼,心里暗自点头。
这帮人总算改掉拽文的毛病了,刚开始的时候总是之乎者也一大堆,社会娱乐版的还好,毕竟这年头通俗白话小说已经不少,但不知道为什么一正儿八经论政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要掉书袋。
接下来抽出第一篇,只看了个开头,他就揉巴揉巴把第一份稿子扔进了纸篓。
“你的论点在哪里?这是报纸,大哥!有几个人会把报纸一字不漏的看完的?说了多少次,头三行没看到论点,就算你写出一朵花来在我这都通不过!”
得,头一个阵亡了。
下一个。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总算开始往下边看,但最后他还是摇摇头,眼皮也不抬,“中规中矩吧,从练兵论述到战时的战斗力,立意太平常,发到塘报去给官兵们看看还行。”
虽然没挨骂,但这无论如何也不算什么好评价。
总算轮到梁梿了,沐忠亮看到一半,眼中就为之一亮,“这个不错,从新入伍士兵的角度阐述入伍的动机,到宣扬保家卫国的情怀。”
“你们要记住,报纸是给百姓们看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给百姓看我们想让他们看的部分,比如说器圃这里写的训练艰苦,但他突出的是艰苦之后的收获,再举例上回曹圣战场立功授奖的事例,让人们认为训练刻苦就能提拔受奖。”
“这……这不是骗人吗?”一名记者不禁反驳道。
“什么叫骗人,我们只是突出了我们需要的部分而已,我也没说人人都能和曹圣一样啊?训练刻苦总没错吧?就算不能升迁,总能更容易活下来不是吗?”
“我再打个比方,等到明年开战,你们少不得要写到战场牺牲,但你们总不能写死了多少人,好惨吧?突出的永远只能是牺牲的精神,以及他们的牺牲为朝廷百姓的贡献,以及极尽哀荣,无上荣誉,而不是牺牲本身。”
“要记住,你们是大明官报,是朝廷的喉舌,要时刻谨记自己的屁股坐在哪头!”
听了沐忠亮的教诲,记者中,稍年长的陷入了深思,年轻些的却面带愤懑。沐忠亮也不以为意,自古以来,哪一家媒体都号称中立,而实际上呢?他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作为官报,首要的更是立场的正确性,其次才是所谓的质量。
一时兴起点评了一番,他又点上一支烟开始继续往下看最后的评论总结。
谁知刚刚还夸赞了梁梿的文章一番,现在他的脸色又回复到木然,眉梢不为人知地抖动着,似乎心理正在激烈的变化。
梁梿此刻也很紧张,密切地关注着领导的神色,他是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的,合不合领导的心意,乃至定下社长的位置,就看这么一回了。
“自甲申天变以来,我骄傲的炎黄之胄不存在了!那些鞑子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肆意践踏我等的尊严,一个曾经万邦来朝,四夷宾服的民族的尊严!
“而他们上溯不到五代,都还在极北苦寒之地茹毛饮血,再往上就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不得不盗用完颜之名,妄称金人。甚至到了今日,他们的妻子还是兄终弟及,甚至还堂而皇之地坐上伪太皇太后之位,对我等礼仪之邦妄称母仪天下。即便做奴隶,你愿意受此等无宗无祖,无廉无耻之人的奴役?!”
“我不知道你将如何回答,但我会说,毋宁死!”
“你们或许要说:梁先生,我只需要一块土地,一个营生,要吃饭。没错,生命诚可贵。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世上仍有一样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就是尊严!”
“一日屠杀广州,新会吃人的汉奸不被车裂,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一日旗人汉奸在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上肆意跑马圈地、作威作福,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一日其他洋夷,在提及我们这个国家时,想到了不是礼仪服章美轮美奂的华夏,而是一句轻蔑地‘鞑靼’,然后嘲笑我们脑后的猪尾巴,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
“所幸,我们还有这些青年。他们自愿离开家乡,为我们的尊严而战,乃至现出宝贵的生命。我们的祖先,数千年来几度浮沉,最终重新崛起为泱泱大国,靠的是明君能臣吗?不,靠的就是这些青年,他们的祖先从未屈服!而现在,他们的血液流淌在后人的肌体中,鞑子尽可以来试试这千年的热血是否凉透,然在此之前,他们要先试试我们的刺刀!”
沐忠亮看完这篇文章,百感交集。他就知道,照这么发展下去,这种东西总会自己蹦出来的,它是良药,但历史也证明了,它可能有毒。
深深看了梁梿一眼。
看上去就是个白面书生,也就眼角微微有些风霜之色,不过就是三十许人的样子,很平常。
但也很不平常。
“你这些话,是怎么想到的?”
“往常我就有研读过梨洲公和亭林公的大作,前段日子我去上了短训班,拜读了大人的《天演论》,始有此想,大人以为如何?”
“嗯,有没有想过老百姓能不能理解你说的话呢?”沐忠亮没有正面回答。
“学生窃以为如此说,远比口口声声大义正统来得有效,按大人的理论,最好的动员就是建立同理。我通过叙述共同的祖宗获得认同代入,再丑化建奴激起厌恶,最后揭起部分伤疤建立同仇感,最后建立同仇敌忾之心。”
叙述完,他便不做声,静静等待沐忠亮的最后评判。
天才,真是天才。
切不可小看古人啊!自己只是稍加点拨一下,他马上就弄出了一篇煽动性如此之强的东西出来。
会不会太极端呢?而且文中这种论调总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但说实话,在现在民众的心中,民族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这时候哪怕揠苗助长也要千方百计加快启蒙的进程。这时候考虑失控的问题怕是太早了吧?都快被鞑子干掉了,还有什么好顾虑的。
罢了,管他治头痛还是治脚痛,反正现在全身都是病,总先治了一处再说。
“嗯,就发这篇吧,我明天便没空来了,以后就由你来统筹,出刊前把样本发审批就好。”
拍拍梁梿的肩膀,“好好做!”
丢下一句话,沐忠亮大步流星离开了报社。
半晌,其他几位记者才回过神来。
“恭喜器圃兄,这社长之位终究还是要以兄之才学才能胜任。”
梁梿终于松了口气,他赌对了!
赌沐忠亮办报的真实想法,赌这舆论的深层次作用。
民心如水,但水凝冰亦可成利剑!
“新年好!”在平南王府改造的行宫偏殿内,一群大臣身穿朝服,正亲热地互相致贺。
眨眼间,已至公元1664,永历十八年,又是一年新年至,不知不觉,就到了沐忠亮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三个年头了。
而这个新年,却还是头一次在自家的正经住处过的头一个年。
第一年,是在海上过的,第二年,琼州不过是临时府邸,牌匾他都懒得挂一个。
在去年朝廷将广州定为行在之后,沐忠亮才真正置办了一个宅子,趁着年前赶紧搬了进来。
而朝廷从最初仅剩十几个大臣,到今天也有了近万人的庞大公务员队伍,从中枢,到最基层的县乡,都遍布了他们的身影。
而在年前,明军的总兵力也到达了七八万人,这么说来,光朝廷就供养了近十万人,而且听张万祺透露,似乎还有不少盈余。
这不,新春头一天内阁会议,闻到钱腥味的各路大佬都来打这笔盈余的主意了。
热情地道贺完,各部、三法司、参谋院、军政院、陆军、海军,以及沐忠亮这位首辅和布政使张万祺都各自入座。
可以说大明官场的最顶级人物都囊括在这里了。
如今尚书只有三名,分别是工部马吉翔,以及吏部尚书邓士廉,吏部尚书则是新晋升的原勃泥知府邬昌琦。
这三位都是前奸党,现在的沐党。而原刑部尚书马雄飞由于实在才干不足,远不及他哥,经过沟通已辞了官,专心当起企业家来。他的位置正好由火箭晋升的刑部侍郎海起晏代理。
剩下的兵、户部,也是由新晋官员中提拔的侍郎代理,仍由沐忠亮亲自掌总,部分交给张万祺日常代理。
除刑部外两个法司则是左都御史任国玺,以及一直非暴力不合作的大理寺卿邓居诏。任国玺还好,反正他的职责也是要找官员的毛病,只要不是构陷,多盯着点没坏处。
而大理寺无非就是断案而已,只要他好好干本职工作,按着法条断案就行,就算天天吊着脸沐忠亮也无所谓。
武官方面,参谋院入座的是定下断粮道以奇袭广州之计的参谋长邓凯。
坐在参谋院下手一位的就是他的平行机构军政院总政委黄士昌。
最后是陆、海军的两位大佬,苏诚和林福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