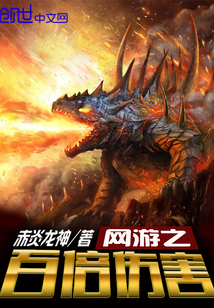施染慢慢的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从气质到神态都带着冷漠,“不愿。”
她手里的玉如意一下子落在了地上,摔在石台上,从中间应声而断。
所有人都在看着这里,亦将施染冷漠残忍的话听得清清楚楚的。她耳边传来“嗡嗡”的议论声,以及兄长连朔掀案而起的声音。
连枝儿眼中很酸,但泪依旧没有落下来,为什么?他为何要反悔?为何不要她了,明明是他答应过的!
“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我是拿你取乐呢。”她的脸上满是笑,可眼底分明含着泪,语调却是那样的欢快,“你这样无死气沉沉的人,难道以后想要本郡主憋闷死了吗?!”
此时连朔已经怒气冲冲的走了过来,眼底充血,只恨不得将施染给一拳打死了。
他见自己的妹妹居然这样的说,却是满脸的狐疑,“枝儿你当真是这样想的,若是他让你伤了心,哥哥这就往他的身上戳几个透明的窟窿给你赔罪。”
连枝儿的目光落在远处的父王身上,他虽没有说话,但手里的珐琅金杯已被他捏扁。她知道,父王这一发怒,便是要血流成河的。
她俯身捡起地上已经断裂的玉如意,裂痕处的锋锐扎进她的肌肤里,竟是针扎一样的疼。
“上京的这些公子哥们都不过是些绣花枕头,有什么好的。反倒不如咱们北凉的男儿勇猛威武。”她的目光落在施染的脸上,再欢快的语调也掩盖不住心底的绝望,“我才不嫁给施染呢!”
************
原本一场给郡主选夫的闹剧却草草的收场了,连枝儿当夜便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她浑身滚烫,更是睡得人事不省,只是偶尔迷迷糊糊的醒过来,一滴滴的泪顺着眼角往下滑,嗓子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好似在哭。
北凉王夫妇守在她的身边,片刻也不敢离开。北凉王妃更是哭的泪天泪地的,只指责北凉王道,“都是你们胡闹,好端端的让她选什么夫婿,如今折腾出病来了,可如何是好?”
见女儿如此,北凉王也是十分的懊恼。
而就在这时,连枝儿慢慢的睁开眸子。
两人忙围了上去,只忙问她想要什么,或吃些什么。连枝儿转了转眼睛,勉强有了几分的精神,良久才喃喃道,“父王,咱们回北凉罢。”
北凉王伸手抚摸着她滚烫的脸颊,一个鲜艳明媚的女子竟成如今病怏怏的模样,或许不该她接来上京,“好,阿爹带你回家去。”
金銮殿内,小皇帝在龙椅上规规矩矩的坐着,一双漆黑的眼睛瞧着殿下的大臣,时而露出惶恐,时而露出好奇的神色。
最后他的目光不断的在施染和阮禄身上转,果然是有爱美之心了,这满屋子的朝臣里面,最出挑的便是这两位了,好似连他也分不出伯仲。
此时太后却坐在小皇帝身边的,虽用纱幔挡着,却见她强撑着柔弱的身子,来支撑今日的局面。
“众位爱卿,今日北凉王上书要请辞回北凉。”
只听得这话,朝堂下的那些大臣们一下子炸开了锅,若非在金銮殿内,只怕要拍手称庆,痛哭流涕了。
北凉那些屯于阶陛的虎狼们终究要走了,再也不必战战兢兢的,过每日刀尖上舔血的日子了。
“可是北凉王要咱们拿出一千万两的白银做军饷。”太后长长的叹了口气,“这该如何是好?”
一千万两,这北凉王可真会狮子大开口,那些大臣们脸上的欢喜尚未退去,便又开始满脸愁容,唉声长叹起来。
这成山成堆的银子便是在太平盛世也很难拿的出,况刚历经藩王之乱,北凉人又在皇宫国库里经常搜刮,如何能拿的出这样多的银子?!
而就在这时,却见阮禄从人群里走了出来,单膝跪地,“还请太后娘娘下懿旨,允许北凉人在京中劫掠商贾富庶之家。”
只闻得此言,众人却是瞠目结舌,一时间朝堂上竟如市井一般,闹得不可开交。
而施染却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一副淡然于世的模样。
终于太后带着几分孱弱的声音从帐幔后面传来,“就依此计。”
朝臣虽有反对者,但还是以大局为重,北凉的兵马不走,朝堂便一刻也不得安宁了。
众大臣退朝之后,太后唯独留下了自己的几个心腹大臣商议此事。
森森的宫闱中,静的连笼中鸟儿拍腾翅膀的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金碧辉煌中,压抑的让人几乎窒息。
后宫一处偏静的小院里,皇后与长公主坐在殿内的两把椅子上,而在屋中站着的却正是施家父子,以及言侯父子。
几个人神色凝重的商议了几个时辰了,终于太后揉着酸痛的肩膀,慢慢的站起身来。
“明日若不成事,那北凉王定会要反了,咱们是拿着江山社稷去做赌注啊。”
施太傅道,“绝不能放北凉王父子回北凉,况又带走这些金银,无异于放虎归山,以后中原便如同他家的花园子,岂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言侯亦冷笑道,“明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受了北凉人这些时日的窝囊气,是该让他们付出代价了。”
终于阮禄冷声道,“即是如此,何不赶尽杀绝,为何要放那北凉的王妃和郡主离开?”
“北凉十万铁骑岂能说便杀尽的,况且北凉王进京原本是护驾的,咱们终究得念着他的功劳,放那些败军一条生路。那些北凉人万一走投无路在京中大开杀戒,岂不是要血流成河了?”施太傅淡淡的道,“放那些妇幼离开罢。”
殿中,阮禄的目光一下子变得冷然起来,只吹垂下眼帘来,目光却落在施染腰间的那块玉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