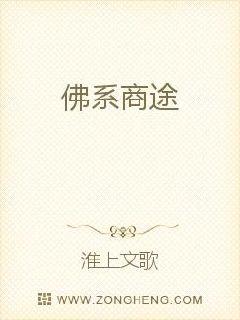东晋隆安二年的仲夏,我们终于回到了西域于阗国大湖之滨的清风泽家园。┏┛
整个行程历时五个多月,沿着当年西行的旧路风雨无阻、昼夜兼程。
连途中几位交好的故人,也没有再去拜访,以免耽搁时日。
包括赫拉特城的火祆教女护法、我的波斯国红颜黛米尔,梵衍那国的弥陀罗法师和高附城的撒马尔罕.琅东表叔。
再次遇见他们时,琅东表叔的全家已迁到了贵霜国的新都富楼沙,法师已然圆寂,倾城倾国的黛米尔公主也早已嫁作他人妇。
岁月不老,人生苦短啊!
从相识到相逢,尽然从青丝走到了白发,世间的万般情愁,到头来皆是空无。
客栈角楼上我当年亲手挂上去的青铜风铃还在叮咚作响,清风泽岸边的水磨风车依然咕咚咕咚的转悠个不停。
但门前的胡杨林里,往日过路客商熙来攘往驼马已经不见了踪影,书院里也没有了学童的诵读之声。
五年前那个充满喜庆生机的家园,好像已经不复存在了。
或许是这几年来经历的事情太多,所有的旧景物在我的眼里都平添了一层沧桑的颜色。
此所谓境由情生是也!
外在的一切还是旧模样,但归来之人已不再是当初的青葱少年郎。
“哥!咱家怎这么冷清啊?阿妈她们不会出啥事了吧?”
古兰朵有点恐惧的问道,为了今日的“衣锦还乡”,她特地换上了当年离家时阿妈亲手为她缝制的越锦夏裙。
“小姐,这就叫近乡情怯!我们每次随老爷行商归来时的性情都是这样的!哈哈!”兰顿大哥开心的笑道。
而沙米汉则是满脸的肃穆愁容,他如今最担心自己的夫人英兰里尔是否还在清风泽。
这么多年没归家,于阗王城中那个温馨的院落也许已经人去楼空了吧。
我们一行急促的马蹄声早已传进了客栈,几位出来迎客的伙计看到是少主人和小姐归来,都忙不迭的跑进后院报喜去了。
顷刻间,几十位家人伙计簇拥着一位白发老妪迎出了门来。
“我的朵儿!金城啊!苍天有眼啊!你们可算回来啦!”
老夫人高举着双臂,嚎啕大哭着颤巍巍的向我们迎了过来。
我这才认出,来者尽是我的娘亲,三年多的光阴她尽然老成了这般模样,身为人子,真是不孝啊!
我和朵儿赶紧下马,俯首跪倒在老母的跟前,一声从心底喊出的“阿妈”赛过了千言万语。
“素儿,快喊阿大!”
我的夫人库日娜比往昔清瘦了很多,满脸苦尽甘来的欣喜之色,怀中抱着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娃正在冲着我直乐呵。
“素儿!我有儿子啦?”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离家三载我的小儿已经来到了人间。
俗话说父子连心,这个小娃尽然对我一点也不认生,好像很早就认识我一般。
“是啊,你的儿子!你们走后的那个冬天出生的,呵呵!曾祖给他起了一个女娃家的官名,封素!易封素!”
家母于阗夫人爽朗的笑道,一扫心中阴霾,又恢复了往日那种大度自信的神采,让我们这些归来人倍感温暖。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封素之家,乐同王侯!咱家的商者衣钵有传人啦!哈哈!爷爷他们几时归来?”
我开心的抖着怀中小儿,放眼环视周边的家人伙计,所有的老人差不多都在,只少了爷爷和商队中的那般老少兄弟。
在太史公的《货殖列传》中,封素同于商贾。
给自己的曾孙起了这样一个官名,可见爷爷的一片苦心,他希望我们易氏家族的行商生意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
“夫君,你还不知道吧,我们阿妈都糊涂一年多了,谁都不认得。没想到你和朵儿一回来,就把咱妈的心病全部治好了!阿弥陀佛,感谢大慈大悲的佛祖菩萨,咱家的厄运总算结束啦!”
库日娜接过素儿欣慰的感叹道,似乎有意把爷爷和商队的话题暂时撇开。
母亲此时正紧紧握着兰顿大哥的手不停的嘘寒问暖,而沙米汉已经与他的娇妻英兰里尔和幼女难舍难分的拥在了一起。
“姐夫,怎么没见秦冲啊?”
“还有刘真儿!那个锅盔刘怎么也没有回来?”
一旁的小姨妹库利亚和樱兰姐姐有点遗憾的笑问道,她俩在归来的马队中没有看到自己的意中人,肯定很失落吧。
“此事说来话长,容我将来再慢慢告诉你们!”
所有的伙计和歌舞姬姐姐都如迎接远行的亲人一般争相招呼我们,确实没有时间向俩位佳人解释迦南起义的来龙去脉了。
“朵儿!快把我们的钱袋子取来!”我对正在与众人欢声笑语的古兰朵大声的喊道
已有伙计卸下了马背上的所有行李,朵儿在一大堆皮囊中找出了装有一万枚罗马金币的那个钱袋,哼哧哼哧的拖到了我的跟前。
“各位兄弟姐妹!感谢大伙这些年来对我们清风泽客栈不离不弃,代我照应家中的妻儿老母!金城这边有礼啦!”
我高举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向这些陪伴我们兄弟和古兰朵一起长大的亲人们深深鞠了一躬。
“如今金城在西方发了点小财!呵呵!我来给家人们分点红利!每人十金,见者有份!”
十个金币差不多是一个成年伙计在我家五年的工钱,听罢我的招呼,所有人都忘情的欢呼了起来,给我鞠躬磕头致谢。
“孩儿们都起来吧,我们清风泽已经许久没有这么喜庆啦!这些都是你们应得的!”
家母对于我的散财之举倍加赞许,就算是散尽万金也比不过她的一双儿女平安归来。
“朵儿快快分钱!哥哥姐姐们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杀牛宰羊,张灯结彩!把王城的亲戚们都请过来好好的庆贺庆贺!”
人们欢天喜地的接过还沾有马背余温的罗马金币,千恩万谢的忙活各自的事情去了。
接下来的几日里,前来恭贺的各路亲戚和商家伙伴络绎不绝,送走了一波又是一波。
我也从妻子库日娜和众人的口中,慢慢弄清了西行几年来清风泽家园的种种变故。
东晋隆安元年,也就是去年,爷爷易临风在从建康归来的途中无疾而终,奶奶慕容琼琳也在几个月后驾鹤西去。
我易门商队就此解散,苏德尔苏叔在爷爷的坟前搭了间草庐,为其守墓,替我等儿孙尽人子之孝。
其他的商队老人已经四散开去,回到了各自的家乡不知所终。
与爷爷相伴一生亲如兄弟的卢羽老丈,也在去年冬季因为忧伤过度老病复发而撒手人寰。
他们这代汉人在西域于阗国的奋斗史,也因为二人的离去而走到了尽头。
按照商道惯例,三年在外未归音信全无的商者就视同丧命天涯。
所以今年清明期间,库日娜忍痛自作主张,在爷爷的坟茔旁边,给我们全体西行人员立下了七座衣冠冢。
并从赞摩寺请来高僧,为我们做了一七的招魂法事。
爷爷去世商队解散后,与远在东晋朝的二弟、三弟、外公他们也就彻底断了联系。
加之我和古兰朵的生死未卜,接二连三的打击,令一向坚如磐石的家母于阗夫人一夜白头彻底乱了心智,变成了一位疯疯癫癫的老婆子。
整个家园靠着我妻库日娜的苦苦支撑才熬到了今日,真是难为她了!
三日之后我谢绝所有访客,替代苏德尔苏叔,住进了爷爷坟前的草庐。
东土汉国有为离世的父母大人“丁忧”守墓的乡俗,苏叔一个与我家只有主仆情谊的柔然人尚能如此。
身为易门的长孙,汉家的人伦之礼我又岂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