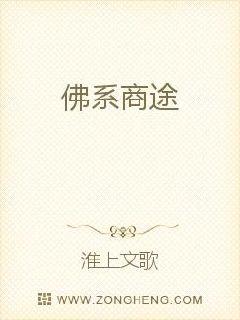古兰朵双手托着下巴,惊恐的圆睁着双眼听苏叔讲述那段血雨腥风的往事。
于我而言,对战厮杀的场景已经在我的眼前展现开来了。
“那时候你们爷爷,还有卢羽卢爷正是血气方刚武功盖世的时候,呵呵!卢爷弯弓搭箭转瞬间就把对方的几位賊首射杀于马上,老爷手执弯刀领着我们这般年轻的伙计一通厮杀,硬是把对方过来的百十个人马干掉了一半,我们却是毫发未伤!哈哈!”
讲起年轻时候的这次经历,苏叔两眼放光的看着爷爷,仿佛又回到了虎狼不惧、神鬼无畏的青壮年代。
“金城你记住了,江湖上行走大多数的时候,都可以用钱财摆平,破财消灾商途常事,切莫因惜财而误伤了伙计们的性命!但也有撒浪山贼这般油盐不进、要财又取命的魔障!既然遇上了也不要惧怕,奋力一搏就是,或可置于死地而后生!要有你在阳关之外手刃苍狼的那股狠劲!呵呵!”
爷爷就如闲谈家常一样,看着我慈祥的笑道。
“哥,你啥时候手刃过苍狼啊!”古兰朵惊讶的看着我叫道,她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哥和秦冲二人联手,干掉了十来头北地饿狼,就在去年东去长安的路上!呵呵,自从那一次之后,你哥哥就算正式入行啦!”
爷爷欣慰的笑道,如果没有那次经历,他如今还真下不了让我执掌清风泽商队的决心。
“朵儿小姐,江湖险恶啊!人要有慈悲之心,但遇见十恶不赦之徒,你的慈悲只会助长坏人的恶行,使自己徒遭厄运!该出手时就要果断出手,决不可有妇人之仁,这也是我们商者的生存之道!”苏叔敦敦教诲道。
“朵儿明白!”古兰朵拱手答道。
夜色已深,在这与世隔绝的山野之中,隐隐传来了几声无名兽类的啸叫之声。
除了几位执勤守夜的伙计还围在篝火周围窃窃私语,其他所有人都紧紧裹着各自的睡袋,在这寒夜中酣睡了过去。
月色如水,穹庐如黛,天与地完全合为一体,我们这世间的生灵仿佛从来就没有到来过,一切皆为空无。
第二日在菩提滩外围的山麓地带休整一日后,商队翻过一座光秃秃的山梁之后,就来到了瓦罕山地。
一眼望去,漫山遍野尽是戈壁石滩,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积雪,看不到半点的生机。
或为无数年冰山雪崩裹挟而下生成,或为经年累月的山体风化所致,和前往长安途中穿越黄龙沙海之后所见的那片戈壁一般无二。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这瓦罕山地身处高寒风口地带,终年朔风肆虐、寒气逼人、呼吸不顺。
阳关之外的戈壁是脱离苦海之后的希望,而这片山地却是苦难行军的开始。
刚刚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走了一两个时辰,我就看到了几具驼马和世人白森森的枯骨随意散布于一片片乱世从中,令人毛骨悚然。
这些枯骨可能都是来自东西方的商贾和僧侣留下的,走到了这里已是强弩之末,只能坐而等死,何其悲哉!
阳春三月的天气,这边连荒漠地带最易存活的骆驼草都看不到一棵,除了石头之外还是石头。
路面高地不平,我们在菩提滩出发前每人都特意备下了一根木棍,此时终于摊上了用途。
“苏叔,这边怎么寸草不生啊!要是在我们于阗国,每年三月胡杨林的新叶都泛绿了!”
我跌跌撞撞的和苏叔并肩而行,驼队、牦牛群和我们的坐骑马队在山间见缝插针的分散开来,两旁连绵起伏的山峰成了天然的屏障。
“少主啊!此处地温常年如冬,三伏天的季节从这儿行走都要穿裘毛外套,草木夏花岂可存活!”
苏叔身披老羊皮裘袄,裹着厚厚的头巾,一条狐皮围领把整个脸全部遮上了,只有一对眼睛露在了外边。
我们正迎着凛冽的西风而行,彻骨的寒冷与冰峰上相比有过之而不及,所有过冬的衣物全部套在身上,都还觉得全身没有半点的热乎气。
“如此恶劣的行程,为何不另寻他路?”我感到疑惑不解。
“从我们西域前去高附城,只有两条道可走,一条是乌孙柔然的大夏古道,另一条就是这瓦罕山地!其他的地方要么是一座接一座的雪山,要么就是我们长上翅膀也飞不过去的千年冰峰,其中的凶险远甚于此处!”
呼啸的西风带着尖啸的哨音,我把耳朵凑在苏叔的嘴边才能听清他的说话。
“少主,忍忍吧!七八天的时间就能穿越这里!与黄龙沙海的酷热相比,我更喜欢这儿!”秦冲牵着马匹跟了上来,大声的嚷嚷道。
他讲得有几分道理,我们这样的商队给养充足,十天八天可以衣食无忧。
冷不可怕,实在熬不过从皮囊中取几块布料裹在身上便是。
烤箱一般的酷热才是最难忍受的,因为你无处可逃。
古兰朵刚进瓦罕山地时,不小心踩入石头缝中伤了脚踝,因此也有了全队唯一的特权,骑在马上上路。
她的坐骑由秦冲、沙米汉、刘真儿三人轮流牵着,小女子坐在马上像个开心的公主一样。
她的雏鹰青鸾可能肉食充足的缘故,见风了长。
几天没注意,满身乌黑硬刺般的羽翅全都长出来了,正在和古兰朵用只有她俩才能明白的方式进行着交流,成了我们单调的行走途中唯一的风景。
在我们进入瓦罕山地的第四日,遇到一位身毒国过来的衣衫褴褛的年轻僧人。
这也是自朅盘陀以来,我们途中遇到的第一位行者。
两匹瘦弱的老马,驮着装有佛学经书的木箱,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多少备用的给养。
真不知道高附之后的这段行程,这位外邦的僧者是如何走过来的。
“阿弥陀佛!大师,你这是要去哪里?是一个人过来的啊?”
全队伙计只有古兰朵一人会身毒国语言,她下马后双手合十膜拜道。
爷爷赶紧招呼全队人马全部暂停下来,虔诚的向僧者行礼。
接过爷爷布施的馕饼、裘袄诸物之后,身毒国僧者诵着佛号还礼道。
“阿弥陀佛,多谢施主的慈悲。我们原来是师徒二人,前去龟兹国的昭怙厘佛寺。师傅刚刚圆寂回归极乐世界,如今我只能一人前往了。”
这位比丘僧人谈及他已经圆寂的师傅,脸上并无悲哀之色,他们出家人早已看淡了现世的生死。
我这才发现,路旁有一处刚刚垒砌的石堆,这位身毒比丘的师傅就静静安息在那儿。
我们来的时候,这位僧人正在念诵超度亡者的经文,如此打扰实为不敬。
爷爷制止了古兰朵的继续提问,让人取出檀香火烛,率所有伙计在高僧的坟前叩拜祭奠,直到年轻比丘的祷告结束。
“法师,从此路赴龟兹国山高路险、了无人烟,途中持钵乞食几无可能。法师不如随我转回高附,从那经大夏古道前去龟兹更为便捷,不知法师意下如何?”
爷爷示意古兰朵翻译道。
“阿弥陀佛,世间的坦途险途皆是冥冥中注定,也是佛祖的旨意。我和师傅自然选择这条前去龟兹弘扬佛法的正途,就断无回头之理!施主的慈悲之心定会结下善缘,阿弥陀佛!”比丘僧人唱着佛号对爷爷深深致谢道。
“老苏,把我们的馕饼、马料多取点过来,这位僧者太固执,他一人一马如何能够穿过这葱岭上的戈壁冰山!”
爷爷回头吩咐苏叔,很是不解的摇头叹道。
佛家的修为讲究度己度人,如眼前的身毒比丘这般,自身的安危尚且难保,又如何去普度教化众生?
但愿大慈大悲的佛祖菩萨,能保佑这位虔诚的传道弟子,让他能平安抵达西域。
和身毒国的苦行僧者分别之后,整个商队都处于一种惋惜、悲伤的氛围之中。
以我们这些凡人的眼光看来,身毒僧者此番前去凶多吉少。
很难想象一个孤单瘦弱的僧侣,孤身一人在我们经过的那片雪山上过夜是何情景。
以身殉佛,也许就是他们这样乞行的僧者毕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我们红尘之中的凡人所无法想象的荣光。
《杂阿含经》卷四有云︰所谓比丘者,非但以乞食,受持在家法,功德过恶俱离,修正行,其心无所畏,是则名比丘。
身毒国僧者正在亲身躬行这样的戒律,令人顿生无限的敬仰。
我暗下决心将来路过龟兹国,一定要去昭怙厘佛寺接受这位法师的教诲,向他布施,皈依他所宣扬的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