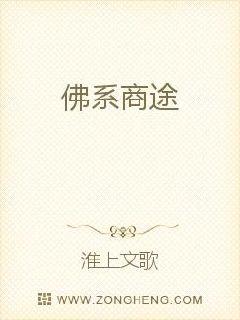几日之后,野马的箭伤痊愈。
大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它们钉上了铜制的马掌,勒好了缰绳辔头。
马蹄铁掌最早由波斯、贵霜诸国的商者传至西域,至今在中原汉地尚未流行。
其主要用途是保护马匹的四蹄,免受路面碎石的擦伤和损害。
西域各国戈壁荒漠连绵千里,不论长途征战或是四海行商,如果没有马掌的保护,任凭大宛乌青这般的汗血宝马,两三日奔驰下来,也会四蹄糜烂肿胀如鼓而不堪驾驭了。
大河以东的汉地祖乡,多为松软的黄泥地面。
加之骡马本身的蹄脚有一层指甲坚硬如铁,无需另外装钉铁掌也是情理之中。
林兄他们常年行商于东晋朝和罗马、波斯之间,对于马掌的形状和功能早已知晓。
所以由林鹤、林青挥锤锻造的铜掌,大小尺寸正好合适。
怎奈这几匹悍马野性未除,何曾受过这般的束缚。
稍微松绑之后,它们就开始发疯一般,肆意踢踏着四周的围栏和脚下的草地。
大伙花费两个多时辰辛苦装钉的铜掌,尽被它们半盏茶的功夫全部踢掉了。
见此情景秦冲暴怒,不由分说抓起缰绳一个鹞子翻身便跳上了马背。
伴随着一声撕裂般的长啸,这匹棕黑色的野马狂躁不羁上下翻腾,想把秦冲摔下马来。
怎奈秦冲这个马痴,竟如黏胶一般贴在了野马的背上。
眼见撕咬腾跃没有效果,围场的栅栏也已打开,这匹野驹便一路狂啸着夺门而去。
快如流星疾如闪电,顺着山脊上的崖畔向着东南奔腾而去,转瞬之间并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
我和锅盔也不再迟疑,分别跨上了各自相中的坐骑。
已有同伴先行一步,跨下的野马也就不再纠缠挣扎,直接奔出了围栏追逐它们的同伴去了。
耳边山风尖啸,侧畔便是万丈绝壁,稍不留神坠下马去,小命可就休也!
“贤弟!秦冲!小心啊!”
“锅盔小心!”
“阿大!阿大!”
身后林兄和小女印加他们的呼喊之声隐隐传来,但我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长到今日,驾驭过的宝马神驹不下十匹,见识过天下列国的野马悍马,但如此性烈的野驹真是第一次遇见。
好在我和秦冲、锅盔三人都是一流的骑手,师从过乌孙国驯化野马为业的绝世高人。
深知驯马之术没有二法,只能信马由缰,任凭野马在草原山野之上肆意狂奔,直至精疲力竭主动归顺才算功成。
没有一腔的血性,驾驭不了这些山野中的精灵。
所以驯马的骑师除了要有一流的骑术,还要有向死而行的心志。
任凭前方刀山火海万丈绝壁,也应如闲庭信步一般。
楚汉项羽和他的乌骓马如此,三国吕布和他的赤兔马也是如此。
此所谓英雄相惜,终成刎颈之交是也!
如此肆意狂奔了约半个多时辰,前方的山脊渐窄眼看就到了尽头,一条两丈多宽深不见底的沟壑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的第一个意识就是赶紧跳下马来保命要紧,野马肯定跨不过去。
就在我稍有迟疑的时候,远远看到秦冲的坐骑已在对面的山梁上了。
而锅盔跨下的野马也如长上了双翅一般,四蹄凌空飞冲过了绝壁。
于是我也就不再犹豫了,彻底放松原本收紧的缰绳,俯身抱紧野马的鬃发,是生是死听天由命也!
山风骤紧身浮于空,伴随着一声明快的轻啸,跨下的乌青野马已经平安落地。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这才感到全身早已汗透,着实被吓得不轻,不禁腾出手来,虔诚合掌连唱了几声佛戒。
稍稍稳定之后,野马又狂躁不安的腾跃翻滚了起来。
不时扭着长脖,张开满是板齿的大嘴回头撕咬我,力图把背上的入侵者掀翻在地。
但我如今已像钉铆一般,死死钉在了马背之上。
使出千钧之力抱住野马的脖子,勒紧缰绳抵御野马的狂暴。
毫不屈服的野驹如同绝望的囚徒一般,不时前蹄凌空打着转转,发出了响彻山野的嘶鸣之声。
辔头勒的太紧之故,已经陷入了野马的下颌之中,殷虹的鲜血顺着缰绳滴滴答答的落入了四周的草地上。
如此威武不能屈者,令我不禁想起了在罗马国为奴的那段日子,不由的心软了下来。
我放开了束马的缰绳,决定不再给这匹狂野的生灵任何约束。
能否驯化成功皆为天意,就看我和它之间的缘分了。
没有了缰绳的束缚,野马再次撒开了四蹄,向着山下的海边荒漠一路狂奔而去。
四野慢慢开阔平坦了起来,乌灰色的大漠戈壁上有零星的绿草和繁花点缀。
左畔是浩淼如烟的蔚蓝沧海,右畔是郁郁苍苍的连绵山峦。
如此天高地阔的所在,正是纵马驰骋的绝好去处。
我和秦冲、锅盔三人,各自相距了一箭之地,任凭野马自由的狂奔。
这些桀骜不驯的家伙虽然还是奔驰如风,但已气喘吁吁汗血淋漓,满含愤怒的锐气已不复当初了。
眼前地貌和于阗国的家园很有几分的神似,而我对于驯服跨下的神驹,已经有了九成的把握。
这时前方尘土飞扬,几十头在此放牧的野马从四野奔腾而来,迎接它们的同伴归队。
正待靠近之时,见到了马背上的我等,马群便轰然停歇了下来。
稍后又兵分多路,若远若近跟在了我们的身后。
如此情景,在汉地长安至贝罗埃亚城邦的这条东西商道上,我们早已司空见惯。
不管是漠北草原、乌孙国的山野,还是萨珊波斯的高原牧场、两河流域的河套一带。
总有牧马的胡人驱赶着流云一般的马群,从商队的侧畔呼啸而过,消失在雾霭朦胧的天地之间。
跨下的野马见到了同伴之后,似乎又鼓起了无尽的勇气。
一番跳跃长啸之后,又肆意狂奔了起来。
就这般又一气奔驰了百十余里,原来追随的马群也渐渐散去,跨下的野马已是强弩之末。
前方是一处低矮的石坡,它们都已无力攀爬,凄惨的悲鸣一声后,慢慢跪下了四蹄。
任凭如何的鞭笞和驱赶,野马也不愿再起身了。
原本充满野性戾气的双瞳,流出了无奈凄苦的血泪,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
奔出围栏时还是清晨,现在已近黄昏。
途中不吃不喝,一气奔驰了五六个时辰。
作为地标的那座海边孤峰,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按照野马的速度,这一日行程应该超过了五百华里,差不多又回到了当初靠岸登陆的地方。
“少主!我们大功告成啦!”
秦冲先到,已在马下迎接我和锅盔了。
此君须发凌乱、嗓音嘶哑,精疲力竭的大声笑道。
“累死我也!快快给马匹补充水液!”
驯马之前早有准备,我们每人背了一个装满盐水的皮囊,此时正好能够用上。
我取下水囊先饮了几口,又把皮囊送到了野马的嘴边。
这个生灵很不配合,不知我们又在用啥花样戏耍于它。
等淋下的饮水渗入它的口里时,才尝到了其中的妙处。
于是张开大嘴一通牛饮了起来,直到把皮囊中的盐水全部喝光才算结束。
补充了水液之后,三匹野马慢慢恢复了体力,踢踏着前蹄站起身来,轻松的抖索着凌乱的鬃毛,很是温顺的耸着双耳,啃实着地面上的青草。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昔日坐骑大宛乌青的影子,不禁一阵心酸差点流出了眼泪。
正如秦冲所言,我们的驯马成功了。
“少主,给它们起个名号吧!”
我们三人不顾劳累,牵着马匹来到了牧草更为丰茂的山麓地带,让劳累一天的它们在天黑之前填饱肚皮。
“本少主的坐骑就叫轰天烈,呵呵。当年爷爷初到于阗国,曾祖慕容秋老人赠送的大宛神驹就叫轰天烈!秦冲,你那匹白马可取名号云中鹤!锅盔,你的坐骑灰不溜秋,就叫它草上飞吧!哈哈哈!”
我拍着轰天雷宽厚温热的脊背,向着两位兄弟开怀笑道。
“云中鹤!彩!”秦冲甚是开心,这几年没有神驹可驭早把他憋坏了。
“草上飞好名头!谢过少主!”
锅盔向我拱手行礼,抬腿跨上草上飞的马背。
这匹神驹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狂躁和惊慌,轻盈的踏着四蹄,驮着我的锅盔兄弟去前方觅食去了。
从此以后,轰天雷、云中鹤、草上飞三匹烈马成为我等最忠诚的伙伴。
每天骑着它们外出狩猎,游遍了这个南荒大陆的所有海国。
等到东晋朝元兴二年的深秋,海船竣工再次挂帆西归之时,我们又把三匹悍马重新放归了山野。
临别之际,难舍难分。
这些有灵性的老伙计,沿着漫长的海岸高崖,一路狂奔追逐着我们渐行渐远的帆影,久久不愿归去。
西风飒飒,萧萧马鸣。
江海一别,岁月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