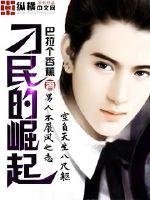等陈厚德一讲完,郭大宝眼眶湿润的看着陈厚德,道:“德哥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哥!等我在鬣狗哪里混好了,我就带人回来,把阎王马家给屠了,为你和毛哥报仇。”金土虎了吧唧道。
“对!屠了阎王马家。”大毛立马附和道。
陈厚德笑了笑,不以为意道:“好!那我等着这天。”
就在这时,张天义手持着电话走了进来,然后把手机递给陈厚德道:“魁哥找你。”
“狗哥电话?”陈厚德不确定,问道。
张天义点了点头,陈厚德见状立马起身接下手机,然后迈步走出门外。
来到门外不远处,陈厚德对着手机惊喜,说道:“狗哥?”
“哈哈哈!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狗头大笑一声,愉悦的声音传来。
“狗哥过的好吗?”陈厚德激动,问道。
“放心!我和你嫂子好着呢,倒是你,可是很不安稳啊。怎么卷进了胭脂楼和阎王马家的斗争中来啦?还受了伤!!”狗头好奇,问道。
“你都知道啦?”陈厚德有些尴尬道。不过想想就释然了,这些事肯定是张天义告诉狗头的。
果不其然,陈厚德话一下,狗头就解释道:“这事天义都和我说了。我听天义说,你现在可是胭脂楼杨浦区负责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之前不是和我说是暂时顶替吴勇的位置吗?怎么现在越陷越深啊?”
“唉!这事说来话长。”
“那就慢慢说,现在你嫂子睡了,我有的是时间。”狗头回了一句。
陈厚德组织了一下语言,便把自己是如何当上胭脂楼杨浦区负责人的事,很详细的告诉了狗头,并且就连自己搞的跋扈网和五脏庙饭店也一并告诉了狗头,基本上算是事无巨细都和狗头交代了一下。
狗头听完不禁感叹道:“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你就居然发展都如此地步,还真让我这当哥的刮目相看啊。”
“我也没想到,这一切都好像做梦一般。”陈厚德同样感慨道。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狗头突然说了一句。
“狗哥你就别夸我了。我就是一条泥鳅,化不了龙。”陈厚德不好意思道。
“你搞那什么跋扈网和饭店,狗哥很支持。但你现在可是在胭脂楼越陷越深。你觉得两年过后,胭脂楼真的放你走吗?胭脂楼在申城的势力不是最大的,但却是关系最复杂的,我怕到时候你想走都走不了啊。”狗头担心,问道。
“狗哥放心,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到时候说不定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呢。”陈厚德安慰
道。
“但愿吧!我问你,你现在手上沾到血没?”狗头突然严肃,问道。
“啊?什么意思!”陈厚德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是人命!”
陈厚德犹豫了一下,解释道:“我也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沾上血,虽然我没有亲手杀过人,但是宴群书、杨之野和那些刀客们却都因我而死。”
“哼!他们该死。”狗头冷漠回了一句,接着说道:“那就好!只要不是亲手都不算。这血一沾,可是想洗都洗不干净了。”
陈厚德一听狗头这话,心里暖烘烘的,陈厚德很庆幸自己能在人生道路上遇到狗头,遇到这位亦兄亦友的良师益友。
“狗哥!谢谢!”陈厚德真诚,说道。
“矫情!以后碰到事就找天义办,特别是脏事,你自己能不沾就不要沾。”狗头提醒道。
“嗯!知道了。”
“那就先这样!哦,对了。你的选择,哥都无条件支持。”狗头说完这句,便直接挂了电话。
而陈厚德却拿着手机久久无法回神,然后对着手机,真诚说了两字:“谢谢!”
…………
第二天早上八点,老胖寝室!
陈厚德从床上爬起,然后开始刷牙洗脸,穿戴整齐后,拿上手机,刚打算出门吃早餐时,就发现手机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一条未读短信。
陈厚德好奇的打开手机查看了一下,短信是郭大宝用一陌生号发来的,不!应该说是郭大宝、金土和大毛一起发来的离别短信。
短信内容:哥我们走了,本打算长篇大论和你说一大段离别之话,可是又不知道说啥。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只能送你一句承诺:若有战,召必回,以后我们就是五脏庙的三把枪,你指哪我们打哪,保重!!!大宝、金土、大毛。
“瘪犊子玩意!虎了吧唧的,你们能平平安安,我就阿弥陀佛了。”陈厚德嘀咕了一声,便把手机揣进兜里,然后走了出去。
自从陈厚德受伤之后,作息算是正常的不能再正常,基本上是早睡早起,要不是身体不能剧烈运动,陈厚德还想练习一会太极拳呢。
今天陈厚德算是起的晚了,因为昨晚从鬣狗场回来,已经是十二点多了,陈厚德因为有伤在身,就直接回去老胖寝室休息了,而洪天明则要去各个场子转一转,并没有跟着陈厚德回来。
陈厚德他们受伤的这些天,最累的人应该算是洪天明,不但要照看五脏庙生意,还得兼顾其他场子的安保工作,再有就是得应付杨浦区各产业负责人。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洪天明可是忙的不可开交,吃住都搬到了外面。
而老胖寝室就成了陈厚德自己一人的养伤之所!
陈厚德吃完早饭,就过去图书馆看书,这一待就是一上午,然后准时准点的过去五脏庙喝张国民精心准备的补血汤,最后又回去图书馆继续看书。
这一天就这样悄然而过!
傍晚时份!
陈厚德一走出图书馆大门,放在兜里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陈厚德掏出手机一看,见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着一个“家”字,不禁咧嘴一笑,这是来自陈家庄小卖部的电话。
这电话是陈家庄出门在外游子们,心目中的家和牵挂!
“喂?”
陈厚德连忙接起电话,愉悦的吐出一字。
可惜电话另一边却迟迟没有回应,正当陈厚德疑惑之时。
手机之中传来了一声,大力低沉压抑之音:“哥……”
陈厚德闻言,身体不自觉一震,抓住手机的手,微微一颤抖,手机差点就脱手而落。
“奶奶走了。”大力接着说了四个字。
此时!
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家庄,陈大力一手握着电话放在耳边,脚上穿着一双老旧布鞋蹲在小卖部的破木桌下,把头埋在膝盖中,肩膀耸动,哽咽声无比压抑,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也没有泪流满面的悲恸,他只是把脸庞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到。
此时的大力,再也没有在深山里与野兽搏斗的铁骨铮铮和骁勇善战,只有无尽的落拓和悲鸣。
说出“奶奶走了”这短短四个字,彷佛比赤手空拳对付一头深山里的熊瞎子还要来得吃力艰难。
………………
陈厚德一听,便沉默了起来,在听到大力那低沉压抑之声时,陈厚德就已经有所感应了,只是没想到是大力的奶奶。
当时陈厚德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母亲,现在虽然知道不是自己母亲,但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与大力相依为命的奶奶走了,从小把大力带大的奶奶走了,大力唯一一位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走了。
陈厚德顿时就像被人抽空力气一般,背对着图书馆蹲了下来,蹲在台阶上,怔怔出神望着这来来往往的学生们。
陈厚德突然抬起头,似乎是不想让某样东西流出眼眶,颤声问道:“奶奶走之前说什么了?”
“让你好好读书,做个有出息的人,还说让我好好照顾自己,说下辈子还当我奶奶。”大力再也忍不住悲鸣,带着哭腔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