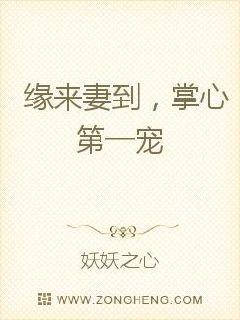“这彩票之营所获之利竟然有如此之巨大?”皇帝指了奏疏处的“可日获万贯之巨利”的字眼,吃惊地问道。
“是。”武旦重重地点头,沉声道:“其实这日进万贯之数还只是齐泰所营的‘聚宝坊’一家之利,如若将整个长安城所有卖家的归总,怕是十万贯也未必没有。”
日进万贯,甚至是十万贯……
虽然武旦言词凿凿,可皇帝还是有些不相信:“果真?”
“果真。”武旦正色回答。
天哪,真是悚然惊闻,拥有九州万方的皇帝陛下被惊到了,他万没有想到不过是小小的几张纸竟能生出如此庞大的巨利!
相比这个行当,盐、矿之产又算得了什么?
若是真能如武旦奏疏上所写,将其归为朝廷所有,那么皇帝一直想要做却不能做的事情就都能够做了,比如说征契丹,平突厥,征吐番……
至于武旦奏疏上所写,以什么慈善的名义募款,将募来的款项用来修桥铺路,办学、经医,扶助孤寡贫病……这些事也是要做的,但是饭得一口一口的吃,事情得一点一点地做……用不着太着急。
只是喜过之后皇帝的脸上又显露出一丝为难来,迟疑地道:“可是,朝廷终归是朝廷,与民争利……怕是会引来非议。”
“父皇不必忧心,太子可为父皇分忧。”李成秀笑着言道。
“哦?你如何替朕分忧?”皇帝兴致勃勃地看着李成秀。
武旦沉痛地说道:“昨日齐泰进宫来,儿臣听他说了一件事,城西永和坊有一家十一口被人火活活烧死在了家中。”
“什么?”皇帝闻言顿时龙颜大怒:“是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
当然,此刻更想问的是,这事儿跟彩票有什么关系?
“父皇且慢息怒,请等太子将话说完嘛。”李成秀冲皇帝眨了眨眼说。
“你接着说。”皇帝一指武旦。
武旦连接着说道:“据齐泰所说,那家人有个儿子人在外面欠下了巨额的赌债,赌坊的人追到家里逼债,失手引起了大火,才致一家十一口惨死火海。”
皇帝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恍然道:“你们的意思是要朝廷以此为契机,对赌博一业进行严查、打击,顺势便可将彩票一行收归朝廷所有?”
李成秀言:“是,也不是。”
“何解?”皇帝问。
武旦说:“凡沾上赌博的人多是荒废本业,倾家荡产的下场,就算是一个好人只要一沾上它,也会变成一个品行卑劣的贪诈之徒。可是,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却并非只是他们自身品性的问题。儿臣们认为,除了赌博者自身的问题外,赌场也有很重的责任。赌博,亦称博戏,戏者,玩乐也。既是玩乐的一种消遣本是无可厚非,想来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将它当成一种发财的途径,都只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然,走进赌场却是由不得他们,世间赌场十间有九间半都会千方百计地引诱他,构陷他,让他深陷于赌桌之上,欲罢不能,直到赢光了他的家产还不罢休,还得让他卖尽自己的儿女,逼死了他才会罢休!就像齐泰所说的城西那家人,就是家主逼债所致!死还只是轻的,更有甚至者是沦为了盗匪。凡是陷于赌博中的人,多是越赌越输,越输越要赌,输得家产精光,儿女卖尽,实在是没得卖了,便做起了贼,行起了盗,贼盗聚在一起便成了匪,为一方之大患!是以,赌博之业实该严格的约束控制,收归彩票一行不过是搂草打兔子。”
说罢,武旦又从袖中掏出一叠纸来,双手举过头顶,递于皇帝的面前:“是以,儿臣还写了一封《奏请朝廷严束赌博疏》。”
皇帝忙将手中的奏疏放下,赶紧将这封《奏请朝廷严束赌博疏》拿起,飞快地将其看完,只觉得字字如刀,句句似锥,撼人心魄。
“你写的这些可都是事实?”皇帝指了奏疏上的一段文字严肃地问道。
“回父皇的话,全是事实。”武旦说:“是儿臣让慕轩和齐泰查实了的。”
“好,好,好!”皇帝面露喜色,将两份奏疏递给皇后,笑道:“你看看老六写的这两份奏疏,颇有老大的神韵。”
皇后也不扭捏,大方地接过了奏疏看了,看完笑道:“语气倒真有些像老大,不过又与老大写的不一样。”
“正是。”皇帝说:“老大的奏疏文采飞扬重恩威,而老六的奏疏却更重实例。一个是严威有度的君王气度,一个是踏实肯干的守城之主。”
“儿臣惶恐。”武旦兴奋不已,却是半点儿也不敢表露出来,还要说:“儿臣哪敢与大哥比高低?不及之万一也!”
“唉!”皇帝手一摆,言道:“好便是好,你不可太过自谦。你是你大哥从小带大的,你要比他强才更好呢!你大哥,你母后,还有为父我是会更高兴!皇后你说是不是?”
“正是。”皇后温婉的笑着回答。
“儿臣会继续努力的。”武旦矜持地笑着道。
“好。”皇帝收了奏疏在枕边的木匣里,想要说什么,却是张了张又闭上,看了李成秀一眼,不满道:“好个没眼色的儿媳妇,为父我说了这半天话口干舌燥的,也不晓得给为父倒杯水。”
简直是神转折!
李成秀一滞,脸儿随之一红,连忙从地上爬来跑到几边抓起上面放着的茶壶拎起来,倒不是空的,却是冷的。
“儿臣现在就去给您煮。”李成秀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抱着茶壶就往外走。
“我去瞧瞧,她第一回怕是还找不到茶房在哪个方向呢!”皇后笑着说,李成秀连忙停下脚步,等着皇后一起出了东侧殿。
出了殿门,下了台阶,往左拐,顺着房廊往南,一直走到了东偏殿尾的一间房间前。
早有宫人跑在前面支会过了,等李成秀和皇后到茶房外,茶房的管事太监已经是恭候多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