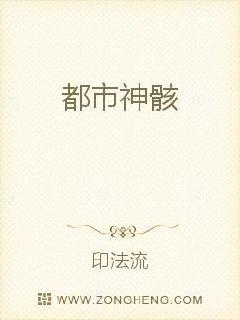小时候不也一起睡过,那时候,四姨为了见母亲一面,偷偷的攒足零花钱从镇里坐车到明州市区,急得整个刘家上蹿下跳都报警以为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姐姐这身份,大上太多岁数,其实年纪小的时候,就基本上担起了半个母亲的职责,四姨和母亲从小关系极好,原因还不是归根于母亲亲手把她带大的,刚出生没多久,也是天天抱着,屎尿布的伺候,一起睡一起吃饭,好不容易长大了些许,然后某一天,这妈妈般的姐姐跟着一男人私奔走了。
但张重水是不大任这借口,自己和四姨才差了三岁,母亲和父亲去明州的时候虽然说是奉子成婚,但小时候母亲带过四姨,也不过就两年时间。要说稍微大了点的四姨之所以总是道听途说的憧憬着母亲,一方面是血脉关系,而更重要的则是,她骨子里,喜欢听的是关于母亲为爱反抗家族的故事。
于是在四姨小学四年级的的某个周五放学下课,便一张车票跑到了明州,在张重水家里住了两晚。
可小时候那都是孩子,孩子不说辈分,也算两小无猜,现在都年纪大了,再一起睡下不太合适。但四姨觉得没必要浪费钱,也不知张重水还私底下给前台补了款项,那领班的小姑娘直勾勾的看着四姨背影,还低声吩咐说小心晚上警察查房,到是让张重水哭笑不得。
不过水哥海外飘荡多年,实话说也遇到过不少形形色色的女人,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美女,热情奔放,浪腾起来简直海啸一般,不过有一句说一句,也很容易滚了床单第二天翻脸不认人。
四姨说要洗澡,进了浴室哗啦啦的水声扑打在她虽然略显娇小但却分外修长的身躯,仿佛都能听见那凹凸有致的轮廓曲线一般,可是让回国两年都还算规规矩矩的张重水心里有些不好的想法。
这时候,就更应该是化身为定力超人,内心般诺般诺清心咒念叨起来,打开电视看着球赛,强行分析球场队友的无球跑动。
四姨出来,穿着一身白色的丝绸睡衣裙子,由于吃的清简,消瘦的上半身总觉得袖口缝隙有那么几许春光乍泄,张重水赶紧进去也用冷水洗了一把,苦笑着自己这两年就疏于锻炼,倒是这么容易蠢蠢欲动,放到以前出任务的时候,那都是无初次掉脑袋的破绽。
好不容易压下焦躁不安的小兄弟,拉开于是滑门,四姨已经是侧卧闭眼。
也是,按照她的性格,若不是出了天大事情都不愿意回到刘家,这次自己亲姐姐出了车祸,心情能好到哪里,这才年过三十,死了大姐和三姐,这又是怎么一种滋味。
关灯躺下,偌大的双人床楚河汉界分明,张重水心大,眨巴了几番眼睛看着漆黑的天花板就有些困意。
“水儿,血浓于水,要记得了。”
“四姨,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我听的别扭。”
“出门在外,总有想家的时候,在大西北想,在冰原中想,在热带雨林里想,景色在变,可脑袋里家的模样始终如一,不管你认不认,亲人总是亲人,你外公外婆也好,还是你张家太爷也罢,有些东西,倔下去只会后悔。”刘瑾淡淡的说道。
张重水却不吭声,他也没说张家太爷那总是什么都要一手把控的性格,当初家里三代年纪最小的父亲弃政从商,说是要一刀两断隔绝关系,可张重水很清楚,父亲能这么快几年就把公司从明州开到中燕中心商业区,多得都是张家暗地里的关系。什么叫藕断丝连,就是都说了一刀两断,却还千丝万缕,总是摆脱不了他们一辈子的影响。
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千丝万缕,到头来也害死了父母亲。
可张太爷是不会道歉的,他知道张重水回来,又有各种想法和安排,甚至说给他安排了个未过门的媳妇,张重水原本是回家拜祭一下父亲,最后臭脾气一涌,没忍住又摔门而去。
“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姨,既然你我如此相似,又何苦相互为难。”
刘瑾一听,身子轻微一抖,总是没有再说话。
一夜过去,也不知枕边人是否无眠,张重水是休息的极好,他长年积累的训练习惯让他哪里都能轻易睡去,却又如何都不能轻易谁熟。
吃过早饭,两人一并驱车前往刘家村子,刘瑾看着那飞腾小破车,笑道说常年荒原跑的越野都比这破烂卖相要好,张重水尴尬点头称是,说有美女,没香车,他的错,罪过罪过。
刘家村就是山沟沟下的一小块谷底,说是刘家,其实里头有三姓,不过百分之五十人口都是姓刘,可也分内外,不都有血缘关系。村子外头早拉了横条,外婆在穷村子一亩三分地还是极有话语权的,又贼好面子,看着不成要把丧事当喜事来办。
张重水下车,换上一身黑色西装,踏着村口破烂泥地的脏水走入,这么多年了,路都还是没有修好,分明国道离得不远,也不知村干部是怎么想的。
都是一张张木生的脸,都是冷色调的衣服,村子人穷,可不是个人家里都刚好有黑色的衣服,穿的深蓝灰色的要不就是白袍的,硬要说起来也没有几分讲究。张重水没人认识,刘瑾倒是有不少人低声叫唤认了出来。
“瑾儿啊,你可回来了,好好的给你妈安慰安慰。”
倔强的老太婆却就在不远处家门口站着,那破烂的土门隔着左右两门神爷,朱红色的门槛被岁月抹平了鲜艳。
老太婆目光如炬,都说脾气差的人精神就是贼好,看着刘瑾一声不吭,也看不出丝毫高兴。家里头亲戚不要太多,三姑六婆围了上来,刘瑾讨厌的是母亲,对这些叔婶没什么想法,露出笑脸,也算有个交代。
“这先生谁啊,您男朋友么?”
“这是水儿,张重水,大姐的儿子,从海外回来了。”
回来两年,张重水自然没过来拜会过两老人,到是通了电话,点到为止。
“都这么大了,帅气啊,在哪里工作呢?做什么来的,有对象了么?”
张重水听着四周燕燕雀雀的一片,分明是死了人的丧礼,怎么却感觉过来唠嗑聚似的,心情也是不太好,三姨生前是个弱气女人,说话温温吐吐,见过一两次,印象一般,但好歹是长辈,张重水心里有些尊敬。
“哪能呢,没本事,在中燕角落开了个报亭,卖报纸的。”张重水笑着也不说穿,就是装穷,让你们数落。
果然人穷志短,又可以欺负更穷的,听到张重水在当报亭亭长,不少人立即是来了劲头,说什么怪你母亲当初眼光不好之类的,要是嫁给那李少爷就不同了,大富大贵,一步登天,也许刘家村的招商引资就解决了。
张重水轻哼一声,这些人脑袋瓜子真好,这都能怪到他妈头上去。
屋内,黑白照片,棺材,散乱的花束枯黄了一片,外公坐在一旁,老态龙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记忆里头那张横跋扈的模样全然不见了踪影。
张重水进来上香,磕头,然后扫了一眼另一侧角落的两个女孩,名字大概记得,唐糖和唐逸,果然眼前一亮,继承了母亲一脉的美好,俊秀灵气,十分讨喜。
“回来了?”
“给您斟茶来了。”
外公淡淡点头,也不拒绝,张重水内心暗叹,前几年死了大女儿,如今又走了三女儿,二女儿嫁到县城,小女儿又闹翻了常年在国外,仔细想想真是可怜。
陆陆续续有人进来陆陆续续有人出去,按照村子规矩,死人,要宴请全村人,主要是为了洗去晦气。
全村一百多将近两百来人,里头包括了不少邻近城市打工的村子壮丁,都算给刘老爷面子。至于饭钱,大分量统一做,其实也不算太贵,嫁到小地主家的二姐咬牙拿出私房积蓄请了,合着估计四姨也出了一份,不然外婆脸色估计更黑。
张重水坐在一旁角落,也不受人待见,他是没有所谓的,没人管他最好。
饭前时辰算到,要给棺材下土,村子一波壮丁扛着出门,向东走了不远来到后山墓地,路上张重水听人说三姨车祸被撞得面目全非,是外婆花了七天七夜一点一点的用针线把脸蛋给碎皮给缝补上去。
一杯黄土盖上,两姐妹走出来,似乎不太习惯有这么多人盯着,迷茫的双眼四处摇曳,好不容易拿出悼词说了生平,眼泪又是一箩筐的哭成了水人,好看是好看我见犹怜,村人看着直摇头。
“可惜了这一对姐妹花,长得这么水灵,却要年纪轻轻许给赵家小霸王当媳妇。”
“这没办法的事情,赵家有钱有权,分明是他们公司的司机撞死了人,还反咬一口说刘静走路不长眼,最要命的还是两姐妹的父亲唐涛,早年赌博欠了赵家八十多万高利贷,现在可好了,夫债妻还,母债女还,命苦啊。”
张重水听着,掏了掏耳朵,感觉像是听故事会一样,就是觉得惨惨惨。
可更惨还没来,好不容易众乡亲入座,刘老爷招呼客人吃饭,这是村口三辆满载的武陵宏光拍马感到,走下就是一波精壮男人,匪里匪气,一脸横肉。
“呵,看来我到的正是时候,来来,赶紧给我丈母娘上香!”
为首的矮胖青年走了进来,嘿嘿一笑,一双眼珠子盯上了唐家两姐妹,差点没有露出哈喇子,那宛若囊中物的赤裸眼神,充满了纯粹的欲念。
刘家村众人纷纷面色转黑,可是又不好说些什么,张重水看着外公外婆两老人气的胸口直震,心想真是风水轮流转,以前的大流氓活成了老流氓,最后被隔壁村的小流氓给欺负了。
赵家小子大摇大摆上香,随便的弯了两下肥腰,然后转头面色一变。
“完事了吧,唐糖唐逸,说好今天带你们走的,行李备好了?学校那边我已经给你们退学了,以后安心在家里呆着。”
两小姑娘相互依偎缩在一起,脸色发白,飘忽的眼神看向四周,但周围一圈人却都偏开眼神不敢相望,显然都是心虚的很。
“走吧。”
赵小子上来,身手就要拉人。
“哟,小哥热情啊,怎么就拉我手了。”
只是低头一看,居然一只老大粗的男人笨伸了过来,被一把握住,定睛一看,众人一愣,可不正是报刊亭长张重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