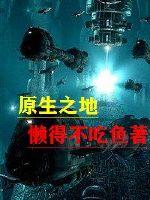第六十六回(上)花开花落有重开日人长人老无再少年
鸣雷帝国,苍云郡,榕桦县。
榕桦县与潼河县南北接壤,由苍云郡通向旭阑郡的东塘关即在榕桦东南境。
作为秦岭驿道与嘉川水路郡际关卡,东塘关每日都吞吐数以百计的商贾队伍。
榕桦凭此地利,郡县生产总值大幅领先于近两年方才脱贫的潼河,水涨船高的,居民平均收入近三倍于潼河。
然而,数据向来无法反映完整的真实,更何况,数据前边还有“平均”二字。
许多“被平均”的居民,依然过着清贫艰难的日子。
老余住在余家庄。
余家庄地处榕桦西北,依山傍水,老余家旁边就有一道山沟。可别小瞧了这道不过四五尺宽的小水沟,老余清楚的记得,从嘉三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大水,大水不光把自家房屋靠近水沟的灶房冲塌,更差点将儿子给打跑了。
余家庄,顾名思义,十数户村民都姓余,老余小时候曾听爷爷说过,爷爷六兄弟为了逃躲饥荒,从蜀岭郡一路乞讨流浪到这里,见这里依山傍水、土地肥沃,便决定扎下根来。经过四代繁衍生息,成了如今的规模。
余家村边就是一堆土包坟头,从没有挨过饥荒死去的五爷爷到后来次第去逝的血亲堂戚,都葬在这片坟地里,都是一系家族,自然没有什么害怕坟地闹鬼、影响村庄风水的说法。
清明早过,可是老余夫妇今天都起了个大早。
见天色尚暗,老余走到灶房土灶旁边的舂碓边上一堆摆放整齐却各种杂物都有的杂物中,小心翼翼的提起煤油灯,提过到眼前瞄了瞄,见尚有小半瓶煤油,放到灶上,捡起火折,就要点起煤油灯。
就要老余即将点燃灯苡时,老余的婆娘一把拍掉老余的手,抢过火折吹灭盖上,咒骂道:“出息了?点油柴不行,非要烧煤油?”
老余一脸不耐的反驳道:“这不是天还没亮好,不大看得清嘛!再说了,我又不是天天都点,今天不是爹的祭日吗?我才想着别那么小气的。”
山野村妇可没甚好听声音,也没甚和气语调,山里的夫妇,能有几天和气日子?通常都是从起床开始,一天到晚都在吵嘴,直到上床睡觉都不消停。
“哟?你不是一直吹牛你那眼睛有多厉害多厉害,以前在部队时,十丈开外都能射中蚊子腿吗?今天牛皮终于破了?”老余的婆娘怪腔怪调。
老余在部队里时,多凶悍的契夷蛮子没见过?可是自从退伍还乡,曾经年轻的婆娘变得人老珠黄不说,白兔一样温柔体贴的性子更是不知何时变得如同野猪恶狼一般。自诩对上三个契夷蛮子都能尽数斩杀的老余,可是怕极了发起火来的婆娘。
被婆娘调笑,老余也不敢反驳,闷声嘀咕了一句连自己都听不懂的抱怨,抬起袖子用力擦了擦眼睛。
“服老咯服老咯……”老余摇头晃脑的感叹一句,却见旁边婆娘已经点燃了煤油灯。
老余的婆娘将灯芯朝下薅了薅,三寸高的火焰一下子萎缩到不足一寸,将煤油灯朝老余一递,嫌弃道:“拿去,我不需要。”
陪自己吃了一辈子苦,老余清楚;婆娘在自己到西疆大营去戍守边防时,婆娘受了怎样的苦,老余也省得;毒辣的刀子嘴下边藏了一颗多么柔软的豆腐心,老余更明白得很。
不过,对老余来说,心底的感激与爱意,可爬不上嘴巴来。
老余只是憨笑兮兮的接过煤油灯,然后就屁颠屁颠的朝门外走去,正好听到一只最先响起的咕咕溜鸡鸣,“哼哼”两声笑道:“就宰这只了!”
老余的婆娘早已到灶后淘起糯米,准备蒸熟,与不知道哪只倒霉的大红公鸡一起,用以祭祀丈夫的先考,当然,也是自己的表叔。
天色渐亮,村庄里次弟响起舂碓的“咚咚”声音,一家,再一家,继而连绵成片,仿佛村庄正在苏醒一般,召示着新的一天、新的开始,
走在田埂上的老余婆娘收起竖得老高,凝神细听舂碓声音的耳朵,啐了一口,不屑道:“要不是我今天有事,能让狗蛋家抢了头碓?要我说,他家娃儿这名就起得不行,狗又不生蛋,像我家鱼蛋多好听。”
城里的女人大多以为山里的女人生活没甚盼头,面朝皇土背朝天,逆来顺受。
这一点,老余的婆娘可是万万不认的,山里的女人,那可是争强好胜得很哩!特别是“能生儿子”和“干活勤快”,那可是山里女人之间一等一重要争胜点,其它更多比鸡毛蒜皮还小的事情,那可就更不能服输了。
总之,除了不争风吃醋,啥都要争一下。
老余翻起白眼:“是是是,你家鱼蛋最好听,是你家的都是最好的,别人家的都比不上你家的。”
“那倒也没有。”
听到婆娘这般回答,老余反倒愣了一下,不料,下一瞬,老余就极度不爽的咒骂了一声。
“人家的男人可比我的好多了。”老余的婆娘认真沉吟道。
坟地就在村边,老余夫妇俩没走多久路就到了。
清明刚过不久,坟地里的每一座坟头都已经用镰刀割去了杂生的丛草,用清水擦洗过墓碑,每座坟头上都插有用青竹与花绿纸钱制成的招魂幡。
来到先考的坟前,老余放下手中麻袋,先掏出一口关大不小的黑锅,从锅里把整个煮熟的大公鸡拿出来摆到墓碑前后,老余再从麻袋底取出香纸,憨笑道:“爹,我又来了。”
老余一向喜欢念叨不停的婆娘,也不知是不是到了公公的坟头的缘故,安静的从麻袋里掏出碗碟,盛了三碗糯米饭,再倒上三碗米酒,摆到大公鸡前方。
夫妇俩摆放好祭祀饭酒,老余就点燃了纸钱。
左手端了好大一沓纸钱,右手不断扯下放到火堆里的老余摇头抱怨道:“爹,你是不知道,现在的钱,可真他娘的难挣!你活着的时候没享过福,现在死了,我就给你多烧点!”
老余的婆娘乖巧的拿来一把香点燃,墓碑左右各插一柱,而其余的,老余的婆娘就插到了坟包各处。
按理说,依然风俗,在墓尾也是要插上一柱,也是要祭上一碗饭、一碗酒,用以祭奠过路的亡魂,莫要打扰在此处长眠的逝者安息。
不过,这个风俗老余可不遵守。
原因也简单,老余是个老卒,老余的老子也是个老卒。
生且不惧厉鬼来,死去何怯游魂扰?
“他们敢?”老余第一次向婆娘解释时,就是模仿老子临死前的哂笑语气。
“爹呐,鱼蛋最新一封家书,是邮差昨天才送来的,不说你还没听过,连我都还舍不得看,等着今天我们一起看哩——”提起儿子,老余脸上不由自主盈上骄傲自得的笑意。说罢,从上衣贴身的内袋里小心翼翼的取出信件。
信封的开口尤其平顺,并且没有完全扯掉,一截细长纸条开口,沾连在半寸的信封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拆信时不是随意的一下撕开,而是用剪刀小心翼翼的裁剪的。
老余从信封里取出信纸,昨天剪开信封将信取到一半时,想到今天就是先考的祭日,与婆娘商量之后,决定今天到先考的坟前一起看,忍了一天一夜,如今可实在是心里得很了。
展开信纸之前,老余先将信封郑重其事的重新放回上衣内袋,而后,一双满是老茧的粗糙大手竟然有些颤抖。
“你激动个啥?没出息!别不小心掉进火里了!”已经半晌没有作声的老余婆娘见到看到老余颤抖的手,再管不得什么贤妻形象,大声咒骂道。
老余看向自己颤抖的手,怔然呢喃道:“不是我抖的,是它自己抖起来的……”
“抖得跟旱鸭……”感觉到丈夫的口气不对劲,老余婆娘将出口近半的怼辞强咽了下去,一下子紧张起来,一把握住老余的双手,感受到老余的双手还在颤抖不止,焦急道:“老余,你别吓我,你没事吧?是不是拉车拉太累了?”
曾以手稳弩准闻名营账的西疆游弩军夜狼营斥候老卒摇了摇头,脸上的复杂神情,是老伴儿看不懂的感慨寂寞。
英雄迟暮。
老余很快调整好了心情,笑道:“人老了都会抖的,你莫笑我,你以后也一个卵样。”
见老余重新挂上笑容,老余的婆娘这才稍放下心,不确定道:“真的?你莫哄我,要是有什么病,咱就去镇上找郎中治。”
“你这糊涂婆娘!”老余不满的骂了一声:“看郎中多花钱啊!咱们的钱,可是要存下来给鱼蛋建房子讨婆娘的!我连地皮都挑好了!”
骂声已然出口,老余才后知后觉的盈上一副后怕不己的表情,论吵架,老余觉得十个自个儿也顶不上婆娘半张嘴。
熟料,老余的婆娘轻叹一声,轻声道:“儿子是重要,但你也一样重要,我们生鱼蛋生得晚,后边想怀已经怀不上,你们俩就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两个男人,谁都不允许出事,谁都不允许走在我前边!”
人生呐,属实有趣。
作为西疆老卒,从入伍到退伍,老余倾尽所有,让自己从善良变得残酷,而从退伍到如今,老余再次用尽全力,让自己从冷血变回温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