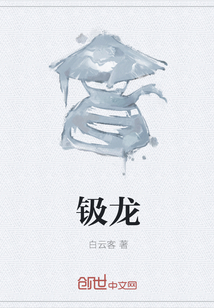汴河的水也浅了很多,水位只有往年冬天的深度,很多大船都靠不了岸;今天更是明显,停在河中心的两艘大船画梁雕栋,三层船舱雄伟壮观,装饰得金碧辉煌,几艘中型的官船正在来回穿梭,把人从码头接上大船。码头上围满了人,只不过是看热闹的,都簇拥在百步之外,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送行的二十多人都在里圈,为首的六人离上船处只有十步的距离。
人群中的翰林学士李邦彦不由得皱起眉头,六人为首的一人身材削长,是刚刚被赶出朝堂,即将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青州的余深;旁边大腹便便的老人是蔡京的亲家宋乔年,已经被贬保静军节度副使,蕲州安置。两人都是额头贴着蔡党标签的人,送完蔡京,明天就要动身赴任;下面的叶梦得、蔡嶷也不意外,都是依附蔡京的死党,蔡嶷从杭州知府的位置下下来,已经致仕快一年,躲过了这次方腊之乱。
黄经臣是宋徽宗安排来送行的,只有站在蔡嶷前面的那个人没见过,那人身躯九尺,穿着一身青衫,站立着有巍峨之姿,叶梦得和蔡嶷就算同样年纪,比起来竟然有几分不如。那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青色的身形却充满活力,仿佛阳光下的春水,蕴含着难以描述的灵活,全不象叶蔡般的呆板。李邦彦熟悉民间的事,立即明白过来,那是个练武的人,但是一个布衣,蔡家怎么会把他排在蔡嶷的前面?
内侍黄经臣也在想这个问题,宋徽宗让他来送蔡京,不仅是表示皇恩浩荡,对蔡京礼数周全,也想看看哪些大臣敢明目张胆地站在蔡京一边。余深四人不出意外,他们与蔡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来送行只能增加他们在蔡京眼里的份量;其余官员,黄经臣心里暗暗地哼了一声,据说半个月来,蔡京家夜里来客不断,但是真要明目张胆地出面,还是有点胆怯。黄经臣看了那个人一眼,来人恰到好处地谦逊笑笑。
蔡崈和蔡绦满面笑容地走上码头,疾步来到六人面前,给余深、宋乔年、黄经臣行礼道“家叔昨夜偶感风寒,实在行动不便,不能下船与各位见面,委托小人向几位大人请罪。”蔡崈是蔡京最喜欢的侄子,也是蔡京的养子,整日里一身道装,只有在朝为官时,才会规规矩矩地穿官服;蔡绦长得和蔡京有几分相似,眉清目秀。
两人说话态度恭敬,余深听完打着哈哈说“没关系,蔡相为国之擎柱,一定要养好身体。”
黄经臣明白,余深的话是说给自己和宋徽宗听的,皮笑肉不笑地敷衍了两句。五个人说完客套话,蔡绦招呼叶梦得和蔡嶷,蔡崈走到年轻人身前,掏出一沓银票道“卢兄弟,一晃十年没见了,周世叔还好吗?家叔感谢你如约把东西送来,这说不上酬劳,是给卢兄弟的路费。”
卢兄弟神情严肃地伸手挡住了银票说“家师已经离世,所以托我把那个盒子送到汴梁交给蔡相。蔡相要没有吩咐,小弟事情已了,就此告辞。”
蔡崈顺手把银票拢入袖中道“也好,卢兄弟连天奔波,正需要休息,周世叔的事节哀。”
余深、黄经臣几人听了吓一跳,蔡京举家被赶出京城,还有这番影响力,周侗派人远途跑来送行,忍不住又看了姓卢的一眼。卢兄弟听了面不改色,朝众人一施礼,转身朝码头外走去,余深望着卢兄弟背影,看似随意地说了一句“人老了,看着就是感觉眼熟,想不起来名字。”
蔡绦点头道“您老还真见过他,他是周侗的徒弟,玉麒麟卢俊义,大名府的第一富豪。”
黄经臣的心一下子悬起来,周侗可不是一般的人,中原第一高手,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和王安石、司马光一起在包拯手下共过事。黄经臣想问卢俊义送来的是什么东西,想想咽下心头,此刻蔡绦说什么自己都只能听着,无法证实;蔡崈忽然朝几个抱抱拳,仓促地朝后面走去,黄经臣身后的小太监低声禀告,杨志来了。
杨志见到蔡崈施礼道“蔡兄,公务繁忙,我来迟了。”
蔡崈和杨志一直是按照梁寻的关系称呼,蔡崈还礼说“杨兄弟,不迟,你刚刚回到汴梁,正是诸事缠身的时候,有心了。卢俊义来过了,周侗老师已经去世了。”
杨志苦涩一笑说哦“我现在过去,才是给周师傅出难题,卢俊义既然到了,想必一切事情已经做完。蔡兄,给恩师带个话,祝他一路顺风。”
蔡崈与杨志都不想太引人注意,两人一抱拳,杨志掉头就走;蔡崈催促着上船的速度,过了小半个时辰,蔡家的人终于全部上了河心的大船,两船扬起风帆,朝东驶去,黄经臣放下心来,权相蔡京没有耍花招,终于离开了开封。
蔡京并没有病,一直坐在船头的舱里,透过窗户,看着码头上的情景,听见管家徐若谷送茶进来,问道“若谷,昨夜彗星不现,对老夫是个致命的打击。后面我们该怎么做?”
前几天彗星一直出现在天空,昨天蔡京确定动身,当夜彗星就没有了,实在是个难言的巧合。徐若谷比蔡崈大一岁,是蔡京的外甥,今年已经四十二了,读完书就跟着蔡京,一辈子没当过官,也不想当官;蔡京几次提出挂个虚官衔,徐若谷都没要,不过徐若谷在江湖上的地位尊崇,是徐州神刀门的掌门。
徐若谷沉吟道“舅舅,彗星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不必当真。我们可以走走停停,顺势而为,只要最后到了泗州,就算遂了皇上的心愿。如果舅舅安分守己,恐怕有人会更担心;黥布谋反时,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不放心萧何,萧何依门客计行事,抢夺百姓田地,刘邦才留了他一条命。”喜欢钑龙请大家收藏x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