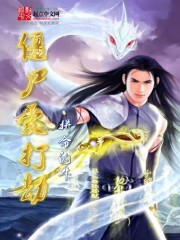车队又行三日,一路无波无澜,然后钻入一片广阔无垠的芦苇荡。
芦苇择水而居,大簇大片,很容易成滩成塘,但绕路而行车队要多行三日,而且芦苇荡里早有窄路,可以避开那些浅滩淤泥,所以也不打紧。
芦苇荡不远有条万里江河,水汽朦胧,在这愈发炎热的天气里倒是个极好的避暑之地。
只是今年雨多了,再加上不久前这条大江几处河堤才溃了坝,虽然明知道这里不可能有洪水,车队里的不少人还是难免有些心惊胆战。
自从知道白衣少年醒了后,方妙语总是喜欢往两个少年人那里跑。
一是表示自己的关心,二是少年的涵养极好,与少年交谈总能让人心情舒畅。
车队里除了赶路也没其他事,倒不如来这里打发时间。
青衣少女依旧那副漠然模样,实在让人生不出什么好感来,不过方妙语也差不多已经习惯了,好歹知晓少女不是看不上他们,而是天生这性子。
只是姐弟俩个一个温和一个冷漠,方妙语常常奇怪,同是一家人,怎么教出了这么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的孩子?
又一番谈笑风生后,在少年委婉提出有些累了后,方妙语识趣离去。
芦苇荡繁茂如林,微风轻拂,便是碧波荡漾。
青衣少女淡淡说,“有人来了。”
不知何时换上一身十分不合身的麻色衣衫的少年笑了下,“我知道。”
然后他忽然说,“教训一下。”
青衣少女微微皱起眉头,看了少年一眼。
少年温和解释,“前两天才找来的,他们很不错。”
青衣少女冷哼了声,不再说话。
车队继续前行,只是谁也没察觉到,芦苇荡里的风声似乎急促了些。
而这些风声掩盖了从几个方向而来的轻微声响。
……
一名年轻人躺卧在被芦苇荡掩盖的一小屋的房顶,微风起芦苇荡,轻轻吹拂着他鬓角发丝,十分闲情逸致。
他自认为是个很乐观的人,从不去怨天尤人。
幼年时与娘亲孤苦相依,受尽白眼,后来娘亲病逝了,他被一群不认识的人带走,送去了那个剑的坟墓,除了断剑,什么也没有。
他不知道那里是哪里,可他却在那里呆了十年,一个人。
前些日子,他从那里出来了,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说,让他在这里杀一个人,杀死了,他便再不用回去,杀不死,他便要永远呆在那里。
那里啊,多么冰冷的世界,哪有这清风暖日来得令人陶醉。
所以,他来了。
……
一个青衫客双手扛着柴刀背在脑后,嘴上念叨着一支乡土气息颇重的小曲儿在芦苇荡里缓行。
“大王派我来巡山啊~”
反复哼唱了几遍,还稍稍蹦跳了几下,终究只是看到一片绿海,百无聊赖,他终于将柴刀从背后拿下来,头也不回问,“你说,老剑神的剑我硬挡,挡得住几剑?”
四周无人回应。
他也不气馁,继续自顾自说道:“当年江湖都以为老剑神折剑,至此一落千丈,谁知近日重出江湖,一身剑术反而像破而后立,几乎无人敢掠其锋芒。若是还有伏龙榜,应该也是前几了,你说我顶着小霸刀的头衔,你顶着毒蜂的名头,虽然是笑传,可你我联手也是能在巅峰修为的人手下不落下风的,一个与那老剑神不分上下的对手,你说胜算有几分?”
手里只有一把柴刀的青衫游侠儿身后依然寂静无言,不过还有漫无边际的风吹芦苇呜咽声,青衫游侠儿就当是回应了。
此人正是江湖上前些日子声名鹊起的小霸刀,张然。一把柴刀刚猛霸道,颇有几分霸刀张冉的风格,再加上名字相似,便被江湖人以小霸刀戏称。
只是这些日子忽然销声匿迹,江湖人都以为是张冉前辈重出江湖,这好汉怕前辈找麻烦,给吓尿了裤子,所以躲起来不敢见人了,却不想竟在这里大放厥词,要知道他连潜龙榜都没进去的。
张然笑了笑,轻轻说,“你喜欢剑,我喜欢刀,你我真是绝配。所以,那柄剑我一定帮你拿到。”
张然身后终于出现一道修长身影,背负着一柄奇特的剑,极细极细的。
她穿了一身黑衫,容貌平平,却格外棱角分明,眉宇间有一股杀伐英气,清风吹拂,那头半长不长的头发便飞舞了起来,有点像狂风里的芦苇荡。
张然立即转身,嬉皮笑脸道:“小洛,你说,你明明长得不好看,我为啥就是喜欢你呢?”
被叫做小洛的女子一本正经说,“因为其他女子都不敢打你,除了我。”
张然一点不尴尬,“那,如果我没打过那人,你以后清明的时候别忘了抽两下我的墓碑,我心里舒坦。”
“好。”女子依旧淡淡说,似乎一点不觉得奇怪。
……
一名粉衣女子由西南而来,手中提了一枝桃枝,提一会儿,她便会拿桃枝去撩拨芦苇,面上便会轻笑起来。
她喜欢这里,这里没有满岛的桃林,可翠绿得让人心情愉快。
她从没想到世上除了漫山遍野的粉色还有令她喜爱的东西,那这次出来就很值得了。
她出来,是有人跟她们做了笔买卖,来挡一个人的路,若挡住了,她们便能彻底出世,不需要再藏头露尾。
这是个很划算的买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所以,她来了。
……
与粉衣女子恰好对角而来的是一名皮肤黝黑如乡野农夫的汉子,神情木讷,略微低头,背上布条微微隆起,似有一个木盒形状的物件。
今日,他要用这些东西取一人的性命。
江湖是不该寂寞,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便是愚蠢。
愚蠢的人从来不该活在这世上。
因为他的愚蠢会犯下更大的错误,像一甲子前的伏龙榜,像江湖的奄奄一息。
这般,一直平静着,不很好吗?
所以,他来了。
……
一袭银杉的男子进入芦苇,背后一柄长剑,缓缓往车队方向而行。
前几日,他与那人一战,胜负难分。
那人说,这世界很大,他偏于一隅,不值。
不值吗?
他不知道,可他生来便是为了剑,从小到大修习的是那些剑术,那个给他喂剑最终被他杀死的人也告诉他,剑楼不能消失,那他不偏于一隅能干什么?
那人说,江湖风云起,何不创出自己的剑术,拾先辈之牙慧有什么意思?
那人说,剑楼,你不就是剑楼吗?那些人迂腐不入剑楼,那些剑术与不存在有什么区别?
是啊,没什么区别,那就烧了吧!
他花了三天时间将剑楼里的剑术都记在了脑子里,然后将那些东西都付之一炬,以后他便是剑楼。
他会寻下一个继承者,等继承者胜了他,他死,继承者便是剑楼。
剑楼,是永远存在的,只要他活着。
可继承者选谁呢?
有人跟他说,这里有个少年,若少年能活着,便是有资格的。
在四个相当于先天巅峰的人……哦,不,还有他的埋伏下活下来的人,即使不是剑者,也是有资格的吧?
所以,他来了。
……
芦苇荡漾,风声飒飒,天色渐渐黯淡。
车队停下,开始扎营休整。
车队间,闭目养神的少年忽然睁开眸子。
与少年隔了些距离的青衣少女也睁开眸子,奇怪看着少年。
少年沉默了一两个呼吸,看向肩上的白鸟,轻声说,“下来,不许乱跑。”
“咕。”滚絮轻叫了声,不过仍乖乖飞下了少年肩膀。
然后少年冲少女轻笑了下,温和说,“乖乖呆在这儿,我去去就回。”
说完,少年站起身来,跳下木车,很快消失不见。
少女怔了下,轻轻皱起眉头。从没有人以这般口吻跟她说话,好像哄孩子般。
她有些不悦,又不知为何生气不起来。
犹豫了一瞬,她歪头听了听风声,也跳下马车,钻进了芦苇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