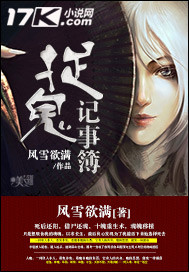第二天一早醒来,看向窗外,街上公路上停的车辆都走得差不多了,也有些陆续开到这个地方来吃早餐的,各个早餐摊子显得异常繁忙,我和师父也去了早餐点凑个热闹,可我们在没问他们什么事?大早晨的提车祸相当不吉利,这对常年跑长途的司机来说是相当大的禁忌,再说从他们身上也在得不到任何的线索了,问了也是徒劳,和闲扯淡是没什么两样的,吃完饭,等太阳升得再高些,阳气在重些,师父打算带我步行到‘死亡公路‘那一段勘察勘察地形,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为晚上的行动打打前站。
吃完早饭,我和师父步行一路向南出了镇子,走出镇子不远,就来到了国道和省道的交汇处,看路上的标识牌上的路标,这一段公路就应该是崖北段到崖南段所谓的死亡公路了,按常理说,这处国道与省道交汇的地方应该比崖北镇中心还要繁华热闹才对,实则不然,而且显得相对的落寞,零星的店家没有生气,也很少有车辆停下有需求,十字路口两旁很多栋低矮的楼房都紧关着房门,看上面风雨抹去光彩的广告牌,以往都应是生意红火的商店和旅馆,它们现在的暗淡的揭示着它们曾经的无限繁荣,现在的这番惨兮兮的模样能充分说明问题了,车祸猛于虎,贻害却无穷。
顺着这些光门大吉的店铺继续往南走,越往南,路两边建到一半却未完成的房屋零零落落的越多,很明显都是些正在建设的还未盖完的突然就放弃了,让人看了真是可惜,得浪费多少的建筑材料,而这些残砖破墙后面的旷野上是片片相连的杨树林,且一眼望不到头,这个时间点公路上车流如虹,运务比较繁忙,在公路上是不会有任何发现的,师父的意思是何不下去公路到两边的杨树林里瞧瞧有什么蹊跷,我和师父像是出来拾荒的,其实是漫无目的却又像是很悠哉那般。
下了公路,走在荒凉的田地间,有沟有坎,杨树林就在眼前,我和师父脚下踩着层叠的枯叶一步步走进冬季落败的杨树林,也算是来对了地方,林子里面是大片的荒坟,看着很是凄凉,像是一首古诗中‘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写意,可除了这些映入眼中的荒坟之外终究还是一无所获,到此,关于死亡公路的有价值的信息还是为零,师父还是决定已退为进,熟悉好了地形,到晚上在前来这里瞧瞧看看,说不定会有意外的发现。
中午,我们师徒也没有吃午饭,所有的事情一筹莫展怎么还有心思吃饭呢,就这么呆在小旅馆里什么也未做。
下午的天,越阴越厚,带着灰蒙蒙的的微光,像是要下雪的样子,到了傍晚,夜幕来临,天空愈加的浓重,这雨雪不下则以,一下便是大的,这鬼天气无疑给这次出活蒙上了一层不安的气氛,师父半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只言不发,我了解师父的脾气,他是心里越焦急表面上越显得平静,静的像他从未存在一样,今天是23日了,还有明天一天就是25日了,仿佛时间从未如此咄咄逼人,难道这几次车祸都是意外,都是偶然,这里只能算是个事故频发路段,只是被人以讹传讹,把这段路给妖魔化了,给扣上了死亡公路的名号?师父平常也是救世主当惯了,难不成这次是庸人自扰,走入了一处无形的怪圈……
一直就这样硬撑到晚上八点多,外出,说是简单吃些饭吧不如说是补充能量,等到夜深了还要进入死亡公路一探究竟呢。
吃完晚饭,和那些个走南闯北的司机凑在一起围着小餐馆的电视机看了会电视,夜终于深了,司机们都陆续的回到了车上休息,我和师父出了餐馆的门直奔死亡公路了,越往南走,街上的灯光越是稀少,偶遇行人都是神色慌张的跑走了,偶尔几辆货车慢慢的从公路上驶过,他们却是远近光灯不停的转换,生怕撞着什么东西或躲着什么东西似的,货车终于远去,我抬眼看向夜空,黑如漆墨,看不见一颗寂寥的星辰,踩着脚下的死亡公路看向远方,也是幽深深一片,这黑暗中的天圆地方犹如地狱的帷幔,掀开绳系,就是地下十八层。
我跟在师父的身后踩着白天熟悉好的路,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公路上,下到公路下面一处白天踩好的点,一处能容下好几个人的壕沟,我和师父跳下去,撩些枯叶扑在身下当是垫子半躺在壕沟里面,就这样守着黑夜,期盼能出现一些有价值的转机……
长夜寂寥漫漫竟然下起了大雪,起始如飞不透黑夜的飞蛾,随后便如鹅毛是漫天飞舞,这雪夜也算是来的及时,为这死寂的暗夜带来了些许的活力,我半躺哪里脸冲着天儿,任由雪花落到脸上嘴里被我的体温融化,你别说还倒挺惬意的,这夜这雪景,还真是难得,在加上蹲在这壕沟里,又是刚下雪的缘故,壕沟里温度尚可,也觉不得冷,我这蛋样和村里那些半截黄土的老人冬日里躺在街上晒太阳有什么两样呢。
师父背对我不知在观察壕沟外的什么也不与我讲话,也许是在陌生地昨晚没有睡好,我半躺哪里没一会就迷瞪害困起来,反正师父离我不到两步,我放松了警惕心想还不如睡一会,但我忽略了一个常识那就是,人们在害困的时候,人的意识也就跟着变得薄弱,这个时候周围的脏东西就会动起来,也正是我这个失误才使我们师徒得到了一些收获。
雪一直下,雪花也许早已掩埋了熟睡的我,时间不知过了几时几刻,我觉得身上冷了,我轻轻的挪动一下身子,心想坏了,我身在荒坟野坡的本想迷瞪一会的怎么给睡着了呢,我轻抖几下脸,眼上的薄薄的积雪滑落,我睁开眼,刚想喊声师父,却发现好些双眼睛正盯着我好奇的看呢,有发红的,发白的,还有两黑窟窿的的,大都头颅残缺,五官不全的整整围了我一圈,我一看则明,这应该是些漂泊多年的孤魂野鬼,它们见我醒来,都凑上来问我:
“你是人还是鬼?”
它们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问梦逼了,我该怎样回答它们呢,要是回答错了会不会有灭顶之灾,我再一想,不对啊,能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连我是人是鬼都分不清楚它们也真够低级的,它们虽然鬼多势众,能看得出大多都不堪一击。
我刚想开口和它们讲话套个几乎,想从它们口中套出些有价值的话,师父也许是听到它们讲话了这才回过头来,我看师父的模样也应该是睡了一会,不然他是不会反应如此迟钝的,也许师父早有此意,害困不过是一种最低级的招鬼术,也是在暗夜旷野中最好用的方法之一。
“你们好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好久了”师父开口。
“你俩是鬼?”它们转向师父怀疑的问。
“对啊,和你们一样啊,它们说让我俩在这里等你们”
要说师父白活起鬼话来还真没有人能比上他,趁它们和师父说话的时候,我抬起头忘了一眼,吓得我心头不由的颤了好几颤,娘的,壕沟内外站站的满满的都是孤魂野鬼,数都数不清楚,刚才我还轻视它们呢,就现在它们的这阵势万一师父说错话发生骚乱它们一鬼一脚都能踩死我们,这俨然是起旷日难见的孤魂野鬼的聚会,有些阴阳先生或许终其一生也不会碰见却让我邵二蛋不幸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