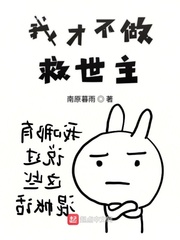第三章 帽子
这天是霍慑的出院日,他难得起了早,预约了出租车,感谢了医护人员,正按日程计划收拾东西,一个仿佛没头的陈霰白横冲直撞地跑进来,进来也什么不说,光盯着他看。
他被她看得发毛,哼出一个“嗯?”
却听陈霰白张嘴第一句话,就是咒他最近会有血光之灾。
要不是知道她是什么德行,他还真想跟这个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的神婆杠一杠。
“你梦见我死了?”他一边蹲着装行李箱,一边问她,“怎么死的?”
陈霰白肿着眼睛站在他旁边,低头像个挨训的小丫鬟:“不知道。”
“身上有致命伤吗?”
她眯着眼睛,回忆道:“可能有?你周围淌了好多血。”
“那我是失血过多?”
陈霰白有一说一:“……不知道”
他把那只讨人厌的熊肚皮上的纸条拽了,拎着熊的后颈问陈霰白:“你要吗?”
陈霰白摇摇头。
预言只跟他说了一半,最关键的霍慑还没听到,陈霰白像个小鸡仔一样的跟着他后面跑,霍慑无视了几次,发现甩不开这个鸡仔,只好停下来听她接着说。
陈霰白如愿以偿,当说到还有个陌生人在场,霍慑终于提起了兴趣,问她:“谁?”
“不知道。”
霍慑不敢相信这个预言本质是个废话:“总之最近我有危险了?”
陈霰白揉了揉眼睛,预言的特殊性在于永远不能被断言,她为难道:“可能吧。”
霍慑实在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初级志愿者,听她说了这么多,竟然还和没听一样,不免有些动气:“你这个预言能不能再准一点?”
陈霰白现在被霍慑这么一顿追问,回想起来也觉得很荒谬,梦里的她明明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就能哭得那么伤心。
最后她把霍慑一路送到路边,车早就到了,她替他抱着熊,费劲地拉开出租车门,转头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最近您还是小心一点。”
霍慑“啪”的关上后备箱,本能地不想相信她的预言,但对她的好心还是得表示一下,于是敷衍地“嗯”了两声,接着对她挥了挥手,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陈霰白目送车载着霍慑消失在十字路口,正担忧不知道她的话霍慑听进去了多少,一低头发现熊忘记给霍慑了。
***
霍慑到家之后,没直接进门,他把行李箱靠墙放在楼道里,先掏手机打了个电话。
两分钟后楼梯上响起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一个穿着宽松t恤的男人,顶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踩着拖鞋火急火燎地冲了下来。
那人在看见霍慑的一瞬,刹在了台阶上,腿上和上身成套装的大裤衩抖成了旗子。
他扶在楼梯扶手上探头探脑地打量了霍慑一番,明明长得十分清秀,却笑出了几分朴实,说:“我都以为你要死在医院了。”
霍慑还没回话,他仿佛直接看透了霍慑在想什么,回道:“我今天休息啊。”
“我知道,知道,”他欢乐地三两步从楼梯上跳下来,从霍慑身后的牛奶箱里掏出一把钥匙,熟练地开了门,“伤员别动,放着我来。”
霍慑听话地把手机塞进口袋,站一旁当起了大爷。
他殷勤地替霍慑提起箱子,忽然想起了什么,脸上多了几分藏不住的腼腆,道:“你在医院住了这么久,看到我们胡老师了吗?”
“说错了,是大家的胡老师,”他接着自顾自地问,“她好不好?”
霍慑也不说话,跟在这个工具人身后,背着手,老神在在地进了门。
“我最近没在协会看见她,还以为她在医院。”他放下行李箱,转头对着霍慑问,“听说协会给你招了志愿者,谁啊?我认识吗?”
霍慑踢了他一脚,苏崇躲着跳到一边。
霍慑弯腰打开行李箱,终于屈尊降贵地开口道:“你不认识,是个新人,”但他转头又想到陈霰白进协会有一年半了,补了一句,“她没什么经验。”
那人听见霍慑在心里提了一个人名,他挠挠头,奇怪地问了出来:“陈霰白?”
“嘶,”霍慑手上动作停了下来,“苏崇,你怎么什么都听?”
叫苏崇的心道不好,刚想跑但没来得及,被霍慑转身一把抓住,霍慑扣住他的腕关节,苏崇警惕地看着他,虽然心里慌得不行,但有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他现在是个“原能力者”,自己慌什么?
霍慑握着他手腕,控制力度攥了一下就松开了,苏崇腿一软没站稳,一屁股坐在地上,咂摸出似乎有哪里不对,他皱着眉仔细听了一会,小区楼下除草机的声音今天格外的吵,但整个房子里除了霍慑翻东西的声音,只剩他自己轰鸣一般的心跳声。
他有些震惊,等反应过来,嘴角不自觉地就提了起来,这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只是他听不见霍慑在想什么了。
这种情况在霍慑住院前经常发生。
他喘了两下匀平了气,盘膝坐好,盯着霍慑的后脑勺,想这狗人瞒着所有人这么久,也是胆大包天,于是手动把笑容复位,装模作样地气闷道:“还是您厉害。”
霍慑不睬他,把从行李箱拣出来的衣服递给他,苏崇抱着衣服站起来往阳台走,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被这个道德渣滓衬托得光辉无比:“我本来还想申请给你当志愿者的,但你不配。你是一个不配得到我们全体志愿者友情关怀的弟弟。”
霍慑想起在病房里要人命的花,心里啐了一口:“屁友情。”
很快阳台洗衣机“嗡嗡”的运行起来,苏崇锲而不舍地对他喊:“这回多久啊,我明天还得去协会。”
“晚上吧,你以为我恢复多少。”
自己搞不好是第一个发现霍慑能力恢复的,苏崇美滋滋地想。
霍慑住院半个月,阳台绿植阵亡一片,仅有两头蒜幸存。苏崇半跪在地上,指头在瓷砖上划过去,沾了一指头灰。
楼下绿化带里工作的除草机突然炸了一下,机器像磕到了什么硬物,发出一阵刺耳的卷刃声,苏崇奇怪地看过去,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其中有个园林工人似乎抬头望了他一眼。
他们俩人的视线刚隔空对上,那个工人就低下头,往树荫处退了几小步。
“他躲什么?”位置离得太远,就算霍慑没关他的能力,苏崇也听不到这个人在想什么。
能力用不上,他就忍不住原地盯着那个人多看了一会。
和其他工人一样,那个人也戴着顶帽子,他此时低着头,帽檐挡住了他的半张脸,苏崇见他个子不高,越看越像是个不好意思的孩子,估计偷看的时候被人发现,正窘得不行。
苏崇也不想为难他,便好心地收回了目光。
洗衣机适时地滴了几声,霍慑那个大爷在客厅催他晾衣服。
霍慑一到家像回了安全区,浑身筋被抽了个干净,软绵绵地现出了无赖原形,有事就招呼苏崇做,没事就闭着眼睛编几个事叫苏崇做。
恨不得未来半个月的家务也让苏崇包了。
苏崇后知后觉自己被人当工具人用了,他本来想着霍慑是个废人,他给帮帮忙就算了,谁能想到这个废人非但没有残废,搞不好养几天就要回协会报到了,顿时手一顿,看霍慑像看个诈骗犯。
霍慑以为苏崇不想干了:“不懂就问,人世间有你这么拖地的吗?”
听得苏崇想把拖把的海绵头塞他嘴里。
霍慑家里的清洁工具应有尽有,苏崇翻他储藏室的柜子发现,光是拖把头的替换,他就屯了四个颜色不一样的。
苏崇搞不懂这人明明这么喜欢做家务,为什么还来使唤他?
他洗完拖把,随手放在厕所窗台上晾,霍慑家没有装防盗网,外面看得一清二楚。
窗外夕阳西下,他临风捶了捶腰,风里传来别人家做饭的味道。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一天就差不多过去了,他难得一天放假,就被人骗来当苦力,真是无比充实的一天。
反正霍慑看不见他消极怠工,他索性打开了朋友圈刷了两下,胡不恤的朋友圈还停在上个月她拍的一张牛杂面。
看得他有些饿了,苏崇把手机塞回口袋,无意瞥了一眼,在路边看见顶眼熟的帽子。
是上午那个小孩。
工人们早就收工下班了,除草工作应该也已经结束很久了,久到苏崇想不起来,那些扰民的除草柴油机到底是什么时候停的。
修剪齐整的绿化带上,他一个小矮子孤零零地站着,抬头一动不动地望着霍慑家这个方向。
苏崇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那小孩看的差不多是客厅的窗户,霍慑此时正好在客厅溜达。
阳台朝南,厕所和客厅的窗户向北,等于这个小孩绕了一圈,饭都不吃,锲而不舍地盯着霍慑家这个目标。
霍慑家有什么好的,能叫人看出花来。苏崇冷着脸,躲在窗户侧面观察了他一会。
帽子下面他把工人擦汗用的毛巾包在脸上,哪怕他扬着头,苏崇也看不见他的五官。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上午他脸上分明还是什么都没有的,太阳大的时候不防晒,现在太阳都要下山了,他才裹着脸。
苏崇越想越觉得他可疑,他不禁有些阴谋论起来:是因为被他吓到过,所以特意遮了脸怕被人认出来吗?
那个帽子怪脸上只剩了双眼睛,现在还眯成了一条线,仿佛被光照得睁不开。
路的对面有个家长带着孩子在边上打羽毛球,一大一小姿势都很业余,但架不住风大,羽毛球在风里借力,在空中划成了一道线远远地落到绿化带里,小孩高高兴兴地跑去捡,帽子怪见有人朝自己跑过来,压着帽子往旁边让了两步,他这么一动苏崇终于看出来了,他哪是什么小个子的“孩子”,明明就是个驼背。
不知道他是故意装的,还是先天性的佝偻病,反正现在缩着肩,脖子僵直地向前倾,活像个王八。
过来捡球的小孩拿到球也不急着走,十分不怕生地站着看了看他,又转头看了看霍慑家的方向,脆生生地童音问他:“叔叔,你在看什么呀?”
帽子怪果然年纪不小了,苏崇第一次对祖国的花朵产生感激的心情。
那人没理小孩,快步从绿化带上走下来,站路边贼心不死地朝霍慑家连看了两眼,扶着帽子匆匆走了。
晚上,苏崇打扫完卫生,去社区超市逛了一圈,没买到牛杂,买了两斤牛肉回来,煮了两碗牛肉面。
霍慑吃完在沙发上坐了一会,终于良心发现,决定去帮苏崇洗洗碗。
苏崇冲掉海碗里的泡沫,冷不丁地背对着他说:“霍慑,今天有个人一直盯着你家看。”
霍慑发现苏崇已经快洗完了,刚想走,听见这句又停住了:“什么时候?”
“我去晾衣服的时候,”苏崇关上水龙头,“还有洗拖把的时候,他也没走。”
霍慑以为是陈霰白,问他:“男的女的?”
苏崇少有的正色道:“男的,前几天都没有,你今天出院,我才看见他。混在园林工人里头,裹得像个神经病,要我跟协会说一声吗?”
霍慑看着苏崇的表情,不由得想到了陈霰白做的噩梦,沉吟了一会说:“没必要,我这几天不出门。”
苏崇看着他甩了甩手上的水,不置可否。
他想到苏崇也是好心,又干巴巴地补了一句:“下次你再看见,觉得不舒服就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