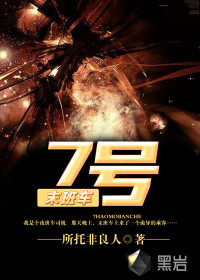第十六章 来人
天上长风如流,乱把白云揉碎。
透过乱流看过去,天上的阳光被扭曲了,显出一种虚幻而模糊的日晕,让举头望日的人们不自觉就眯缝了双眼。
螺旋桨带起的磅礴风压过境,吹散了酒德亚纪的发髻,几缕青丝拂过站在她身旁的叶胜脸庞。
叶胜皱眉感受着这风声片刻,往前踱出一步侧身挡在了酒德亚纪面前,又伸手帮她把发丝重新挽到耳后。
放在以前这动作总会显出几分暧昧的绮旎,但现在他们二人都已经没精力从这种细枝末节去品味双向奔赴的甜蜜了。
因为兵临城下,万马齐喑。
仿佛有盛大的战争就要在下一刻打响。
这是丽晶酒店最顶层的天台,在施耐德的指挥下,一刻钟之前卡塞尔学院所有在职人员备份上传完毕资料后,连同被许白帝打伤的全部伤员都撤离到了这里。
如果这是一场面对杀手屠夫的大逃杀游戏,那其实这样不管不顾地蒙头往上逃窜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因为最后坠在后头的死亡总会追赶上来,而自己却已经坐困愁城无处可逃。
除非像古德里安教授所期盼的那样,真的有黑鹰直升机从天上降下救命的软梯。
——真的有直升机从天而降。
但踏着狂风从直升机上走下来的,并非来自秘党执行部统一的制式风衣,而是全身笼在一袭黑袍中的奉剑侍者。
他们沉默地排成一排,手捧的每一具剑匣都是半开的,匣中满是切切的锋锐之意,隔着丈许远的距离依旧让观者肌肤生寒,仿佛能够听到炼金古剑在悠长地呼吸轻吟。
面对不速之客,此时空旷天台上所有人都看向被自发簇拥在正中央的三位教授,他们脸上的表情各有不同。
刻在曼施坦因教授面孔上的神情一如既往的深沉严肃,他的视线从左到右依次在雕花镂刻的剑匣上掠过,仿佛一把冰冷而严苛的戒尺正在挑选足让自己正视的对手。
只有古德里安教授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依旧频频往施耐德脸上瞟去,眉宇间透露的都是感觉自己先前说对了的自得之意。
如果酒德亚纪看过那部经典港片《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那古德里安此时脸上表情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是:“施耐德你还说你没准备逃跑用的直升机?”
又或者“我一进来就看见施耐德在喊直升机快点来。”
施耐德面沉如水没有说话,他隐没在面具下的真容让人看不真切,铁灰色的瞳中同样宛若结上了一层云翳,所有近乎于“人”的情绪都被封锁了,但周身浮动的低气压很明显地表达了他某种如同生铁般的决意。
这种决意并非关于生死,而是代表着两尊并立庞然大物的意志冲突。
“你们坏规矩了。”长久的对峙与沉默后,施耐德推着氧气瓶小车越过众人走出,“1972年2月,我们双方曾经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签署了互助协议,协议当中就有关于卡塞尔学院在这个国家招生与设立安全观测机构的条例达成了一致。”
“确实,我记得协议内容规定,从属秘党的卡塞尔学院有权在任何地方吸纳任何具有自由意志的学员。”
一连串的轻声咳嗽后,拄着拐杖的老人最后走下了直升飞机,梧桐木制成的拐杖敲击在水泥地面上发出“笃笃”的闷响。
缓慢踱步的他站在施耐德面前半米处立住:“当年我们还用炸酱面、涮羊肉和北京烤鸭招待了你们。弗拉梅尔先生打趣说,给他一瓶茅台酒,他愿意在任何协议上签字。”
头发已经花白斑驳的中山装老人说到这里似乎回忆起了某些往事,于是微笑起来:“但太久远了,那个年代路上跑着的还是永久、飞鸽以及凤凰牌的二八大杠,车头上的银色铃铛在大街小巷叮叮当当地响。骑上自行车座位之前,人们往往需要推着车先小跑几步,一脚踩在踏板上一脚连着蹬地,然后借着惯性姿势漂亮地跨上座椅。
当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是大城市人家嫁娶时才有能力准备的三件套。我也是个年富力强的精神小伙,每天从床上蹦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一边等候着广播里女主持人用她温柔的嗓音播报昨天的新闻,一边嚯嚯磨着牛角刀准备把今天派发到我手上的死侍剥皮拆骨,脑袋里想着的不是接下来应该怎么下刀,而是我什么时候能搞到那套票据去娶街对面的小芳呢?”
随着老人平缓的讲述,酒德亚纪怔愣住了,好像自己的灵魂轻轻飘离了二十一世纪星级酒店的天台。
整个异国他乡七十年代的景象扑面而来,空气里弥漫的是柴火土灶的气息,身旁站着正把污水泼到门口石板上的街坊,骑着自行车远去的行人一边抬起双脚试图躲避飞溅的污水,一边操着京片子骂骂咧咧。
“过界了。”曼施坦因教授的声音打断了这种幻觉,于是画面片片破碎凋零,最后一声自行车的铃铛声远去了。
酒德亚纪悚然从幻境中惊醒。
“你们过界了。”曼施坦因咬字极重地重复了一遍,“所以你们是准备要单方面撕毁《长城协议》吗?”
类似护犊的愤怒在这位秃顶老人并不高大的身躯中升起,他直视着来人,黄金瞳点燃摇曳。
“怎么会呢?那一年你们秘党得到了我们提供的资料,终于成功补全制定了言灵序列表。而我们从与你们的交流学习学到了更加先进的炼金技术。这是很经典的双赢案例。”
“但你们的招生范围从一开始就并不包括世家门阀的血脉后裔。”拄杖老人风轻云淡地回答,“所以彼此彼此。”
三十多年前的秘辛在昭昭天光下被揭开了,所有足够幸运去聆听这一段尘封历史的人们都屏息凝神不敢有任何动作。
“我还以为这项条款的重点应该落在‘自由意志’四个字上。”施耐德冷冷地嘶声回答。
“可是小孩子又怎么会懂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老人摊开了手掌,“常言道,听人劝吃饱饭。我们无非希望他听长辈的一句劝告而已。”
曼施坦因回话了,语气里是直白的讥讽:“长辈?难道你们会承认一位从来没有祭拜过你们祠堂的族人?”
“如果是别人,当然不会。但他的名字是许朝歌。”老人点了点头坦然接受了这种质疑与讽刺。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种穷小伙买彩票中了五百万,于是远亲近邻纷纷觍着脸上来拉关系的趋炎附势之感,但现实就是如此。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篇用于给儿童启蒙发智的文章,叫《昔时贤文》。文章写的辛辣也正确,里面有一句是‘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是这么回事。”
“那还真是‘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你们放养了他接近十六年,现在才出现,这哪里是走亲戚攀关系?这是孩子成才之后,弃养的生母突然出现明争强抢的社会伦理剧情啊。”曼施坦因教授鼓掌并冷笑,“还有,弗拉梅尔其实不太爱喝白酒,也许那句话算是他这辈子的情商巅峰了。”
他特意把巴掌拍得大力又响亮,“啪啪”的声响在天台上回荡,就好像是在抽着对方的耳光。
“比起祭拜你们的祖庙祠堂,他已经先一步签下了秘党的亚伯拉罕血契,他的入学学号都已经生成完毕了。”施耐德挥了挥手,叶胜走上前躬身递上了一份签名契约。
老人没有浪费一眼去看那些字母和签名,他抬起拐杖把那份契约轻轻压落到地上:“入学学号?那这孩子的姓氏与生俱来。何况这玩意只在你们的所罗门法庭有效,但我们遵从的是宗族戒律。原始的、不被现代文明接受的、但和你们无关的宗族戒律。况且即便你们有亚伯拉罕血契,但他名字叫许朝歌,从出生时就叫许朝歌。”
“你们的自谦听起来还真让人措手不及,严格意义上来说除了古埃及王朝比你们更久远。在蒸汽时代前,你们的文明可是一直凌驾全世界之上长达两千余年。”
曼施坦因俯身捡起契约文书拍去了纸上的灰尘,“所以说这是楚王兴兵伐随吗?那时候两国交战还讲究师出有名,于是随国辩解说‘我无罪’,但荆楚之地的泱泱大国居然自谦称‘我蛮夷也’。”
“说笑而已,如果我们是真的蛮夷,那么匣中宝剑应该已经出鞘了。”
楼道中传来轰鸣,好像天声震落。老人视线低垂,落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好像能透过层层阻隔看到丽晶酒店中正上演的画面。
“我很疑惑一个问题。其实你们没必要来这的。”施耐德向老人问道,“如果那女孩打赢了许朝歌,她自然会把许朝歌带走,我们没人能阻拦。但如果许朝歌赢了,我不认为你们这些黑袍剑侍又能拦下他。”
“放心,不把混血种世界展示在普通人面前同样是我们的守则。”老人满不在乎地笑了:“所以剑侍是用来撑场面而已。此行的目的只是想和那孩子见一面好好聊聊。”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打算用武力把许朝歌绑回去?”站在一旁看戏的古德里安教授突然明白了,他右手攥拳敲在自己左手手掌上,好像脑袋上陡然亮起了一盏代表智慧的金光灯泡。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问问许朝歌他自己怎么想的呢?”古德里安建议道,“他固然没有在你们大家族中长大,但他和我们接触时间同样不超过一个小时。”
“早该如此。”老人双手撑在拐杖龙头上露出微笑。
施耐德和曼施坦因对视了一眼同样点了点头。
角落里半躺在担架上的楚子航脸色苍白看不出喜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