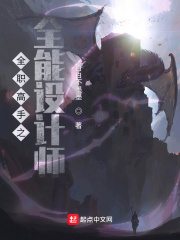一个个的浪头砸在我的头上,我有点怀疑自己到底是被水呛醒的、还是被犹如斧凿般的海浪敲击而醒。
层层叠叠的浪头卷起的雪白浪花,像顽皮的孩子贪婪地舔着平滑的沙滩;又慢慢地退去,像羞怯的少女轻轻拉动拖地的长裙。
嘴里满是沙泥,每当我向咬着牙往沙滩方向挪动时,牙齿和沙子总会发出一连串令人不舒服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比起我身上的伤,又算得了什么呢?
海水的浸泡令我全身有些麻木,但这对我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反正也不是头一回了,九年来比这更惨烈的处境我也经历过,自然明白这只是身体的自然反应。
我努力在海水里揉搓着自己的手脚,舌头反复来回抵住牙床,好让自己的意识尽快复原,可当我真正躺在沙滩上翻看着伤势时,却惊奇的发现自己居然仍旧全须全尾的活着,无论秃子在我手腕上留下的勒痕、还是那么冒充我的人对我头部的撞击,竟然丝毫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是皮肤以下的血脉再次呈现出那种熟悉的海蓝色,而皮肉也异常的透明。
比这更不对劲的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根本不是昨天被打晕时的所在。
你二大爷个孙子的!
心头一阵怒骂,可惜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把这些话吼出来。
“今天,这就是你的报应,你就在去你说的那个阎王殿里,好好的琢磨琢磨我是谁吧!”
我的耳畔始终回绕着那个假扮我的人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脑袋有点浑浊,不知道是不是海水喝多了的缘故,是的,我可以不去想这个人到底是谁,或者说,我明明知道那是谁,却不愿想起她。
唯一搞不懂的是,在这个连胶水都没有的原始荒岛上,她是如何做到易容我易容得如此惟妙惟肖。
海边是沙滩,沙子金黄金黄的,趴上去又松又软,就像踩在一套羊毛地毯上,这样的歇息足足维持了半个多小时,直到自己的嘴角唾液停止了向沙面的垂淌,我才用胳膊努力撑着身体翻了个身。
天蓝得像一张蓝纸,几片薄薄的白云,像被阳光晒化了似的,随风缓缓浮游着。
他们一定以为我是死了,随后把我拖到了某处崖面抛入了海中,这样的毁尸灭迹其实并不高明,假如是我......好吧,我知道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或者说、以前的我做不出这样的事。
不得不说,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命大,那人手中的石头对我的每一击都那么致命,我却没有死,只是暂时的昏厥,这才让他们做了错误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当我恢复了些许体力检视周围的时候,我却猛然发现自己兜兜转转的竟然又飘回了熟悉的那座岛,是的,没有人比我更对这里熟悉,还记得吗,在九年前我初登这座孤岛时、醒来的我不就是落难到了这片海滩?那几排密叠林里一棵酷似榕树的巨木、曾经让我挨过了孤独的第一个夜晚。
但现在的这些对我来说却绝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
几乎在一个激灵之间,身体便已滚翻到一处矮灌木的侧面,冗杂的灌木栀将我的身体包裹得完完整整,是的,我必须这么做,因为这里距离缓坡太近了,尽管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但哪怕只是一晚,我也毫不怀疑那个伪装成我的人已经接管了我的部落,甚至现在已经在屠杀包括川妹子和岐女在内的很多人。
一种莫名的悲伤感让心头顿时一酸。
九年,九年所建造出来的一切很可能就这样拱手于人,最令我接受不了的是,企图杀我的人竟会是秃子,而另一个人......我不想回忆那个女人,事实上她说的没错,我的确太心软,早在她在那魔鬼一样的密林中对我显露出第一次叛乱苗头时,我就该亲手宰了她!
我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她是最早跟随我的人,并且,她是个人!
直到我搞明白自己所处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让自己再回到那个文明社会时,我才把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军人原则抛到一边,什么反人类罪、什么国际法公约,什么人人平等,当我知道再不会有任何一个军事法庭会约束自己的时候,我才活回了自己原本的样子,只是有点晚罢了。
双眼死死盯着榕树林里的动静,我很期盼那里能出来个人,也好能让我一袭之下打探出现在部落的情况,但我又确实不太想出现这么个人,因为我的实力未必能neng得过冒出来的活人.......
在灌木里这一蹲、直至天色擦黑我也没见着有人出来,倒是一只寄居蟹拖着它那小房子又灌木前优哉游哉的经过,我很羡慕它,它有家,有个自己想回就能回去的地方。
海上的夜色降得很快,极目千里,海天浑然,阴云在静静疾走,浪在无声奔流,似能感到地球、天体的运动;似能跳到早已消逝在地平线外面的过去年代的人、物。绰绰约约,虚渺飘忽,历历在目。
口渴得厉害,我拎起一棵蕨类根茎就嘬了两口,甘甜的适感由喉头润到了胃里,自己也不免摇着头苦笑。
还记得吗?九年前的我第一天到这座岛时,自己也是同样的境遇,而那时的我全然不懂这些生存的技能,像条狗一样趴在死水坑里吸溜了半天,直接导致腹泻了十五天,险些一命归西。
习惯性的拔出腰间的匕首,切了两片软蕨草塞进了嘴里,这东西不仅仅能解饿,还能提供些我必要的盐分。
突然,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令自己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匕首?”
我下意识的往腰里摸去,一摸之下自己一屁股呆愣愣的坐在了灌木丛里,任由荆棘此刺扎着我的身体。
我的腰上居然缠着一条皮带,皮带之上竟稳稳挂着那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匕首套。
可这些不都在九年前随着潮汐飘向大海了吗?
更令我毛骨悚然的是,当我发现自己穿的并不是灰色工作服,尽管天色暗得看不清衣服的颜色,但由兜的位置判断,这是军装,是九年前我初登小岛时的那身四兜军装!
我闭着眼睛让自己清醒了清醒,随即“啪”的一声抽了自己一个大耳光。
疼!
这不是梦,更加让我确信这不是梦的,是我在裤兜中摸出了那盒九年前就已被我吃完的“中华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