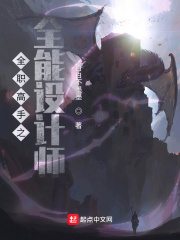迷迷糊糊中,我似乎感觉身下软绵绵的,睁眼一看,却发现我躺在家里自己的床上,身上穿着一件不知道什么时候的破军装,腰上缠着武装带,那武装带扎得紧紧的,勒得我有些喘不上气来。
我的右手垂在床边儿,可能是睡觉压的,丝毫不听使唤,就那样垂着。
房门突然打开,是妈妈,她老人家端着一碗炸酱面,眼神中充满了怜爱的看着我说:“早就该回来,跑去当什么兵!看把你累的,赶紧起来,把面吃了,这麦子是你爸种的,我给和成了面条,你尝尝”。
我突然感觉自己轻飘飘的,接过了老娘手里的面条,就着一堆面码儿(各式青菜,炸酱面必备)就这样啃嚼起来。
等再一抬头,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到了我的床边,那如刀削的脸孔上仍然写着“严肃、认真、奋发、图强、强军、崛起”这十个大字,他轻轻地抬起右手,像抚摸兔子一样抚摸着我的脑袋,而左手却从军装里掏出了一瓶地道的北京二锅头,只淡淡说了一句:“知道你想家,想家就回来,别在外面飘了”。
我能感觉到两股热流由眼中涌出,我看着父亲,他老了很多,原本乌黑的短发,现今已夹杂着几许灰色,突然想起,突然想起,我似乎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如此仔细的看过他。
结果他的二锅头,一口就把酒吞进了肚子里,那酒是咸的,就像海水一样的苦咸味,十分难喝。
我猛烈的咳嗽着,像是被这酒呛得连肺子也要吐出来的样子。耳畔突然传来海水敲打船板的声音,而父亲的声音却渐渐淡去,母亲的面容也越来越模糊。
刺眼的阳光终于替代家中柔顺的灯管照进了我的瞳孔,我似乎明白过来这是一个梦,一个美梦,我试着想让自己再睡过去,哪怕是一会儿也好,让我再多看一眼妈妈,以及那个我曾经憎恨的爸爸。
我的身子仍然泡在海水里,借着太阳的暖意,那海水已经不再冰冷,右手像断了一样毫无知觉的在海水里耷拉着,而我的左手却像是钩子一样仍然死死的挂在那坨兔皮沙袋的绳子上,手指已完全没有知觉,只有手腕能传来一种脱臼后麻木的感觉。
正史因为左手仍能挂在一个着力点上,才不至于让已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我大头朝下的沉浸在海面以下憋死。
海面的风早已停息,看太阳的高度,至少也已经不清晨,但也不再是昨天,因为,那不是夕阳,炙热的光线令我明白,昨夜的暴风雨已经过去,缓缓的微风才是现在海面上的旋律。
左臂已经酸麻、右臂完全指望不上,我努力的踩着水,这样似乎能让胳膊缓一缓力,让血液循环慢慢正常过来,但,我太累了,小腿在不住的哆嗦,继而转为抽筋儿,几次都险些让我垂直着沉进海里。
我试着让左腿由海里抬出海面,挂在另外一个兔皮沙袋上,但这太吃力了,我完全做不到,只好用刚刚缓了些血脉的左臂勾住沙袋,用身体的重量向下重重一压,借着独木船向左稍稍倾斜的那一瞬间,才猛的将左腿挂在预想的那个沙袋上,而后手脚并用,滚进了至少一半海水的小座舱。
我就这样坐在座舱的船底板上,屁股下面是已经被撞翻的那个木凳,很坚硬,顶得我盆骨传来阵阵刺痛,我又向旁边挪了挪,折让船里的积水直接淹过了我的胸口。
再无半点力气改变什么,就这样有气无力的坐着,任由荡漾的积水拍打着我的胸膛,有时还会钻进几滴偷偷流入我的嘴巴,我只想坐着,天底下还有比现今这个姿势更舒服的吗?
至少又是半个小时过去,直至我能感觉到左手手指传来像针扎一样的刺痛,我才用手肘支撑着船板站了起来,旋即又差点晕回积水里。
我的左手手指的指甲脱落了三个,右手手臂上有着非常明显的螺旋形勒痕,那一定是救生绳缠绕的结果,我几乎断定我的右臂就此废了,毕竟勒得太久太久,但这丢卒保车的做法,也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事情,丢了右胳膊重要还是丢了命重要?我相信答案非常清楚。
许是光线的作用,我发现我的皮肤,又一次呈现出了四年前的样子,稍稍有些透明,甚至比上一次更加的严重,我似乎能看见手臂下青色的血管里包裹着的血浆,在随着心脏的跳动而有节奏的涌动,不仅仅左臂,连同右臂也是一样,我试着咬了咬左臂的皮肤,却发现并无其他异样的感觉,只是皮肤变得透明了许多。
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四年前也发生过相同的事,还记得吗?在郑和号海难后,我泡在海里不知过了多久,最终被冲上了海滩,那时的我,手臂不就呈现出了透明状?现今也是,难道,我这皮肤得了什么怪病?
低头借着积水的反光在水面上仔细的看了看自己的脸,却发现脸上一往如初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被海水泡得过久,显得非常苍白,这让我还算欣慰不少。
右手臂伴随着血液的涌动,似乎也在慢慢的恢复着知觉,我内心中默念着:“谢天谢地,我终于再一次的挺了过来,而且,是全须全影儿的挺了过来!”
很久后,尽管浑身仍然虚弱,我却不得不赶紧将仓里的积水排干,这积水我尝了一口,是咸的,很显然是雨水混杂着昨天进入仓里的海水的混合物,这不能喝,假如,我所携带的淡水全都在昨晚的暴风雨中消耗殆尽,那么我确定仍然活不过四十八小时,现在的我身体严重缺水,海水的腐蚀抽走了我体内大量的水分,仅仅是由于浸泡才没有让我产生口渴至极的幻觉而已,刚刚起身的晕厥足以证明这一点。
左手伸进积水里,在水下焦急的摸索着,摸索昨晚我曾拼命护住的那一个装有淡水的陶罐,祈祷着它千万别也像其他罐子那样的悲惨命运,幸运的是,我在仓位的一个夹角找到了它,尽管它旁边还有几个破碎的罐子渣儿刺痛了我那没有手指甲的嫩肉,但我还是找到了它!
一口比泉水还甘甜的淡水灌入了嘴里,我不敢多喝,担心五脏会承受不了这份水压,转身将罐子放在船头,再捞起半个烂罐子开始了清除积水的工作。
我是幸运的,在积水清理工作大致结束后发现,我的淡水虽然损失了一大半,但仍然剩下了两罐之多,装肉干的罐子碎的最多,但好在还有几包是我包进塑料布里塞在装放鸟铳的那个沟槽里的,至今仍然死死的卡在那里,连同它一起卡在那里的,还有我的鸟铳和那些同样包裹及其严实的火药和铅弹。
损失最大的,看来是我的身体和补给,但,经历过昨夜的灾难般洗礼,我真的变得虔诚,无论是安慰自己也好还是真的一心皈依,我开始思考思考“这是佛祖、上帝、基督或者老天爷他们给予我的惩罚,体罚是其中的一部分,让我经历饥饿和口渴,用以加深惩罚的力度”。
越是这样想,便越能给予自己希望,毕竟,眼前无边无际的大海,除了身边海水敲击船舷的声音外,我什么也听不到,甚至,我连只海鸟都看不见,这块大海还是感觉深沉得有些让人透不过气来,极目千里,海天浑然,云在静静疾走,浪在无声奔流,似能感到地球、天体的运动;唯独感不到的,便是我能活下去的希望。
我坐在座舱里沉沉的睡了过去,太累了,甚至没有力气竖起桅杆和船帆,事实上,那颗椰子树也在昨天的暴风雨中遇难而不知所踪,仅仅留下了塞在船头夹缝里的那个小三角帆,但失去了桅杆,这帆又能有什么用呢?
再次醒来,天色却已入夜,我极力的揉眼睛,企图让瞳孔聚焦一些,但却发现丝毫不起作用,我在天空找不到任何一点点月光,哪怕是星星,我也找不到半颗。
用力的揉了揉自己的脸,确定自己并不是在做梦,那,这又是怎么了呢?
我确定自己没有失明,事实上我能看到海底一些浮游生物自己发出的微弱光亮,只是那天空,再也找不到一丝天体的痕迹,像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宇宙大爆炸将一切化为虚无,而仅仅剩下地球上这些生灵。
不再对这些似有似无的未知感兴趣,也早就失去了探求的动力,我现在最大的期望,只是能活下来,即便是我的小岛,我都不再奢望能回去。
半梦半醒之间,突然一阵极具的撞动令我的头重重的碰在了座舱木板上,这撞动大极了,像是独木船撞到了一处铁板一样,幸好他独木的材质,假如是普通的木板拼合船只,这一撞的威力足够它沉上七八次。
纵然如此,船仍然连续摇晃了数次才稍稍稳定了些。
怀着激动的心情由座舱站了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是有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