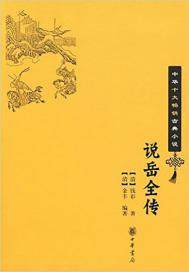荀钰扬眉,眼底平和:“好。”
前些他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小匣子,岑黛心里没来由地有些高兴,弯起唇角:“师兄嘴里还苦不苦?”
荀钰不动声色地朝外间瞥了一眼,眸光闪了闪,转头乖顺道:“苦。”
隔着一扇半开的门扉,做贼心虚的何妈妈忙拍着胸口舒气,一双眼睛却笑弯了起来,同身旁的妇人小声笑道:“在过往的多少年里,家中众人何曾见过大公子这般亲近人的模样?”
邢氏也随之松了口气,多看了岑黛一眼,转身轻手轻脚地往外走:“他们这小两口,自有自己的一套相处方式。以后遇上什么事,何妈妈需得问过少夫人了,再来告知主院这边儿,莫要让新妇觉着自己在家里是外人。”
何妈妈明白了邢氏的深意,福身行礼:“老奴记下了。”
荀家内里被荀钰这一回的风寒给吓得够呛,毕竟对于如今的荀家人来说,他可是最大的顶梁柱,一出事家中所有人都紧张。
幸而荀钰在晌午时分便醒了,加之荀阁老从始至终都未曾发话,家中众人心里有了一定的底气,不至于慌了手脚,于是便不曾多探听风来堂的消息,岑黛这边自然也随之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压力。
至于朝堂上的动静,岑黛今日可收到了卫祁的多封消息。
一向勤勉有加的内阁首辅今日未能上朝,一群朝臣可都在眼巴巴地盯着荀家的动静。
得知荀钰这回是染了风寒,好些官员心中都在窃喜。心说璟帝这才刚打算进行清洗的大动作,荀钰这把利剑便用不趁手了起来,平白给大家增添了许多笑料。
只可惜一群人还未笑完,立刻便笑不出来了。
荀钰前些日子的勤勉没有白费,一应紧迫的动作他早已经安排完毕。内阁今日依旧是在照计划呈递审核举报,由太子杨承君领大理寺众人查办了许多户籍田地,招招都是在往庄家的亲信上打,直将正打算看好戏的众人给打懵了头。
书房之内,岑黛看完信笺时,心里只想笑,同冬葵笑说:“师兄与表兄在文华殿中的那一年相处,可不是白费。老师费心教导他们君臣之道,虽无意揭开了两人之间潜在的矛盾,可也教会了他们携手对敌的本领。”
她烧了信笺,心里暖洋洋的:“一个是利刃,一个擅用利刃。尽管师兄与表兄之间隐有争锋,但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二人是相辅相成的。”
冬葵抿着嘴笑:“婢子瞧着姑爷与太子殿下的立场始终是一致的,在这等大事件上,哪里真的能有什么矛盾?”
岑黛却逐渐收了笑。
她想起了前世在朝堂上,位高权重城府深沉的荀首辅与太子杨承君两党分庭抗礼、水火不容……
“话可不能说满。”
岑黛垂下眼,低声道:“现在是舅舅施展手段的最初阶段,师兄和表兄采取的打算相同,都是以根除为主,二人想法相似,自然就不会有任何分歧。”
“可往后,若是遇上有争议的大决断,这两人的立场却未必还能够保持一致……”
她皱了皱眉,转头看向冬葵,沉声问:“庄家这回可失了好些根茎,荣国公府那边还没有任何动作么?”
冬葵垂首:“荣国公府依旧未尝做出任何回应……长公主殿下这些时日始终在盯着国公府的动作,也不曾发觉出任何异样。岑家这些年过分低调,目前也仅仅知晓他们与庄家暗有勾结。除此之外,整座国公府几乎如铁桶一般,一点缺口都不曾暴露出来。”
她顿了顿,抬眸迟疑道:“甚至,荣国公近日爱上了听戏,还专门请了梨园的戏班子在府中搭台。长公主殿下暗地里调查了一番,依旧未尝发现任何不妥之处。”
岑黛拧紧了眉,终究是叹了口气:“老狐狸既然还打算装疯卖傻,定然是还在等待时机。况且他这般坦然,保不齐一应准备早就已经铺垫好了。”
冬葵微愕:“可自天盛楼一事后,陛下与长公主殿下就已经在暗暗提防岑家,国公府哪里来的时间去准备好所有事宜?”
“要么是在更早之前就做好了准备,”岑黛蹙眉沉吟:“要么,就是荣国公的那番准备根本不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
然而形势是瞬息万变的,没有人能够保证可以提前猜想到所有细节,更没有人能保证他的准备能够如计划一般派上该有的用场。一点儿小小的变化,都可能导致整场计划的崩盘。
如若荣国公果真是提前做好了所有准备,中间出了这么多意料之外的变故——皇族的警惕、岑骆舟的背后捅刀、老太君身死——难道他的计划还能够如常发挥作用?
岑黛觉着这种可能性很小。
那么便只剩下第二种猜想:荣国公的打算不需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无论何时都能进行,唯独只需要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岑黛揉了揉眉心:“这能是什么法子?”
冬葵提醒道:“郡主出来得有些时候了,姑爷那边还在等着您呢。”
岑黛舒了口气,取了荀钰书桌上的布帛文册,又命冬葵抱了文房四宝,准备回去暖阁。
——
何妈妈端了汤药进来,瞧着荀钰裹了鸦青大麾,正在审阅今日内阁传进来的消息,温声嘱咐:“这秋雨一下,想来往后京中就要大降温,公子尚在病中,该添衣了。”
荀钰抬眸瞥了那碗黑乎乎的东西一眼,隐晦地蹙眉,淡声:“我记下了。”
何妈妈早已习惯了他的性子,搁下姜汤便打算离去,却听身后荀钰突然唤了一声:“何妈妈。”
他抬起头,眼中无情无绪:“你是母亲留给我的婆子,不是她的眼线。既来了风来堂,往后做什么事,总得问过了这院里的主子。我是这院子里的主人,少夫人也是。”
何妈妈心下一凛,知道他说的是今儿早上在门外偷看的那码子事。
彼时他初初清醒,岑黛忙着喂药,可没时间告知家中其他人,可邢氏却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必定是得了谁的消息。纵然邢氏那时未曾出面,可他到底还是发觉了异动。
岑黛将将掌家不久,又是个不争不抢的性子。身边有婆母的线人,她心下或许并不会因此而觉得不舒坦,可荀钰却替她生了气:在院子里做主的女主人,有一个便够了。
何妈妈躬身行礼:“大公子放心,老奴再不会擅作主张了。”
仅仅一日,就得了邢氏和荀钰这母子俩各一次的警告,何妈妈在心里苦笑,知道这回是一时脑热办错了事。
纵然岑黛手生,掌家的本事也并不突出,可这家里的人却各个对她上心得很。新妇才刚刚嫁进来,一家人就立刻放了权,将界限划得明明白白。
岑黛进屋来时,何妈妈早已经离开了,暖阁里只剩下青年还在审阅手里的信笺。
他未戴金玉发冠,嘴唇还有些苍白,显得整个人更加年轻单薄。可他仅仅只是坐在那,一身的气势却足够惊得所有人放下心中的轻视。
岑黛站在原地,定定地看了几眼,发觉如今的荀钰,已经愈发有了梦中那位荀首辅的样子了。不可忽视的气势、锐利的目光……这是大越的内阁首辅。
荀钰抬眼看过来,眉目舒展开:“站着干什么?”
他表情未变,可浑身的气势却是软了下来。
岑黛眼里带笑,将手里的册子递过去:“师兄要的文书,看看少没少些什么?”
荀钰随意看了眼:“不缺。”
他见着小姑娘空出双手,将一旁矮桌上的姜汤端给她。
岑黛笑脸一僵,暗暗咬牙:“都过了这么久了,师兄的手难道还麻么?”
荀钰面色如常:“不麻,但是我要捏着鼻子才能喝下去。”
“那可真不巧,刚刚给师兄取册子,宓阳的手麻了。”岑黛皮笑肉不笑的:“师兄的两只手都健在,就不能一手捏鼻子一手端着药地喝下去么?”
荀钰直直看着她,哑声道:“雀儿乖。”
岑黛心里一跳,顿时泄了气,干巴巴道:“我喂。”
她只觉得荀钰抓住了自己的命脉。自从归宁那日他说了句“掌心雀”,往后她就觉得雀儿这称呼充满了亲昵和占有欲,一听就要脸红心慌。
冬葵在一旁忍着笑,心想自家郡主撒娇了这么多年、皇族多少长辈对她要星星给月亮的,却是第一回对别人的撒娇招架不住,果真是一物降一物。
——
荣国公府中,荣国公听完了今日的戏曲儿,笑眯眯地回到书房理事。
岑远道坐在书房中写字,瞧着他进屋来了,道:“今日庄家托人捎带了消息,问及何时动手。”
他住了笔:“这回庄家受了很一番打压,他们是百年的书香世家,虽因人脉在京中盘根错节、不至于伤及根基,但终究是吃了一回大苦头。京中其他的老狐狸尚且还在观望,想要看清璟帝下一步的准备再开始动作。”
荣国公只笑:“急什么?时候未到。”
他坐下来,懒散地揉了揉脖子,笑道:“对方是那等庞然大物,咱们岂能与他们硬碰硬?想要赢,就必须得等到能够一击致命的时机。”
“一击下去,若是杨家和荀家垮不了,那么死的可就得是我们这一帮子人了。”
荣国公始终都是轻松的语气:“至于庄家么……出出血也好,免得到了最后,咱们岑家还得让他们那群贪心的家伙填饱肚子。”
岑远道皱眉看着兄长。
荣国公睨他一眼:“权力才能给予我们安心,但权力是有限的,庄家多咬一口,我们就得少咬一口。”
“远道切记,人心是用来利用和针对的,可不能施以信任。”
岑远道终于开了口:“二哥就不怕庄家反咬我们?”
荣国公低低的笑出来:“他还能有什么路可以走?他那贪婪的本性已经被璟帝看了个分明,不可能再有退路,他只能咬牙往前横冲直撞。”
他含笑看向三弟:“远道,好好的一台戏摆在眼前,咱们何必要去插足其中?杨家和庄家的争斗,我们岑家暂且只需要坐下看戏便够了。”
岑远道愕然,这才知晓荣国公早年与庄家的勾连,不过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挡枪的护盾罢了。
他从没想过要与谁联手下棋,只是因为百年庄家的底蕴够深,经得起璟帝长时间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