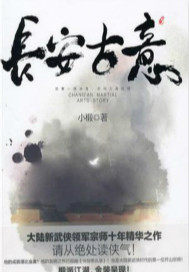那日的余果老头笑完了就是大咳。他果然老了——裴红棂一叹——但他也还好小,有一种人,心里有一处地方,几乎是永永远远长不大的。
就象余果老现在的大咳一样,他正坐在车辕上,人显得瘦瘦小小,一头白发在风中萧然散乱。他蜷着一条腿、因为风湿;他的眼也混浊了,这时头正一点一点地打着嘻睡。
还是二炳赶车,车行在临潼以东十五里的地方,再往前就是潼关了,那是个险要所在。
车上还插着一把旧旧的镖旗,旗上写了四个字:“威正镖局”。和那字体的飞扬虬劲相反,护镖的老人未免显得荒凉可笑。
这是一个人的镖局。
局主,总镖头,镖师,趟子手,都是他一个人。可“威正镖局”二十五年前还号称“天下第一镖”。
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只剩下一个衰年老者独撑着这面旧旗?
裴红棂看着车两旁的山势,越来越险,可能是为了逃避“五牲刹”,余老人未过潼关,而是岔上了一条荒僻小路。车每一刻都在左摇右晃,和裴红棂此刻的心绪一样。
记得昨天,她还问过:“五牲刹是什么人?”
余果老收起他那把大关刀,轻咳道:“他们是东密的人。”
“东密也就是密宗东支,自汉代传入,这近二十年他们发展极快,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真正的内幕,如果说还有人知情,那尊夫可能算是唯一的一个了。”
“我听说肖御使这十年来一直就在追查东密的事,至于详情如何,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似乎他们和朝廷上有一股势力暗相勾结已久,其中大有阴谋。也听说东密早已恨肖御使入骨,为什么一直没有暗杀他,倒也颇令我奇怪。据说,东密是顾忌一个人的存在。”
“但肖御使一走,他们与那个人的约定自然解除。可能最让他们放心不下的就是肖御使掌据的内幕和你昨日所提的《肝胆录》,所以、他们必要逼你交出而后快的。‘五牲刹’就是东密负责执行截杀任务的五个杀手,分别为‘马刹’罗虎,‘犬刹’费严,‘羊刹’张天翅,‘猪刹’朱正,‘牛刹’高罗。”
“他们都是艺出西密,后来才投入东密的。西密原属藏传佛教,他们有一套秘密的仪式,名为‘天葬’,据说他们的工夫就由此习来。这门工夫和佛法、风俗有关,专以消解万物尸体为事,但中原人见了不免惊骇。适才来袭的,如果我看的不错,就是‘马刹’罗虎与‘牛刹’高罗两人。”
“我诱敌成功,留下了高罗一臂,但他们绝对不会甘心。所以我估计,这镖他们今日劫定了。”
正说着,忽听有个人在左侧哑着嗓子唱起来:
“……只见他手持刀器将咱觑,嘘得我战扑速魂归地府。登时间满地血模糊,碎分张骨肉皮肤。尖刀儿割下薄刀儿切,官秤称来私秤上估。应捕人在旁边觑,张弹压先抬了膊项,李弓兵强要了胸脯……”
这本是一套北曲,名唤“牛诉冤”,写耕牛被宰的惨况。猛地里在这个时候空旷旷地山谷里嚷了起来,听得人不由牙根发酸。
余果老面色一变,喝道:“快走!”说着已从二炳手里夺过缰,鞭梢一扬,山谷里就“啪”地传出一声脆响,拉车的牲口闪电般朝前窜去——余果老出临潼前已换了牲口。那牲口跑得好快,但就是这么快,也逃不过车两边的声音直钻进车厢。只听牛叫、马叫、羊叫、狗叫、猪叫,都似被屠宰的声音,声声传来,其间还有利刃过骨、爷头猛剁的杂声,小稚一听都吓得变了脸。
那余果老亲掌缰绳,对这条路竟似极熟,狂奔一刻,猛地一带左缰,那牲口就转进左边一个山谷,奔至谷内,余果老单手一勒,那牲口应声而止,余果老疾道:“下车。”
裴红棂行动也变得利索起来,她抱着小稚,猛地一跃,就跃到一棵老树之下。她问孩子道:“怕不怕。”
小稚摇摇头。余果老也已跃下,却把裴红棂引到一棵树后,交给她一把匕首,从树洞中拉出好几个绳结,疾道:“一会儿我说一声砍,你就依着次序一次砍一根。这事很重要,切切!”
裴红棂点点头。这还是她头一次握刀。余果老把小稚扶上树枝,自己就跃回谷中。裴红棂仔细看去,却见这山谷中居然有个小校场,她哪里知道,这里就是当年“威正镖局”训练年轻镖头们的地方。余果老自知“东密五刹”甩是甩不脱的,所以放弃大路,要引他们到此决战一场。
这山谷偏僻隐秘,余果老望向校场四周,当年的兵器架都已朽烂了,只孤零零地剩着一个还摇摇地站着,上面插了把锈迹沉沉的大刀。余果老觉得自己也象那刀一样的老了,他还挺不挺得过这一战?他也不知。望了树枝上的小稚一眼,他相信:刀虽老,钢还是好钢,只要好火痛锤,就又是一把利刃!
那个‘末路红颜’裴红棂此刻就是他的火、而小稚那无辜的眼神也就是击打在他心上的重锤,直要击打出他一份深藏的勇气来。只听谷口声音渐近。土黄、赭红、干青、麻白、黯黑,闪出穿着五色衣服的五个人影,东密五刹,终于到来。其中,土黄布衫的那个人缺了一条左臂,正是昨日被余老人一刀斩落一臂的牛刹高罗。他惨着一张脸,那《牛诉冤》一曲就是他唱的。——“东密”密功果然不同,才一天工夫,他虽受此重创,仍可行动自如了。
只见“牛刹”高罗一眼看见余老人,脸色就一变,口里尖声唱道:
……筋儿铺了弓,皮儿鞔做鼓,骨头儿卖与钗环铺。黑角做就乌犀带,花蹄儿开成玳瑁梳,无一件抛残物。好材儿卖与了靴匠,碎皮儿回与田夫……
他的声音尖锐嘶哑,本不适合唱歌,听起来简直就象勺儿刮碗的那种舔噪声。他的声音却被那个穿着一件赭红色衣服的“犬刹”费严打断。
只见那费严长得黑乎乎的,面目凶恶。只听他尖声道:“余老头儿,你这二十五年来,‘威正镖局’牌子还算一直不倒,虽说只剩你一个人,但你可要掂量掂量,那不是光靠你的本事,是江湖朋友不忍心再为难你,看在你一年只接一趟镖的份上,抬抬手就过去了。今年,你好象已走过鸿兴酒楼李大嘴那一趟镖了吧?再接,可就不是一单了,不能怪我兄弟们不买你的面子。”
“何况,我们追杀在前,你接镖在后,你到底有没有把我们‘五刹’放在眼里?”
裴红棂在远外却听得好奇——原来这老爷子二十五年来都在走镖?而且每年都只走一趟镖,那是为什么?为什么他喧赫一时的镖局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裴红棂心中疑惑无限,但这些却不是现在应当想的事。
只听那“犬刹”费严继续尖声道:“余老头儿,你想好,小心这一下翘辫子了,留下那二十七门孤寡没有活路。”
裴红棂看向那已长满了荒草的校场,这是昔日威正镖局全盛之日教练子弟的地方,余老人站在那儿显得又衰老又**。费严一句话后,余老人本有些驼的背就似乎直了。天上,是一天惨日。余老人一反手,就掣出他背后的那把大关刀,刀长三尺,阔八寸,那一天惨日砸在这荒芫的校场中,那刀就是这片惨日中最暗哑的光。
然后只听余老人说:“你无权拿我们镖局的孤寡开、玩、笑!”
他一字一顿。分明那“犬刹”费严的话已刺到他心中神圣处。世上总有人不肯一切都以滑稽涕突为时尚,如果有人敢干犯他心中圣地的话,他会一语拦断的!然后他并不侧头,口里却喝出了一个字——“砍”!
裴红棂一机灵,知道这一字是喊给自己的。她用尽力气,一匕首就向第一个绳结砍去。然后她眼前一绿,那绳索似缀着什么,一断以后,就向后抽去,飞快不见。却见校场上空有一片绿色的大布天幕般地罩了下来。那块布长达两丈,阔有五尺,猛地遮天蔽地地泻下,校场中人无不大吃一惊。
余老人就在那时出刀。他用的是大关刀,这一刀劈出风雷隐隐。惨淡日光中,他白发蓬飞,更显一种极为孤惨的悍勇,他这一刀劈向费严,这招名叫“挽弓挽强”。
费严大惊,疾退,就在他的退后中,他胸前一块作护心用的狗皮已爆裂开来,为刀风所破。那狗皮本经百般硝制,是他护身三宝之一,狗皮一裂,他胸膛裸露,险险让开刀刃,但刀风还是在他枯黄的胸口留下一道红痕,五脏六腑之间只觉翻来覆去地难受。
五牲刹没想到这老头老了老了,出刀还会这么快。只听余老人又喝道:“砍”,然后一刀横抹,直劈向“牛刹”高罗。这一招是“大关刀”的第二招“用箭用长。”
裴红棂虽为女子,但也觉心情激荡。她爱愈铮十余年,只为在他的宁淡中读出了在旁人身上读不出的两个字:风骨。而今日,她却在一个衰朽老人身上,读出了另两个字:英雄!
她望向她刚才砍落的第一块垂下的布幕,上面大大地写了一个字:“请”。字不好,但意兴豪飞,可能正是此老当年的笔意。她运尽腕力剁向第二根绳,又一副布幕落下,还是老旧的绿色,但已与前一块绿得不一样。上面也只有一个字:
“从”!
这一幕落下,晃花了五刹的眼,余老人就从布后出招,一刀就劈进了本已受伤的牛刹高罗之心口,高罗惨退,但刀跟着他,他退到哪里刀就进到哪里,他终于避之不过,任由那刀跺进了他胸骨三寸,萎然倒地。余老人全无慈悲,口中又喝道:“砍!”
裴红棂手起刃落,第三字现身,却是“绝”之一字。余老人已使到他大关刀第三招。第三刀名唤“射人射马”,这一刀变抹为削,转削“猪、马”两刹之双足。二刹急退,却也打出了他们绝门暗器“射影含砂”。这暗器名列‘东密五毒’之一,端的非同小可。好在余老人有蔽身的布幕。对方‘射影含砂’一出,他就不见了。然后余老人第四声“砍”已叫出,第四块布幕落下,余老人以布幕一卷,卷住了那蓬青砂,但布幕荡回原形时,裴红才看到上面已被毒砂蚀破了好几个大洞。依稀犹可见到的残字是“处”。
静如处子的“处”。
余老人却动如脱兔。他第四招再次劈向“犬刹”费严!“擒赋擒王”——余老人一喝出口,他不能给对方一口喘息之机来重组反击。
他老了,体力不会支持很长久,他不能允许对方反击!
费严退,还是退,口中大声地喘气,心中已在后悔惹上了这个老丧门星。裴红棂虽不解武功,但敏感于节奏,已看出余老人是要借威正镖局当年的七块旧布幕之哗然落地惑敌心志、助已意气、激发杀心、昂扬斗志,她也已见出余老人那大刀之间的顿挫之迹。
余老人第五声‘砍’开口的几乎同时,裴红棂已砍下第五根绳索,一个“读”字从天而降,这一下配合更为默契,余老人这时的一招叫做“杀人有限”,却是一式阴平刀法,以阴平对阴毒,羊刹张天翅本一直没出手,跟在余老人背后准备暗袭,可那块布幕一落,余老人忽然不见了,然后,他在自己喉间读出了一抹凉意。
他惊诧了下,大关刀还能运出这种平寒小巧的招术?然后他喉间一抹鲜血浸开,他瞪着眼颓然倒地。
不可能——羊刹在倒地之后还觉得不可能:没有人能在练成‘大关刀’后还可以用大刀使出女子们才会用的‘小解腕十七手’。那是匕首的招术呀。
但今天余老人做到了。
所以张天翅死了。
但就在余老人杀死张天翅之际,‘犬、马、猪’三刹已有了一息之机。他们重提一口气,立在场中,互相背靠,六只怨毒的眼睛罩定了余老人。
是他、在没打招呼之下出了手,也是他、已杀了自己一方的两个人,一手破了五刹阵。
他们非杀之不可。
自己一方是死了两个人,但余老人杀气已泄。
所以,反击的时候到了。
余老人果然被迫在避,回过神的三刹的反击极为激烈,满天都是砂,飞砂,不能沾上一星半点的砂!而他们三人脚步凝重,空谷校场中传出巨石滚地般的声音,象一只只大象在这空谷中踏着,他们踏的是余老人已经不多的生命。
——飞砂走石、尸解天下,这正是五刹酷绝天下的绝技!余老人的刀却象这狂砂巨石中努力不倒的一面旗。
旧旗。
风雨飘摇中的旧旗。
——白发萧驳的旧旗!
裴红棂看着余老人,才发现,他原来真的只剩有一只手好用了,那是右手。而他使用的大关刀本来沉重,本来就是该用两只手来握的,他塌了一肩,只有用右手的肩窝夹住大关刀柄。裴红棂忽然很后悔很后悔请余老人出这一趟镖,为什么还要拉上这一个耿介老人呢?自己娘俩儿死就死吧。死说不定反而是和愈铮的团圆。
为什么要再拉上这老人呢?
树洞里还剩两根绳。
‘余老人怎么还不喊砍?’裴红棂想,她的手心已全是汗。她望向场中,余老人明显已更落下风,他忽喉头一耸动,但没叫出,好在裴红棂与他似已有了心灵感应,在他出口前,手已剁下,一个大大的“侠”字从天落下。
一线之机,只有一线之机,余老人获得了一丝喘息,但他要她连砍两个绳结!可他张口要再叫“砍”字,丹田之气却已全运在刀上,喉中竟出不了声,这一急急得他满脸通红。他已老了,他在苦战三个年轻人,他只有这一个机会!他要最后一块布幕!
可他喊不出、喊不出!
裴红棂也不知自己是否真懂了老人的刀意,但她砍断第六根绳后,不知怎么,一咬银牙,挥刀向第七根就砍去。拼了——她想——拼了!——当时拼却怒颜红,就是这样一怒,这样一红吧?——如果她错,那她自刎谢余老人于泉下!
最后一个字格外刺目,那是:“气”。
——“请”、“从”、“绝”、“处”、“读”、“侠”、“气”……
——请、从、绝、处、读、侠、气!
请从绝处读侠气!
裴红棂只觉自己女性温柔的胸中也热血一炸。余老儿长啸进招,大关刀最后三势“列国有疆”、“苟能制敌”、“岂在杀伤”一气而出、奔涌而出!
裴红棂想:请从绝处读侠气!
——余老人刀意疯了,那刀意居然把七大块布幕的底端削碎,满天碎布中,他出招。
这一招天地无语,日光哑然。
三刹大惊。
惊也要避。
但如何避?
‘愿时光停顿在此一格’——裴红棂想——‘小稚在树上’——‘让他好好看看,好好记住今日的旧校场,记住五刹、记住这日光、记住老人的刀、还有——一个老人在惨日下如何出招’!
记住——“侠气”。
当此绝途。
记住侠气!
刀落。
“马刹”罗虎立毙。
“猪刹”朱正背裂,再毙。
“犬刹”重伤在额,遁,余老人补刀,杀之。
没有人能在这样的刀下一遁无踪。
校场上,只剩下余老人白发萧然,拄刀而立。
易水萧萧襟袖冷,看此翁白发拂如雪!
——乃识阔落此衰翁!
小稚忽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以后多年他还记得:他从没曾那么痛痛快快地哭过。
在惨日下,旧校场中无声地大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