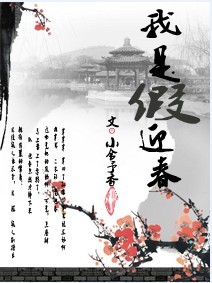孙绍祖见迎春哭了起来,也慌了:“别哭了,好么?都是我的错,别哭了,我最见不得你流泪。”
迎春不理孙绍祖,身子转向里面,哭得更厉害了。
孙绍祖在迎春身后拥住迎春:“我当时确实有些急躁,没想清楚就冤枉了你,伤了你的心,都是我的错。”
迎春的泪水落得更多。
孙绍祖板过迎春的身子:“你罚我,可好?你说怎么罚,就怎么罚?”
迎春止住哭,狐疑的看着孙绍祖。
孙绍祖郑重的说:“我是认真的。”
迎春心也软下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自己对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强硬不起来了。
迎春啐了一口孙绍祖:“哪个要理你,你记得,你已经欠我两次人情了!”
孙绍祖一笑,搂紧了迎春:“好好好,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好了。”
夫妻二人的矛盾,就化解在浓情蜜意的幔帐里面了。
五日后,司竹跑进来告诉迎春:“夫人,陈姨娘醒了。”
迎春听了后,点点头,让司竹遣小厮把消息告诉给孙绍祖。
孙绍祖提前从衙门里回到了府上,直接去了陈姨娘的院子。
孙绍祖一进屋,见香舍正喂半依着床的陈姨娘在吃粥。
香舍见孙绍祖进来,忙站起身。陈姨娘看着孙绍祖进来,竟然泪眼汪汪。
孙绍祖接过香舍手里的粥,摆摆手,打发香舍退下去。自己坐在床边,亲自给陈姨娘喂粥。
陈姨娘泪落了下来,声音极细小:“老爷待碧容真是再好不过了。”
孙绍祖劝道:“你大病刚愈,快别哭了。”
陈姨娘收住了泪,笑了笑:“我听老爷的。”
孙绍祖把陈姨娘喂过粥,扶她躺下,然后坐在床边说:“你能醒来就好,这几日,我和夫人也是很担心你。”
夫人?陈姨娘不由得抬头看向孙绍祖。
孙绍祖笑着说:“夫人也很是担心你,在昏迷时,夫人曾多次探望。”
“老爷怎知道夫人来了?是夫人告诉老爷的?”
孙绍祖听见陈姨娘这样说话,先皱了下眉,还是和声说:“不是夫人告诉我的,是其他丫头说的。”
陈姨娘冷笑起来:“夫人会这样关心我?她巴不得我早些死了才好。这话也定是夫人教给丫头们的。也只有老爷这样的实心人才会信。”
孙绍祖腾的站起来:“碧容,你这话是何意思?”
陈姨娘见孙绍祖生气了,心头的妒火燃得更旺,但是脸上却笑起来:“老爷生气了?碧容只是开个玩笑,老爷就当真了?”
说完,陈姨娘轻轻笑了起来。
孙绍祖狐疑的看着陈姨娘,陈姨娘岔开了话:“老爷,到底是什么令我昏迷这么多天的?”
孙绍祖眉头皱得更紧,思量良久,说道:“是香,你抚琴时总焚的香。大夫说,香料太多了,就会伤身。”
陈姨娘惊恐的看向孙绍祖:“老爷,难道……有人要害我?我并未得罪了谁啊。那香,也是夫人送我的。”
“这事和夫人无关,但是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会派人查下去的,定会还你个公道。”
陈姨娘抽抽答答的哭了起来,不再说话。
孙绍祖安慰了会陈姨娘,起身要走。
陈姨娘弱弱的叫声“老爷”,孙绍祖回身对陈姨娘说:“你好好养着罢,我和夫人说去,许你这个月都不去立规矩。”
“那你……这要去哪里?”陈姨娘还问出了忍了很久的话。
“我去夫人那里,告诉她一声,也好让她放心。”
陈姨娘不再说话,孙绍祖转身走了。
迎春这一日在房中和丫头们比对花样子,有小丫头急急来报,说迎喜行的一个伙计要见迎春。
迎春一皱眉,迎喜行一般有事都是泽英来的,而且,泽英来也是报帐,现在并没到月末,今天却让一个小伙计来,那么泽英做什么去了呢?伙计来又做什么呢?
迎春让人马上进来。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一进门就扑通跪倒,口中急急道:“夫……夫人,大事不好了,顺天府的差官现在迎喜行,说我们欺瞒买主,那里正闹着要捕泽英呢。”
迎春一惊,马上叫绣橘和司竹准备马车,去迎喜行。
马车上,司竹对迎春说:“夫人,要不,夫人和绣橘姐姐去迎喜行,我这去老爷的衙门上去罢,老爷一出头,迎喜行的麻烦许是好办些。”
迎春摇了摇头:“司竹,铺子是我自己开的,我岂能事事都去找你们老爷,司竹,我们做女人的,也要有些骨气,不到万不得已关头,我们是不能去找老爷的。”
司竹和绣橘都看向迎春,夫人……真是与众不同,不只是坚强,更是能独挡一面。司竹和绣橘都佩服的看着迎春。
马车到了谷雨街,迎喜行门口已经围了很多的人,几个差人守在门口处。迎春急急的下了马上车,带着绣橘、司竹就要朝里面走。被门口的差人拦住,官差上下打量着迎春:“你是做什么的?来这里要干什么?”
旁边的伙计马上说:“这位官爷,这是我家夫人,是迎喜行的东家。”
官差看了看迎春,放迎春进去了。
迎春进来后,见一个婆子正扯着张五家的袖子,大嚷大叫着。而正座上坐着一个四十上下的官差正坐着喝茶。
迎春上前给这位官差一施礼:“官爷,我是这家迎喜行的东家,我想问问,迎喜行到底犯了什么事?”
官差冷冷一笑:“我是顺天府的通判,有人已经告你们欺瞒买主,私令媒婆骗婚,以诈取银钱,我是特来拿你们的。”
通判的话刚说完,那个婆子和张五家的撕扯着走过来,婆子气冲冲对迎春说道:“你就迎喜行的东家啊,你来得正好。”转头又对通判说:“大人啊,就是她们,她们不仅骗了钱财,还毁了我们家儿子的一生啊,我儿子现在一个和别人有了婚约的男子,以后可怎么好再找人家啊,大老爷一定要给民妇做主啊。”
迎春问张五家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五家的哭道:“夫人啊,我冤枉啊,前几日,这个嫂子来求我们为她的儿子说门亲事,我在都中也是个有些名气的冰人,知道的人家不是户户皆识,但是也认识了大半,我并没见过这个嫂子,也没听说过她家,原不想帮你说亲。可是她苦苦哀求,无奈我帮她选了一家姑娘。”
张五家的抬头看向迎春,哭得更厉害:“换了帖子,过了大礼,这位嫂子却忽然来说要退亲,可是这大礼都过了,哪有退亲之理啊。”
婆子听张五家的说到这里,急急的抢起话来:“你先前可没有说那个姑娘是个脸上有胎记的丑八怪,我这么信你,让你帮我儿子找个好的,你却找出个这样的丑八怪来给我家做媳妇,我怎么可能不要退亲,我就是要让你们迎喜行把彩礼都给我退回来!”
张五家的辩道:“我们做冰人的,有我们的规矩,此事重大,我就是想瞒,瞒得过初一,难道能瞒得过十五去?都中的人家也有很多知道我张五家的,此错一次,我还能再当冰人么?当初我就和你说过,这个姑娘脸上有胎记,你说无妨,我才帮你去说亲的,现在你倒倒打一耙。”
张五家的说这些话时,迎春偷眼看了下那个婆子,只见那个婆子眼睛转着,像是有些心虚的样子,迎春见此,心下有底。
张五家的话说完,迎春对通判施了一礼:“通判大人,我现在怀疑这个婆子要讹诈我迎喜行,我要状告她。”
婆子没想到迎春会说这样的话,眼睛瞪起来:“你倒会恶人告状,你们骗了我的银子,毁了我儿子的一生,官爷啊,求你给民妇做主啊。”
通判皱起了眉头,对迎春问道:“你说这个婆子讹诈你们迎喜行,你可有证据?她现在倒是有你们迎喜行写的租单为证,你们呢?”
迎春吸了一口冷气,自己这里并没有十足的证据,只是自己的怀疑而已。
婆子见迎春不说话,眼里闪过得意之色,她快步走到迎喜行的门口,对着外面围着看热闹的哭道:“迎喜行的东家依仗有些背景,竟然瞒下了我家的家财,我给儿子说亲的彩礼都是我借来的,这让我怎么还啊,而且,我儿子的一生就这样毁在迎喜行了,大家说公道不公道啊。他们仗着有势力就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大伙给评评理罢,我老婆子是没法活了。”说完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谷雨街是在城中,两边因全是酒楼,来往的人很多。迎春行门前本来围着的人就已经很多,听着婆子喊着的话,路过的人和左右两边的铺子里都探出头来,往迎春门前看去。转着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投向迎春的目光也变得义愤起来。
迎春没想到这个婆子会这样狡猾,居然去扇动普通民众的情绪,一起来对付迎喜行。如果这件事不解决好了,只怕就算是这个婆子真是诬告,都中的人也不会知道,反倒会以为迎喜行仗势欺人,迎喜行以后也就不用开了。
迎春走上前,蹲下身子柔声对婆子说:“我们并没有瞒你的财物,这事只是个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