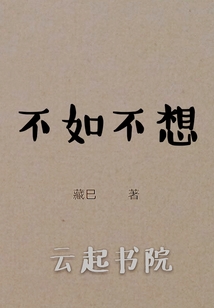“我父母很早就死了,坠机。不过我不像你啊,他们死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阿维故意摆出一副凶狠的样子,“我这样,是不是很没有人性。”
“没心没肺。”我开玩笑。
村子里的葬礼,办得像个婚礼。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父亲一去世就冒出这么多人,他们都是顶着送葬的名头来围观凑热闹的村民。
所有的事情都被安排好,我需要做的,就是一直跪坐在灵堂前。我也不愿与这些陌生虚伪的嘴脸打交道。他们甚至没有流露出一点悲伤,围坐一桌嘻嘻哈哈,推杯换盏哗闹。
按规矩,丧礼办得越是热闹,逝去的人才会走得风光。于是请了个戏台子。着实是一出好戏。台子支在了院子里,戏子的声音吸引了村子里的所有门户,人群漫到了马路上。
粹亮月色下
辽散旷野里
立着一个戏台子
台上的人物
红红绿绿地动
台下的人物
疏疏朗朗地站
台上
铁头老生背插旗
不翻筋斗
耍把式
小旦咿咿呀呀唱
台下
呵欠谈天
台上
红衫小丑被打鞭
台下
笑看恸天
台上
老生坐唱惹人嫌
台下
乌篷船里自成天
不过是一流货色
二流呈现
丧宴一直持续了三天才封殓。盖棺的时候,我望着父亲被刷白涂红的脸,一寸一寸被掩盖。我还幻想他能紧着最后一片天坐起,然后笑笑告诉我们,其实一切只是个玩笑。诈尸,这种超自然现象只能在故事里大摇大摆实现。
听说土葬延续不了多久了,父亲算是赶上了最后一波。几个吃饱喝足三天饭涨了力气的男人抬着父亲的棺材跟在我们后面走着,我不时就回头看看,又盼着棺盖里能发出咚咚的敲击声,听父亲说他睡醒了。没有听到我就转过头继续往前走,每走百米就得停下来,因为那些壮汉得停下喘口气。寻安的身材看起来比那些人要纤瘦得多,可没听见他有喘粗气。我每次回头,他都像散步似的轻松自在,看我的眼神也是一如既往的柔软。
就这样走走停停,一段简单的路程耽误出西天取经的命途多舛。我都生怕父亲的遗体被他们折腾散架。好不容易到了据说是自家的那块山头,把棺木放进先前挖好的洞里,覆土围砌,再把墓碑立起,一阵鞭炮声后,我听到所有人都发出如释重负的嗟叹。
望着母亲不断地鞠躬道谢,我始终是面无表情。
我想自己死后一定不要这样大张旗鼓的做样隆重,化成灰多轻松,一个人就捧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