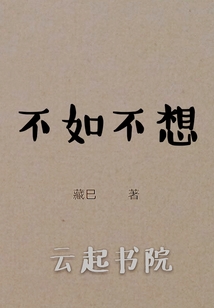生活无关紧要,但日记还得继续写。
我再进了那间房,趁安南去外地的时候。她最近的心情不错,我表面配合她嘻嘻哈哈,但心里的疑问一天不解决,我一天笑不畅快。
家里寂静得很,我是瞒着母亲回的。那时家里没人,我掏出钥匙打开大门的时候,有一层浸透了灰的透明羽翼拥向我,就像进了栋被遗落的烂尾楼。
客厅里的所有物件都积了层灰,灰不厚,但还是被我注意到,因为触手可及的颗粒感,还有即使拉开窗帘也消散不掉的暗色,包括茶几上五彩的模型房子,它已经被完整拼凑出原状貌。
我没仔细端详,但情况大致是没变。我切入主题的过程有些冗长,也许还是因为担心被抓包或者不能消化那些发现。我在沙发上整整躺了两个钟,可周遭除了尘埃落地再无其他变化。
尿意让我起身。洗手的时候我看着镜子,里面的我面无表情,看不出悲喜。流水的凉激灵得我霎时清醒,我记起了此行的目的。
我把手放在一旁挂着的毛巾里,任它吸。出洗漱间右拐,经过楼梯间,我到了密室门前。锃亮的把手彰显它的唯独,它是这栋屋子里面唯一的净土。我把手搭在它身上,握住,使力,旋转……动作之间都有清晰的间隔,这使得进门的动作冠上了仪式感。轻松拧开,看来母亲没想过再把它当成密室。父亲去世,她可以堂而皇之在里面做些怀念。
房间里确实一尘不染,因为灰尘怕人、黏人。原先的跪垫直接变成了可躺的沙发,可想而知母亲多愿意为怀念这件事占用打扫其他屋子的时间。
我顺势躺在沙发上,上面还沾染着消散不了的烟草味道。我回想起第一次的误入,为里面的神秘性不过几次就被消磨光而惋惜。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引火吞云吐雾。我不算会抽烟,但不熟练的情况下功效愈发明显,我的心思随着烟气散了。燃烧之后的余烬掉在了手臂上,没有温度,我把它甩到地上。
沙发把我的全身心收入囊中,我想到了母亲。她会把双腿折叠,屈膝靠向一侧坐着,一手撑住额头,冥思苦想。她或许不会睁眼,灵台上的照片早已刻骨铭心。她会一待就是一整天,茶也不思寐也不服。
我起身,在没有亮子的屋子里窥探究竟,在一干二净里寻找蛛丝马迹。
他听到这才提起了些微能动性,眼皮稍微一抬,停下在桌上敲打的手指。
“我等到了事情的关键?”
“关键?”
“能决定你是否在妄下断语。”
我当然不是信口开河,更没有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一些无关紧要。我从没有在乎过所谓的关键。施教者常把“处处留心皆学问”挂在嘴上,换言之,留心之处便是关键。何况我也非褊狭之人,不会时刻把“关键”拿出来左观右望。我只是目睹,放不放心上是一回事,拿不拿它当说辞又是另外一回事。
安南常说我喜欢咬文嚼字,简单的问题也可以和形而上挂上钩,把和他说话的人带到沟里去。我突然想到她夹紧眉头的样子,于是就笑了出来。可是人在这个场合里不配笑。
他显得有些愠怒。
“面对我,也能让你想到她?”他把刚升起来的怒气转化为了揶揄。
果然他全都知道。
从我进来到现在,他一直闷不做声,听我在说。我与他的兄弟情自小就浅,他对我做的最擅长一件事就是呼来喝去、颐指气使,他对我的态度可以称得上是不屑。面对这样的他,我倒是有些不习惯。
“继续吧,说说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说处理就意味着它之前是一场大型事故的案发地,我能闻到血腥味。虽然没发现血迹,但味道还在。果然烟还是有用,我的意志明显比之前清醒,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里面没有其他人,不妨碍我闻血腥味。他们匆忙给父亲收尸的时候,忘记把门打开透气了。我推测他们运动的轨迹,密室是第一案发现场,然后是一路拖到洗手间把尸体洗净抹干,最后再把他完整放到床上。我顺着轨迹走,总能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我还是回到了密室,总觉得没有找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