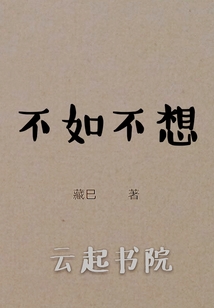原来监狱跟家里也没什么两样。
家里的西北角是间除母亲以外禁止他人入内的神秘屋子。它常被锁着,钥匙被母亲收在哪里我们没人知道。
我自诩调皮捣蛋惯了,什么地方都爱蹿上一趟,就唯独不爱上学。很快就面临上小学,我如临大敌,死活都不愿意去学校,跟父母斗智斗勇玩起了捉迷藏。
眼看着报道期限就要过了,父母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拎起来。脑子里还是一锅浆糊,我稀里糊涂地看着母亲在我身上捣腾。我表面服从一切安排,心里却在暗中盘算。
“我必须想个办法,让他们都找不到我!”
家里大大小小的地方我都藏了个遍,他们都有经验。父亲在外面浇着花,躲到外面就更不可能了。我在客厅里来来回回走,最后趁着母亲上厕所的当头,一股脑儿钻进母亲的密室。
我把门锁好,耳朵贴在门上听动静。
母亲出了厕所,“君泽,你又跑哪儿去了?该去学校了。”她跑上跑下,每间房都来回搜罗。
“怎么,这臭小子又躲起来了是吧?”父亲闻声也加入搜寻我的阵营。
我提起十二分精神,心悬到了嗓子眼儿。“老天爷,保佑我千万不要被爸妈找到……”我学着电视里那些人的模样求神拜佛,双手合十,忙不迭地鞠躬。
“你最好自觉一点主动出来!”父亲发出威胁,我想着母亲一定会保护我,就又鼓起勇气。
“君泽听话,快点出来,爸爸是真的生气了。你要再不出来,到时候被打妈妈可不会帮你!”母亲猜中了我的心思,也跟着装模作样恐吓。
事情已经覆水难收,我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被打还要去上学。我给自己鼓劲,一定要撑住。
他们几乎翻遍了整栋房也没能找到我。双方都费了许多气力,该休战了。我有些得意,觉得自己找了个不错的窝藏点。
“会不会是出去了?要不你去外面找找?”母亲说。
“这样,你开车往大路上找,我走路去他平常会去的一些地方看看。”
父亲开车离开,我听到外面的铁门也被关上,他们终于出门。我舒了口气,紧张过度的身体顺着门滑下,我坐到地上。
我好奇他们为什么唯独没有找上这间房,又联想到母亲每天都会进来待很久。平时它都明令禁止不让进,想必这次是母亲忘记了锁门。好奇心驱动我打探起这间房。
房间很黑,什么都看不清。这间房连个窗子都没有,密不透风。我在墙上摸索,想找到开关把灯打开。顺着墙壁从上至下一路摸索,我没有找到开关。房间里面冷清得瑟人,我想入非非,以为它就是传说中关坏小孩的小黑屋,又叫鬼屋。
压迫感越来越强烈,我不敢再动,只能紧紧贴住墙身。背上的衣服也早已被汗水浸透。我陷入无尽的恐慌,把头深深地埋进自己的双腿里,紧闭双眼,瑟瑟发抖,忘记自己其实可以开门出去。
“爸妈怎么还不回啊?”我想起父母,想让他们赶紧找到我。
可我越是害怕,时间就似乎过得越是慢,我开始哭喊了起来。我不能再这么继续等下去,一鼓作气站了起来,两臂向前伸,摆出一副扫荡的气势,准备冲出去。
在这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空间里,我佯装着什么都不存在的样子,凭着感觉一路向前走……结果,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我打到了一个硬物,痛得把手立马缩了回来。好不容易缓解了疼痛,我再次鼓起勇气向前摸,原来是一张桌子。
桌子很高,我摸不到桌面上放了什么,但是桌子底下的空间倒是很大,我一股脑儿钻了进去。许是因为密闭的空间带给了我安全感,我放松了许多。接下来,就是等着父母回来了。
眼前似乎还有些别的东西,我蹲着把手伸了上去。触感很软,感觉好像是块垫子。我把它抓过来,一屁股坐了上去。
“躲在这里,要是我不发声,他们估计就永远找不到我了……”想到这,我又忍不住偷笑了几声。想起之前被吓哭的模样,我庆幸没被他们看到,不然又会被当成笑话。
过了好久,依然没有听到父母回来的动静。紧张过后的放松,让我生出了困意。坐着坐着,我打起了瞌睡。
恍惚间,我听到了开门声。我一下子惊醒过来,忘记自己是在桌子底下,连忙站起身子,结果把脑袋给砸晕了。
桌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倒了下来,我听到了“哐当”一声。
就在我一边揉着脑袋,一边好不容易钻出来的时候。房间里终于闯进了光,我眯着眼睛看过去,原来是母亲进来了。
“妈……”我还没来得及向母亲哭诉,只见她如临大敌一般地向我冲来,然后一把提起我扔了出去!
不敢相信母亲竟然把我当作垃圾似的扔了!我被吓得大气不敢出,乘着仅有的那些许光,我不自觉地回头看。原来桌上放着的,是一个灵牌,还有一张照片。
我的脑子还没把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给理清,父亲又抓住我的领子,把我举了起来。
“妈!”我赶忙呼喊母亲,在空中不断地扭动。
可是她并没有出来,而是一把关上了门。
我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一次不会再有任何人来帮我,我要为自己的调皮买单了。
“爸……我知道错了。”
“你不要打我……我乖乖跟你们去学校,好不好?”我不停地道歉,虽然知道可能并不会起作用。
父亲一路把我拎到外面的院子里,然后甩到草坪上。他随手抓起一旁的扫帚,用力向我扑过来。我被打得“哇哇”大哭,可是依然不见母亲出来帮我。我的哭声对父亲来说反而像是在鼓劲,他越打越厉害。
这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打我。我不知如何是好,不停往后挪。躲避是天生的自我保护举动,但显然,我和父亲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那一口池塘。
我滚了下去,砸到了池塘里的石头,然后晕在了水里。
等我醒来,自己已经躺到了医院里。第一次去医院,我睁开眼,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不知道医院为什么酷爱白色,也许是为了让红色的血液更加鲜明吧。
回到家,父母不再逼迫我去学校。我看着镜子里那个满头纱布的自己,只觉得意识模糊,分不清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再过不久,母亲又怀孕了。看着她浑圆的肚子,仿佛自己也置身其中。母亲一边摸着我的头,一边揉着自己的肚子。那种感觉很美好。不过一年,弟弟妹妹降生了。他们很健康,也很漂亮。
每当我再次走近那间密室,还有那口不知底的池塘,我的大脑就像被搅拌似的疼。这明明是件不小的事情,却被父母轻描淡写地带过。反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对弟弟妹妹降临的欣喜中。这让我心有余悸,也让我更加坚定,自己一定要弄清楚那个灵牌背后的秘密。
一天夜里,趁着父母还在熟睡。我拿起手电筒,再次靠近那间房。门被锁住了,我打不开,只能先跑到父母的屋子里找钥匙。我注意到母亲每次关门时都会把钥匙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果不其然,钥匙真的在里面。
我打开门,静悄悄地往里走,然后不发一声地关上门。稍稍站定几秒,平复好自己强烈跳动着的心脏后,我举起了手电筒。
这确实是一间典型祭祀用的房间,里面没有任何常规的摆件,除了祭祀台和灵位。为什么要在家里保留这样一间房?
我正对着灵台,让手电筒的光直直打在上面。
强光打在照片的玻璃外框后又反射到了我的眼里,我睁不开眼。于是调整了手电筒照射的方向,尝试着慢慢睁开眼睛,慢慢向他靠近。
终于,我看清楚了他。
照片上的他很年轻,眸子里透出一股坚定。我被深深地吸引,仿佛透过他的眼睛我也可以看到那时的画面。更加奇怪的是,我莫名觉得熟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去之人的照片,但我却丝毫不感到畏惧。心里甚至产生了一种“与其面对自己有血有肉的父母,还不如看着他冰冷的照片更让人觉得温暖”的古怪想法。
自那以后,我经常在夜里偷去那间房,然后坐在灵牌前的拜垫上,静静地望着这个让我觉得有缘的陌生人。但我时常想他到底是谁?我不敢去问父母,那时的我就已经察觉,他在我们家是个不能被提及的禁忌,所以才会被锁在不见天日的地方。
我渐渐地不再像之前那样爱父母,尤其是对父亲,我居然觉得恨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次事件的发生让我变得畏惧,从而不再爱他,但我对弟弟妹妹却是由衷的喜欢。我感恩他们的到来,让我不再孤独。但同时我也为他们惋惜,也许他们不该投生于这个家庭。
那个时候,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在学校里孜孜不倦,而我却是领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终日在田地里蹿。我也自得其乐,并不为此觉得惋惜。有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并不一定总是相互对应的,父母不再用手段惩罚我的顽皮,这本该是件好事,我可以不用再对他们有所忌惮,但我并不喜欢这种区别对待。
我在童年就开始了自己漫长而又孤独的人生,陪着我的竟是一块灵牌。
弟弟妹妹逐渐长大,眼看着就要离开家去学校了。我自然是不舍,却又左右不了别人的想法。他们不像我,他们满心憧憬自己的校园生活。每每想起以后的生活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心有不甘。渐渐地,我的脑海里诞生出一个可怖的想法——我要让他们和我一样被困在这个家里,永远不接触外界。
我半夜把他们叫醒,称要带他们去探险。
妹妹因为怕黑,始终不肯进去,我害怕她闹出动静把母亲吸引过来,于是便只把弟弟领了进去。弟弟的性子与妹妹相反,从小就不爱闹。哪怕是进了这样一间黑漆漆的屋子,他也不为所动。我指引他看向灵牌,他和当初的我一样径自走了过去,呆呆地看了许久。
“这个人长得和你很像。”他是看着我说的。
闻言,我猛地看向这张已经看过无数遍的照片里的这个男人。确实如弟弟所言,他的模样与我很相似。我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那股熟悉感源自哪里……也许,他和我的关系非同寻常。
“这件事情,你不能让爸妈知道。”
“否则他们会很生气,知道吗?”我警告弟弟守住这个秘密。
“他的脑部受到重创,也许,会影响到他的智力……”
这是那次事故后,医生对父母的说明。也是从那时候起,我被当成一个糊涂人,受尽他们的照顾。
小孩若是被狼带大,那么他的生理习性全都会随了狼,他只似一个人,但其实是只狼。我什么事都不用操心,即便是所谓的生活必备技能,我也不用想办法去掌握。看起来,我的智商似乎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年。这么为难人的事情,我却做得很好。身边这些所谓最亲近的人,全都没有看破,这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家是一个不需要伪装的地方,这是一个伪命题。
我用尽各种招数,但还是没能让弟弟妹妹留下来。他们告别了这个难堪的地方,但我并不羡慕。终有一天他们会回到这儿,看着它破碎。
我导出的第一场大戏,就是吞石子。
既然是表演吃饭,不管碗里装的是什么,我都得吃下去。这样的演出才够逼真,才够引人入胜。只需一个简单的吞咽动作,我就能达成目的,想来真是足够轻松。他们的情绪被带动,家里面乱成一片之后,我却尤为平静。看着他们为我着急忙慌的样子,我其实很想笑,正如那些无知村民认定我是个傻子之后,他们的大声嘲笑那样。
这也是我第二次来到这个纯白的世界。这一次,父母完全笃定了医生的那句话。我看到他们流泪了……那是悔恨吗?还是在怜惜自己?
难为我那年纪尚幼的弟妹,什么都不知情,还以为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群众演员就是这样,明明不是主角,却背负着所有的应该和不应该。
躺在病床上的我,痴痴地看着天花板,好像灵魂已经飞走了,只是一个被魔鬼控制住的躯壳而已。可怕的是,我却还能感受到痛!当洗胃的管子直穿我的身体,到达我的胃腔的时候,我居然真的觉得很难受……明明当时吞下那些质地坚硬,棱角分明的石头时,我都毫无感觉。
我在毁灭自己,当然会产生难以割舍的痛感。
我的人生注定要成为别人口中的笑话和悲剧。每每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嘲笑自己。痛苦到了最后,就连自己也不放过自己了。
回到家,一切又变回原样,天大的事一旦到了这个家都会变成无人提及的小事。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黑洞,稍不留心被吞噬了,我就不再是我了。
母亲把我扶在沙发上坐定,拉着父亲急冲冲地出了门。
透过落地窗,我可以看到他们在商讨着什么。
“大哥,我错了。”
“咱们以后再也不玩这个游戏了,你别生我的气好吗?”妹妹委屈地走到我跟前,摇晃着我的胳膊向我认错。
我无奈地笑了笑,“你没有做错什么事,不用跟大哥道歉。”
我摸了摸她的头,想让她停止自责,然而却把这小姑娘给弄哭了。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我想。
弟弟见她哭了,连忙走了过来,一把抱住她,让她别哭。这个画面真是温馨感人,一下子刺痛了我的双眼。
在这个家,我永远是个局外人。他们总有人陪,我却只有照片里的那个人。
我已经习惯了夜里要与他相互作伴,他成了我的精神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