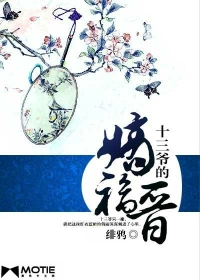念声脸上已经凝重起,“疹子也好,痘儿也罢,终归都是会过人的。有些事儿虽然可大可小,但不想让事儿大了,终归还要咱们自己加小心。”
挂蟾点了点头,退开念声身边两步,冲着她福了福,“福晋放心,奴婢一定替您看好了这些人。”
念声有些上前交待挂蟾几句,却被挂蟾兰拦了。
“主儿,您也奴婢远着些才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想想晚间在富察府看见的那具尸首,挂蟾就不寒而栗,如果自己真有个万一,那也决不能再让自家主子有什么不测。“奴婢现在就去外头,点齐了今晚去过的人,打扫好花房边上的屋子,连夜搬进去。”
念声虽然不忍心,但还是点了点头,“只是委屈你了。让人把一应用具都备齐了,你也别有旁的想的,只当是我放了你去轻省几天,好好歇歇就是。”
挂蟾眼角闪过泪光,赶紧低头跪下,给念声磕了个头,就出去安置了。
不多时,盐丁站在了门边。
上夜的小丫头早得了念声的吩咐,看见他来也不多话,只默默打了帘子让他进去。
盐丁心里纳罕,这才吃了教训没多久,怎的福晋又找自己?再看这小丫头的样子,也着实不像能有什么好事儿。可又不敢耍滑不来,值得咬着牙,硬着头皮往里走。
念声在花厅里坐了,见盐丁进来也不说话,只是默默看他打了个千儿,晾着他自己在那儿弓着身子跪下去也不是,想起来更不敢。
“福……福晋……”盐丁弓着身子单膝跪地,偷眼瞄了一眼念声,就又赶紧低下头去,轻声叫了一声。
念声眉梢一挑,好似刚看见盐丁一般,“来了就起来吧。你这样,叫本福晋怎么吩咐你差事啊?”
盐丁听了一句话,索性跪好了,给念声磕了头才说,“主子吩咐奴才差事,只管交待就是。奴才一定万死不辞。”
“嗯,倒是前儿个才听过你要誓死效忠的话。可不成想,这会儿子就给了你机会了。只是不知道,你做不做得到,别只是嘴上说说的漂亮话才是。”念声也不喊他起来,只看了他慢悠悠的说着。
盐丁不仅缩了下吧脖子,心里已然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之前就是卖乖,才在福晋跟前栽了个大跟头,眼下一时不慎,平日里嘴边滑顺溜的话竟是没过脑子就说了出来,正给人抓了个刚刚好。
“怎么?这就怕了?”念声的话里带了两分轻视。
“奴才全凭主子吩咐。”盐丁被念声激起了性子,觉着此刻福晋大约就是要跟自己秋后算账了,与其被收拾的窝窝囊囊的去死,倒不如有些气性,总好过临了让人看轻了。
念声闻言点了点头,“总算你还有几分骨气在。起来吧。把心放进肚子里,起来好好听吩咐,今儿个晚上,还要好些事儿要仰仗你呢。”
盐丁听的一愣,刚从地上爬起来,一岔神,差点又跪下,“福晋,您……您要给奴才派差事?”盐丁怀疑自己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原以为再不会有机会巴结福晋了,这怎么就来了差事?
念声忍不住笑了,“不然呢?这大晚上的,专门使人把你从贝勒爷身边叫进来,就是为了听你几句巴结?还是就为了吓唬吓唬你?你把本福晋想的也忒闲得慌了。”
“奴才不是那个意思。”盐丁吓得又要跪下。
“站好了。”念声赶紧喊住了他,也不知道胤祥府里的下人都是谁调教的,从总管到下头的粗使下人,未见的得多中用,这下跪磕头的本事倒是一个赛这一个的利索。“仔细听了,事情多,没工夫看你在这儿跟我论礼数”
盐丁又弯了弯腰道,“奴才不敢。”才算是站稳当了。
“晚间听闻是富察小姐染了痘疹,身上不大好。她将来也是要进到家里来的,我便使挂蟾去了富察府里一趟瞧瞧。听挂蟾回来说,大约是真的不太……”念声横竖也没想到个合适的话来,只好含糊了一句。“眼下家里,一头是大姐儿身上还没好利索,一头是贝勒爷整日进进出出,也就少不得多谨慎些。”
“福晋说的是。”盐丁虽然一时还没听明白念声到底要说什么,天生的机灵劲儿还是让他自然而然的应了一声。
“为着这点子谨慎,我便嘱咐挂蟾,连带今晚出去过的几个人,都暂时住到花房边上的屋里去。等过上几天,都无事了,再上来伺候。”念声的手指轻而不紧不慢的叩着梨花木的桌面。“我身边一直只有挂蟾一个顶事的,余下的不是太小,就是没经过事儿,短历练。她这一时歇下了,我难免没了左右。”念声的话说到这里,意味深长的看向盐丁。
“福晋的意思是?”盐丁已经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压抑着翻涌上来的欢喜,赔着小心问。
“贝勒爷身边有你师父伺候着,你跟着你师父也有一段时间了吧?”念声不错眼的看着盐丁,“对着里里外外的事情,应该是有些经验了,我便想着先把你调进内院几天,就算是我给自己找个帮手?当然,我也知道,家里事情琐碎,不如你跟着贝勒爷在外头要排场有排场,要面子有面子的痛快。”念声把话说的很克制,哪怕自己眼下是真的缺人手,也没打算给盐丁太多好脸色,毕竟还是个没定性的孩子,真的纵了他自傲起来,将来指不定是多大的祸害了。
话听到这里,盐丁要是还不明白福晋喊自己过来的意思,那他这么多年的差都算是白当了。于是一躬身就端端正正的跪了下去,看了念声说,“奴才全凭福晋调遣。定然好好服侍,尽心办事,不辜负福晋的器重。”
念声忍不住笑了,心说到底还是个小孩儿,才一听说有提拔他的意思,脸上的笑意就藏不住了,轻咳了一声才说,“说什么器重不器重的,还要看你自己了。这会儿子喊你进来,就是要问问你的意思,你要是乐意呢……”
“奴才乐意的。”盐丁急忙说,好似生怕答应的慢了,福晋就不用自己了似的。
“那我明儿个就跟贝勒爷要了你过来,你师父那里,我自然也会招呼。”念声听见让自己还算满意的答复,才继续说道,“只是这差事,怕等不到明儿个了。”
盐丁从地上爬起来,扬起一张笑脸,“主儿,您吩咐。”
念声细细嘱咐了几件眼下要紧的,盐丁就一一应了,把自己不甚明了的地方再问过,才告退下去。
随后又有支应的嬷嬷上来回事儿,再是索多图进来,隔着帘子领对牌,勾了账上的使用器具去铺排……前前后后,来来往往,说不尽的细碎,饶是念声耐着性子,挨到过了子时,也是有些心烦。强撑着去看了大姐儿睡的还算安稳,才松了一口气,回到自己屋里卸妆歇下。
可巧当值上夜的丫鬟是贝勒府里的,本就对新福晋有些顾忌,今晚有亲眼看着念声里外操持调配,虽弄不明白里头的章程,可也打心眼里生出了敬畏的意思,伺候起来愈发的谨小慎微,只怕有什么惹了福晋不痛快的地方。
若是挂蟾在身边,念声定要说上几句畅快的才好躺下,看着眼前丫鬟恨不能把头低到肚子上的劲儿,也就没了说话的意思,由着她们收拾好,也就熄灯安置了。
胤祥看了几眼闲书,早早睡下,一夜无梦,早间起来自觉神清气爽,连带海亮替他梳头手重了一下,也是笑笑就过去了。“福晋起了吗?”心里只惦记着出门之前得不得见一眼自己媳妇。
海亮替胤祥把辫子穗扎好,又请人起身,忙着整理腰带,套外头的衣裳。“奴才听人说,福晋昨儿是忙入了夜的,都过了子时才歇下,只怕这会儿子未必会起。”
“怎么个意思?”胤祥一愣,“去,让挂蟾过来回话。她怎么伺候的福晋?”
海亮晨起听盐丁跟自己说了个大概,看贝勒爷急了,赶忙解释,“昨儿福晋打发挂蟾姑娘去看富察侧……富察小姐。”看着胤祥的脸色,海亮到了嘴边的话又拐了弯儿。“听盐丁说,挂蟾姑娘回来以后,就禀明了福晋。大约是富察小姐病的有些凶险,福晋怕昨儿去了的人带了病气回来,这就吩咐连夜收拾了府里花房边上的屋子,把那几个去过富察家的,都隔了住进去。说是,等过上几天,要是都没事儿,就回各处当差。要是有个万一,也好避过了咱们这一府的人。”
胤祥没想到会是这么个事儿,不免有些着急,“怎的现在才说。昨儿个晚上为什么不来回?”
海亮蹲下身子,把胤祥的袍角展展平,才接着说,“昨个儿晚上,福晋身边的小丫头只让来传盐丁过去,说有些吩咐,奴才当时也没多想,就没多问。这不还是刚刚盐丁赶着奴才伺候您起来前,说了这几句。奴家正说,等你收拾得了,就去后头给福晋请安呢。”
“诶?贝勒爷,您这是干嘛去啊?您的帽子……”
胤祥没等海亮说完,抬脚就往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