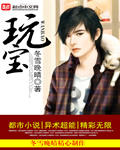贤惠二字咬得很重。咫尺间赵胤一双鹰眸,泛起了雪亮的凛意和试探,逼得刘蕙浑身僵住,半分装傻充愣的余地都无。
刘蕙初始的惊诧迅速平复下来,心思转动,立马明白了话里深意是说杨胭那茬,她反而无声的松了口气,脸上挂起刚刚好的畏惧和坦诚。
“陛下这话说的,哪个女子愿意见着夫君一心多用呢,妾当然略有失意。但妾首先是皇后,才是人妇,陛下三宫六院也是多添子嗣,为祖宗社稷筹谋,妾又岂可为一己私心而步愚人后尘。只要杨氏安分守己,忠于陛下,妾这点容人之量也是中宫该有的气度。”
赵胤眸色闪了闪,放开刘蕙,眸底的寒意迅速褪去,又是那副病容怏怏的模样,打了个哈欠:“皇后言重了,你侍奉朕数十年,你的心性朕岂是信不过?只是自从敬元皇后没了,你就对后宫之事毫不上心,朕纳多少你都无所谓似的,故有方才一问。”
被话中某个名讳戳中痛点,刘蕙眉尖猛地一蹙,霎时心口都喘不过气来。
但她似乎对这种应对极为熟练,心绪转念镇定,跪倒,又是那番滴水不漏:“多谢陛下体恤。妾唯愿西周国泰民安,龙凤呈祥,千秋万代社稷永固也。”
赵胤勾勾唇角,这话听得舒服,转头看向刘蕙的脑门顶,缓声道:“你们刘家这么多年都只是个五品官?”
“官不论大小,只求造福民生,为父母官也,妾身母家已是感念圣上恩德了。”刘蕙恭敬的回禀。
赵胤闭目沉吟,他如何不知自己岳父母的家门,只是试探刘蕙的意思,好在从始至终女子的反应都没让他失望。
至少表面上,是合格的国母,那就够了。
潭洲刘氏,江南有头有脸的清流,书香门第也,官不算大,但深得民心。东周某日,其嫡女被南下务公的右相赵胤看中,带回盛京,封为侧室,宠眷不衰,后来沧海桑田,右相成了皇帝,侧室成了贵妃,再后来,又成了继后,改惠为蕙,世称刘蕙。
奇的就是这刘氏以前官阶不高也就罢了,自家女儿成了皇后了,还只是五品,一连二十几年了,还真就当得舒舒服服,半点怨声也无。
“朕当年初登帝位,国基不稳,恐外戚乱政,故一直冷落刘氏,受委屈了。”赵胤的脸色柔下来,虚手扶起刘蕙,下了决定,“二十几年了,刘氏的忠心朕也瞧清楚了,该赏,该升。”
刘蕙一惊,抬眸。
赵胤披衣下榻,取了案上的朱笔,往折子上落批:“来人,传旨:曹家陷害良家子花氏一案,准东宫和钱家奏。曹家居心叵测,胆大犯上,即刻,全族罢官,抄家,当事者流放。从今往后,江宁织造不姓曹,姓刘。”
立马有中书舍人接了折子出去,寂静的深夜,暗流已经在酝酿,江南城注定是一个不眠夜。
刘蕙跪下谢恩,啜泣着说些隆恩浩荡的话,赵胤正色:“刘氏入主江南,别跟曹家一样,脚落在这地界上,就把山大王认成真的王了。”
“妾一定提点家族,忠心侍君,绝不辜负陛下厚望!”刘蕙抹了把泪,再拜。
“很好,刘家就帮朕盯着点钱府。这次来江南,也不算完全亏了,东墙垮了西墙又建起来了……不破不立,不破不立呀!”
赵胤心情大好,身子往被窝里一缩,便被绒团儿似的火塘烤得倦意袭来。
十一月,江南秋末初冬,霜凝寒天。
搅得江南风起云涌的曹家案终于尘埃落定。
曹家全族罢官,抄家,一代名门分崩离析,潭洲刘氏迅速上位,据说曹家诸人迁出江南城时,没一个人送,因为官民都忙着恭贺刘家去了,十里八乡都是热闹的爆竹声。
荣辱更迭,兴亡谁定,年纪本就大了的曹由气急攻心,没几天就一命呜呼,而曹惜礼则失去了踪迹,但是多年后有人说见过他,在孤山。
据说他身边还有一位女子,两人作农户打扮,布衣补丁重叠,俨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两人一块儿坐在梅树下看花儿,女子还买了一串糖葫芦,特意叮嘱小贩少放了饴糖。
两个人脸上的笑,都很美。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不足以记在历史上了,时间回到今日,江南,钱府,停留些日的东宫启程回京了。
东宫因为阻止立妻一事不要命地赶到江南,所伤的元气和精神都歇回来了,圣人还下了口谕,让他走水路回去,少些颠簸,慢些也无妨,政事反正都耽搁了,也不差这几日,老子到底还是心疼儿子的。
所以这日,程英嘤看着长身玉立的赵熙行,看得心喜,男子倦色一扫而空,脸上也不再敷脂粉遮掩,本就是天容玉色的模样,如今往杨柳码头一站,云朵都围着他打转。
“东宫回去了,哎呀,可惜,再瞧不见这么好看的脸了。”
“这歇几天把精气神歇回来了,整个人就愈发俊儿了,哼,便宜那花氏了。”
周围跪拜的百姓窸窸窣窣,尤其是小娘子们,硬壮着胆拿眼偷觑,脸红了一片,正可谓美色当头,一把刀,圣人的规矩也不怕了。
程英嘤比赵熙行先一步注意到这些目光,几声轻咳,端起良家子的架子,吓倒是把那些小娘子吓住了,码头边重新肃穆起来。
“赵沉晏,你这回去没几天,圣驾也该启程回……你看着我作甚?”程英嘤转头和赵熙行说话,却见男子瞧着她,憋笑。
赵熙行唇角弧度更大,俯身,低头:“看本殿的良家子吃醋呀。”
“呸,大庭广众的,耍什么滑头。”程英嘤板脸,慌忙瞧了四周一眼,确定没人听见,才忍不住一笑,“我跟你说正事呢,圣驾铁定要在下雪前回的,说不定你前脚到,我后脚也到了。”
“你就这么盼着回京?”赵熙行眉梢一挑,意味深长道:“是了,良家子只是未侍寝前的封号,等正式……”
“哎呀,你再胡说!”程英嘤立马耳根子发烫,轻轻一跺脚,又想骂他,又怕周围听见,憋得脸皮都红起来。
赵熙行则有些委屈:“本来就是嘛,封良家子你亲口应了的,万不得反悔。”
程英嘤词穷,心里藏了一只小猫似的,不停的挠,多的话没有,自己就想到天边去了,于是连看都不敢看赵熙行了。
忽感到一双手轻轻的按住了她肩膀,宽大的掌心,温厚的,又似乎有些烫,她抬眸撞进深渊般的黑眸,隐隐燃起了火。
“鸳鸳,你听好了。”赵熙行声音沙哑,压得很低,“本殿只是暂时,暂时的,让你做一下良家子……希望待回京,你准备好了。”
程英嘤脑海里轰一声,整个人在原地都站不稳了。
再一回神,缃袍男子就已登舟远去,消失在碧波尽头,徒留下耳边小娘子们的叹惜,闹嗡嗡的,梦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