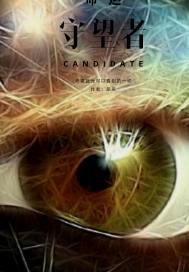打开门,见风尘仆仆的沙陈宝买了很多吃的东西递给阿姨,站在门口跟兰老板打着招呼,说厂子里有事需要处理,得马上回去一趟。
这会儿,他看见我坐在房间里,转身要走的他又回过头来若有所思的说道:“大姐,外面挺冷的,我开车稍你回去呀,顺道。”
我朝他点点头,接过阿姨手里沙陈宝买的东西放在客厅里时,无意间瞥见大嫂那久违的一撇嘴样子跟发出轻微的“切”声。
我跟这一会儿咳嗽得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的兰老板告辞,叮嘱门口的阿姨照顾好她们的同时照顾好自己,跟着沙陈宝一道儿出来。
长长的透了一口气,楼梯间里似乎飘着一股烂酸菜味儿。
这一时,电梯里的沙陈宝对着电梯的按键吹着口哨,随心所欲的一种曲调,似是茫茫草原上养鹰的人,在用哨音叫回盘旋在高空之中的老鹰。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幻想着听他无意间跟老丫谈起小时候一直在草原上骑着马赶着羊群放牧,遇到了雷暴的天气,大草原上无处躲藏的他,追逐着到处“抱头鼠窜”的羊群的场景。
当雷暴走远,看着眼前只剩下一半的羊群跟被雷电霹中躺在草地上烧焦的很多只羊,身体上还冒着烟火,年少的他欲哭无泪。就如同山坡上的放牛娃,忽然躺在山坡上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牛放丢了一样的无助。
这会儿,从楼里出来,街头清新的空气裹着一种淡淡的香甜味,不远处一家做无水蛋糕的小店门前人头攒动,排起了一条长龙。
“大姐你看,人家的生意有多兴隆!”沙陈宝用左手指着说道。
“哦,你也是!”我说。
他哈哈的笑着说:“我也是?”
“是啊!你当然是,不过早一天晚一天而矣,在我看来。”我说。
“借大姐吉言,兄弟先谢过大姐!”说罢,他跟我深深的一抱拳。
一路上他风驰电掣的把我送回到店里,进门时,我抬头看了看墙面上的表盘,时针跟分针完完全全重叠在一起,形成一条直线笔直地伫立在表盘的正上方。
老丫早已经吃完了饭,我找出来一碗泡面泡上。忽然,身着黄背心的外卖小哥喊着我的名字走进来,送来了两盒冒着热气的三鲜馅的饺子,还有一小盒酱油跟蒜汁放下便走了。
“你订了外卖还泡面呀?能吃了吗?”老丫跑过来说。
“喂,吃货的眼睛里只有看到了吃的东西才放亮闪光,对不对?叫出来香菇姐一起吃。”我说。我打趣着老丫的同时,知道这件事一定是沙陈宝干的,除了他没有别人。
她们俩的嘴可真壮,在吃饱了中午饭之后,俩人还能合伙吃上一盒饺子跟半下泡面。
这会儿,看着空空如也的盒子,一直在问我:“你吃饱了吗?你吃饱了吗?”像极了食堂里打盒饭的那位大师傅,一边不停地抖落着勺子,一边不停地寻问着你“够吃吗?够吃吗?”这算不算是一种明摆着的气人法儿,我也不知道。呵呵!
晚上,窝在被窝里看着妮子发来的视频,假装跟她一起沐浴在南方的暧阳里。
转眼,看见杜鹃跟香菇姐在群里叽叽喳喳的议论着什么,依然是那股子鲜活乱崩的劲头,像极了一只快乐的小鸟。
看着她发过来的照片,头顶上戴着一顶遮阳宽沿帽,站在云南的小集市上,脖子上扎着一摞各色的花围巾,戴着耳麦高声的叫卖着。似乎从一段破裂的婚姻感情之中走出来的杜鹃,一如一朵灿若云霞的杜鹃花。
"云外青山树外楼,雪花飞缀景偏幽。"
第二天的午后,窗外飘起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飘洒洒。仿佛是一片片沟通天地间的精灵,徐徐飘落至眼前,如杨花细,似梨花白。
“梨花输雪一段白,雪输梨花一段香。”
但见先是一片、二片,后是七片、八片,在就是漫天雪花,数都数不清。小广场的地面上,瞬间铺起一层纯洁的地毯,纯洁得就象山谷之中的百合花。
冬日的天空,这会儿,只为雪忙。
这一时,我正在望着雪景发着呆,贺龄玲打来了电话,说派她的助手小微送样板来了。我说雪下得这么急,等等吧,她说人都快到了。
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小微白白净净的一张小圆脸,理着很短的头发,染成焦糊的那种黄色,活脱脱地一个假小子,听贺龄玲说她特别能干活。
贺龄玲一心想把未曾结过婚的小微介绍给她离过婚的大哥,然后,小微一进门就当妈,贺龄玲如卸重负的喊她一声大嫂!
我心下暗想,人家小微能乐意吗?你大哥那模样跟黑旋风李逵似的。是否忘记了,上一位大嫂是怎么被你大哥捶跑的了?
这会儿,老丫一边儿帮小微拍掉身上的雪花,一边儿接过去她手中提着很重的样板。我给小微倒了一杯热水说:“小微,也不是什么急事,你顶风冒雪的急个什么?”
“雪下得大,在工厂里也没啥事,慢慢开过来的。还行,我这水平还没有凹到掉沟里边去。”小微说笑着。
“小微,这一段时间老秦在你们那里工作得怎么样了?他还好吧?”香菇姐忙凑过来问。
“嗯,秦师傅早就放假了,可能得放到年后吧!放假前,我们老板不是跟你们老板商量了吗?你们不知道呀?”小微说完,若有所思的用手抓着头皮。
“啊,我们老板不是病了吗,病得还挺重的,一直也没有到店里来。”老丫说。
“哦!她好点没有啊?我听我们老板说了,咋突然病得那么厉害呢?”小微说。
很对贺龄玲心思的小微,是个漂亮的女孩儿。
“唉,小微,你啥时候给你们贺老板当大嫂啊?到时候你准备在今天这样的好天儿,指示她做点什么事啊?”我跟小微开着玩笑说道。
小微立刻就似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蔫吧了!然后,寻思了一会儿,蔫头耷拉脑地学着贺龄玲的声调说:“小玲啊,你开车去东边的菜市场给我买点青菜回来,你把菜揣怀里带回来,冻硬了可不行啊!然后,在去西边的面食店给我买五个二合面地、五个三合面地,五个豆面地大馒头,记住了,你哥就爱吃冒热气地,别买错了!”
哈哈哈,大家一阵哄笑,笑点很低的香菇姐,这会儿却只是咧了一下嘴。
时间自是过得飞快,捻指半个月过去了。
这天的大清早上,兰老板穿着一件几乎拖到地面的深蓝色超厚羽绒服来到了店里,惨白的脸色把那些蝴蝶斑映衬得更加明显。她的病需要时间静养,看来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静养。
我用最简短的语言跟她汇报了店里的一些事情,她点了点头。喉咙里好像总是憋着一口痰,发出呼噜呼噜地,来回拉着风匣一般的声音。哎,反正感觉她的身体极其的不舒服。
这时候,沙陈宝跟马凤一起走了进来。也就一个月没有照面的马凤胖成了个球,跟在走起路来脚下生风就要起飞的沙陈宝身后,好似是车的轮胎在地面上来回的轱辘一般。
虽然,他们俩夫妻跟兰老板的相识时间并不长,但我预感到他们的确感动了兰老板一把。
如果,接下来兰老板又动了养病租兑店的心思,那么,在大哥跟沙陈宝还有贺龄玲之间,或许,沙陈宝的优势会更多一些。
我在胡思乱想着,没有注意听他们坐在一起聊着什么。这会儿,马凤走到我跟前说,你们大姐说让你给泡杯清淡点儿的茶水,她要喝。
“哦,好!”我答应着,连忙泡茶。
当我把一小杯茉莉花清茶放在兰老板面前的桌子上时,看见老丫冲泡的咖啡已然是凉了。我把咖啡端下来放在一边上,跟老丫说,她嗓子不好,喝不了甜的东西了。老丫就又从桌子底下的纸壳箱里拿出来几瓶矿泉水放在桌子上。
遥望着窗外小广场上的地面,保安已经把雪都清理到一边上,中间露出了花岗岩石头的原色。
少了花坛里五颜六色的花朵,取而代之的是皑皑白雪覆盖着的一层棉被,几根高大的枯枝在阳光下,了无生机的摇动着。自西北而来的寒流冷得让人透不过气儿来,这会儿。
那个爱跟在兰老板身后头说笑的保安,这会儿,身体留在门外,整个一个大脑袋伸了进来,来回翻动着大眼珠子,费劲地说着让兰老板挪挪车呗!
搞怪又滑稽的他,看见兰老板因想跟他说话憋红了脸,一阵急促的咳嗽,嗓音都要咳破的动静后,转了转大眼珠子,悻悻而去,可能这几天之内不会再来了。
沙陈宝跟马凤一边说着保安的滑稽相,一边自动自觉地出去挪车走了。
不一时,听见在走廊里传过来沙陈宝跟大哥说话的声音,果然,大哥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羽绒服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迎面奔着兰老板而去,数落着她天冷来店里来做什么?有事不是还有他呢吗!
这会儿,一根筋的老丫在冲泡着一杯很淡很淡的咖啡,她觉得兰老板爱喝咖啡,不加糖,冲得又很淡,是不是就能喝了呢?
她没有喝老丫端过来的咖啡,笑着说:“宝贝儿,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傻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