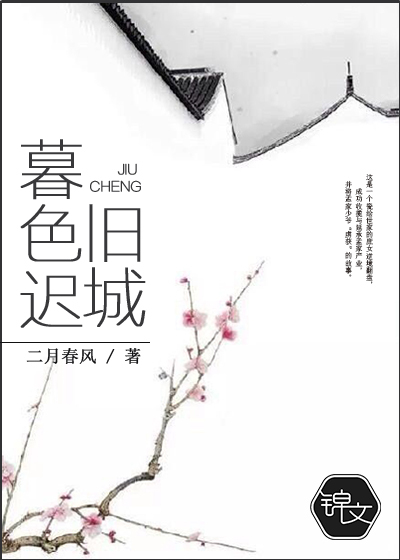一面害怕着,一面愧疚着,真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情,但思卿再也不动让人走的念头,因为更怕对不起自己的心。
潘兰芳知道姜雅容没有怀孕,剪碎了新做的衣服,打跑了新请的奶娘,长生锁弄不坏,只好丢到门外边去,然后她重新把自己关在了祠堂,继续看列祖列宗的牌位。
她已经满头白发,偶尔想,自己也太能活了,怎么他们都死了,自己还好端端的呢?
姜雅容不信思卿的承诺,她还得去找怀安,非要把怀安的旧情给唤出来,好保证自己能够有个依靠。
但她又做不来撒泼打滚的事儿,暗暗使一些小手段,只是唱独角戏,压根引不起关注。而且,她发现,怀安与思卿之间太信任了,不管她怎么离间,那两位连解释都不用,因为根本就不会产生误会。
这种信任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只是因为爱情吗?
她使尽了浑身解数,半点用没有,自己也技穷了,回过头发现,自己这么多幺蛾子明明全都被看得清清楚楚,孟家上下却没多说一句。
除了顾盈月偶尔会瞪她两眼,可是在她夜晚不舒服的时候,顾盈月还起身来照顾过她。
她慢慢不想再闹了,可是安静下来,又觉得人生没了盼头,日子过得没什么生气。
为什么会活成这个样子呢,一根稻草抓不住,余生就全都没希望了吗?
云儿终于把想说的话跟她说了,云儿说,离开吧,不要再打扰孟家了。
她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困惑:她漂泊了很多年,不想再回到那种居无定所的日子。
找一个地方住很简单,拥有家人却是奢望,可她太需要家人的陪伴了。
她直截了当地拒绝:“我不走,我要留在这里。”
“小姐,二少爷不愿意娶你,你是个外人,为何非要赖在别人家里?”
“外人?”她嗖地起身,“早晚会变成‘内人’的,不信,走着瞧!”
为着让自己的生活有支撑,她得继续闹下去,变本加厉地闹,把孟家闹得鸡飞狗跳,就不信没人关注她。
她隔三差五地故意磕着碰着,把自己弄伤,可怀安不来,思卿替他出面给她请大夫,她换了招式,主动出击去西园给怀安送饭,她知道思卿也在,就等着思卿劈头盖脸给她一顿骂,她好在众人面前做出委屈状,可她一去,思卿就退出了,直接把场地留给她,一点儿也不跟她争,她的计划就实施不出来了。
再后来,她另辟蹊径,决定不装可怜,而是把自己变得讨厌,那样总可以被关注了吧?
她开始挑吃挑穿,挥霍无度,还动不动就打骂孟家下人。
这一回,潘兰芳终于有些微词,说了她几句,可怀安与思卿仍然没反应,只要她花费不是太过分,就由着她。
她每天都生事,如愿以偿地把孟家闹得乱七八糟,怀安思卿和顾盈月白天都不在,潘兰芳每天都得过来给她收拾残局,起初的礼貌与讨好全都没了,一见着免不得要教训几句,几次动过要把她赶出去的念头,可是还留着她会生孩子的念想,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慢慢地,潘兰芳收拾残局都收拾习惯了,祠堂也没工夫去了,每天都在想着如何管束姜雅容,如何安抚下人,如何把孟家这被搅和的七零八落的事情给理顺。
不知不觉,她竟发现,时间比以前好打发了。
偶尔,两个人急赤白脸累了,也能坐在廊檐下,看着庭前的花草,好生说上一会儿话。
年年岁岁花相似。
孟思汝与欢儿再没有回来,可有人站在孟家门口大声说在外地见过他们,母女两人聚到一起了,开了店做起了生意,模式仿照思卿以前在向家小院附近开的那个惊鸿馆,专门为女子提供一个艺术展览的平台,听说生意还不错。
至于究竟这外地是哪儿,这人却说:“我哪儿知道啊,就只是碰见过他们一回而已。”
“你对他们聚到一起,开了惊鸿馆都了解,竟不知他们在哪儿?”顾盈月问。
“就是不知道呗,再问也不知道。”那人说完就走了。
思卿拉住还要追上去问的顾盈月,笑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只要过得好,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吧。”
顾盈月叹了口气:“我还没见过有家不想回的人,我只听说过,有家不能回的人。”
她回到院子里,眼看着院子里的梅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
孟庭安收到的信中,只剩下“皆安,勿念”四个字。
他希望往后一直都只有这四个字,只要皆安,其他的,就全都放下,当真勿念了吧。
青龙帮的老大阿唐又来了浔城,他还没死心,听说孟思亦如今已经不大受欢迎了,他就又来找孟思亦,想要她跟自己走。
其实不单单是孟思亦一个人不大受欢迎了,而是整个小凤楼的角儿都不大行了,这跟他们没关系,主要是没多少人还有钱和精力泡在戏楼里。
陈掌柜入不敷出一筹莫展,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那孟思亦正在戏台上耍花枪呢,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轰隆一声,戏台子倒塌了。
台上台下顿时乱成一片,所幸人都没事儿,陈掌柜赔了客人的钱,还得收拾烂摊子,不巧这晚又下雨,一行人焦头烂额地忙到天亮,雨一直没停,陈掌柜顶着湿漉漉的蓑衣,脸上布满了灰,心里不舒服,懒得挪动,就坐在雨中啃馒头。
然后看见一行侍卫沿街狂奔,踏在雨中的靴子溅起水花,再重重砸到地面,迸散成四分五裂的水珠。
“发生什么事了?”他放下馒头,伸长脖子看。
这一看,发现大街上很多人都打开了门窗,和他一样伸长脖子往外看着。
每个人眼中都带着困惑和迷离,但是没人敢说话,天上的云压得深,笼罩着底下的侍卫们,好似屏蔽了一切杂音,只有这让人将要窒息的踏步声。
远处寺庙忽有鸣钟传来,惊了探头的百姓们。
乍听街上高声悲吟:“皇上驾崩啦……”
雨点砸碎了所有人的声音,街上那一声长吟,伴随着远处的鸣钟,猛地敲在人们的心间。
陈掌柜手里的馒头掉在雨地中,他回头看着还没搭建好的戏台,想:“得,搭不成了。”
大丧期间禁铸造,禁文娱。
新帝三岁登基,太后尊太皇太后。
还没喘口气,翌日,长街又报:
“太皇太后薨。”
所有人停下动作,一时没反应过来。
小凤楼的戏台彻底搭建不成,戏也唱不成了,角儿们都各自谋出路去了。
阿唐去找孟思亦的时候,正看见陈掌柜晃晃悠悠地踩着梯子,将那门上的牌匾慢慢摘落,摘完后,他小心翼翼拂了拂上面灰尘,回头对阿唐苦涩地笑。
孟思亦当初说,除非戏台上不需要她,否则她要一直唱下去,可惜,还没等到不需要,那戏台已经没有了。
她终于松口答应跟阿唐走,阿唐还想带着无处去的陈掌柜,但陈掌柜不肯走,他在浔城过了一辈子,在别处住不惯,他说自己有积蓄,饿不着,阿唐只好作罢。
走之前,阿唐邀请怀安夫妻以及向浮一起吃饭,孟思亦不愿意见孟家人,不肯露面,他只能自己来,他在席间终于能正儿八经地叫怀安一声二哥,兴许孟思亦已经不认这个亲了,但他叫得高兴。
可是向浮不大高兴,阿唐敬酒他一杯也不喝,只抱着双臂瞪眼睛,他以前就想不明白阿唐为什么对孟思亦情有独钟,那个刁蛮丫头,在他眼里没有一处优点,当然每个人眼光不同,情有独钟也就罢了,人家明摆着压根就没喜欢过他,要不是自己混不下去了,此次也未必会跟他,他这么长情还这么痴情又是为什么呢?
阿唐知道向浮的不悦,他最近在学文化,饮下几杯酒后,想在几人面前把话说得文气:“世人皆笑我痴心错付还不知悔改,可我少时心动就一直心动,我见着她一次就心动一次,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了她,再没有任何人让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认定了她,这心动让我浑身上下都得劲儿,舒坦得不得了,啥子值不值得,讲究那多干嘛,管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乐意对她好,我对她好我心里痛快,痛快不就得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向浮还是不以为然,他没觉文气,只觉酸气。
但说到底,孟思亦这么一走,大概就不会再回来了,虽然她一直也没回过孟家,可始终在浔城,好似还在跟前,而这一次,是真的远离了。
孟家,又离开一人。
阿唐原本还想逗留几日,可突然遇到急事,当天便匆匆携了孟思亦离开浔城。
向浮刀子嘴豆腐心,离开时去送了他们,他神色匆忙,吊起了向浮的好奇心:“什么事儿那么急?”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广州那儿有人抢生意。”阿唐抹着嘴角道,“日本商船当着我的面搞私运军火的勾当,老子还活着呢。”
他边搀着孟思亦上车,边继续道:“广东水师李大人要与我合作一起扣押商船,你说说,我好好一黑帮,怎么干的尽是他们的活啊,不说了,我得赶紧走了啊。”
“好,那你小心。”向浮一听广州就有些忧心,他弟弟向沉在广州,叫他回来就是不回来。
喜欢旧城暮色迟请大家收藏:()旧城暮色迟53中文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