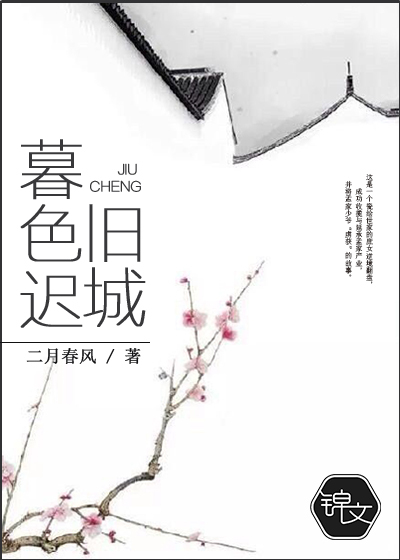睁开眼已是过了四五天。
外厅站了不少人,家中女眷多,却都是不方便进来的,几个小厮近身照顾,还有个碍眼的人坐在茶几旁,瞧他醒来了,慢腾腾地挪了过来。
这家伙两眼圈像是被人给揍了一样,乌黑乌黑的,让人一看就扫兴。
床上的人环顾一圈,撑起身子,劈头盖脸问:“思卿呢,你把她弄哪儿去了,怎么还没回来?”
“在医馆。”程逸珩实话道。
“什么……”
“你别激动!”他连忙按住他,“没多大事儿。”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程逸珩转了个身,躲过他的目光,“那天她非要留下来陪你,我觉得太危险,就……把她敲晕了,对,就是这样。”
“你……你敢打她?”
“我又不是故意的。”
“敲一下,晕了几天?”
“嗯……留下再观察一下么,免得有后患,你好好躺着吧,我现在去帮你接她。”他迅速向外走去,回头间见床上的人要起来,又连忙道,“别别别,你不要一起去了,我那轿子坐不下,而且别让我还得分心照顾你。”
不必要添的麻烦,的确不能添,怀安纵然焦急,但此事,是信得过这个家伙的。
这些年两人打打骂骂,数次决定分道扬镳互不往来,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要一碰面,“恩怨情仇”就都忘干净了,说起来,身边诸多好友,唯有这位,依然是托妻献子的交情,不管他做了什么。
医馆的药味呛鼻。
思卿瞪大眼睛看着天花板,但听得外面有敲门声,她轻轻叹了口气,起身将外衣穿上,打开门,迎面见程逸珩慌里慌张地喘着气:“我按照你说的,不让孟家人知道,现在他可醒了,要是他过来就瞒不了了,你要回去吗?”
“回,我没大碍了。”思卿点点头。
“那我安排人送你。”程逸珩往她脸上打量了一下,“真没事啊?”
“没事。”
“你这……为什么不打算告诉他们啊?”
“已经没有了,何故还要招人心伤,那不是添堵吗?”她道。
这好像也有道理,她在医馆这几天,程逸珩帮她打探怀安的伤势,两边不停地跑,亲眼看着那孟家人把怀安围了个水泄不通,却没人想起来问她去哪儿了,还是欢儿那小丫头问过一次,他当着孟夫人的面说得明明白白,告诉他们思卿病了,暂时留在医馆观察,而当时那孟夫人道:“呀,那我赶紧安排几个丫鬟过去照顾,回头等怀安醒了,我们就去看看她。”
当然,她一直都没来,思卿这也没让丫鬟过来。
孰轻孰重一语透彻,连亲生不亲生都没关系,倘若叫那唯恐孟家无传承的孟夫人了解她的病情,那真真是极其添堵,想一想就知道,她一哭二闹定是免不了的,没准还要三上吊。
程逸珩憋了半晌,摇摇头,向她郑重道:“行,我也不会多说的。”
很快,她被送上那顶红轿子,七八个人抬着她往孟家回,前后亦有兵丁开路,行在街上,惹来不少目光,一瞬间好似回到了当年出嫁的风景。
只是当日从孟家离开,今日,花轿徐徐,却又是朝着孟家而去。
孟宅门前,有人披着衣服翘首以盼。
见他紧张神色,思卿则更加慌乱,虽然已决定不告诉他,可这病容是隐藏不了的,又该如何解释呢?
轿撵停在孟宅大门前,一只手掀开轿帘,向她递了过来,她满怀心事地牵住他,慢慢低头走出,走得一步一软,仿佛踩在棉花上,使不出力气。
但好在走得慢,旁边的人应该察觉不出异样,她侧目看了看,不露痕迹地又放慢了一些。
还没跨进大门,忽而一手覆在腰间,一个用力,把她抱了起来。
她慌了一慌,不知他是否看出了什么,而又想到其他,连忙问:“你的伤还没好呢,别又……”
“无妨,抱你还是绰绰有余的。”怀安的语气温柔,可是面上未带丝毫笑意,只是板着脸道,“太过分了。”
她心一惊:“什么过分?”
怀安低头盯着她的脸,左看右看,咬牙切齿:“程逸珩那小子敢打你,还不过分吗?”
“哦,那算什么打?”她松了口气,仍担心他的伤情,“你还是放我下来吧,我能走。”
“我喜欢抱着你。”怀安这才笑了笑,在她额头轻轻吻了一下,虽然眉宇间有些疲倦,但面上是少有的轻松,“跟你说哦,大家不会再找我们的麻烦了。”
“真的?”
“对啊。”他的目光闪闪发亮。
她也笑起来,更觉有些不开心的事情,还是一直不要说出来为好。
怀安一直抱着她,直到走进前院,碰上思汝与欢儿出来,才放了她下来。
那对母女捂着嘴偷笑个不停,直直笑得两人都红了脸,怀安没好气地拉过欢儿,攥着她的辫子道:“小孩子不该看的不要看,知道吗?”
“什么小孩子啊,我十五了,是大姑娘了。”欢儿不满地道,“二舅舅你们不用害羞,我又不是不懂,你们俩这样好,也能早点给我添个弟弟或者妹妹不是?”
此话让对面两人静了须臾。
思汝要插话,还未开口,却听欢儿又道:“这不是我说的,是外祖母说的,外祖母天天念叨,说什么别让那啥算命的给说中了,老说你们为何还不要孩子,又不敢在你们面前说,就逮着我们这些人絮叨,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我觉得,外祖母简直是不大正常了,原本还要打我娘的主意,为我娘又说了几门亲事,全都是歪瓜裂枣,好歹让我拦下来了,对了,你们说,那算命的说孟家无后人,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怀安道,“我说你这孩子,可真是‘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啊,什么陈年烂谷子的谣言都能被你打听出来,怎么没后人,我们的欢儿难道不是孟家人吗?”
欢儿努努嘴:“外祖母才没这样觉得,不过无所谓啊,反正我也不姓孟,我姓洪。”
这话让怀安咂舌,他都快忘记她姓洪了,想当年,这是大姐唯一一次不肯听孟家的话,非要欢儿随了洪轩的姓。
一旁的思汝听他二人说话,却不见思卿发言,她觉得思卿脸色不太好看,忙拉过欢儿道:“你外祖母信那些,你也要信啊,你不是自诩新学堂的新女性吗?”
“那倒是。”欢儿听此话,郑重点点头。
却听旁边“噗嗤”一声笑。
她回头一瞪:“二舅舅,你笑什么?”
“还新女性,明明就是个小丫头。”
“我再说一遍,我是大人。”欢儿气得脸通红,“二舅母当初回孟家的时候不就跟我这般大,她那时候都能说亲事了,怎么我还是小孩呢?”
“嘿,你这小孩,一天到晚都关心些什么啊?”怀安挽起袖子佯装要揍她,她做了个鬼脸,嬉笑着跑开了。
思汝不想打扰他二人,向他们笑了笑,也速速离去。
剩下二人于原地静默了片刻,刚才的话虽然来自小孩子的戏言,但也不得不让听者上了心,半晌后,怀安方问:“你……怎么看?”
思卿的眼中闪过一丝悲切,心中杂乱无章,她说不出心平气和的话语,只能掩盖住情绪,反问:“那你呢?”
“我……”怀安见她神色,以为她因刚才的话不痛快,便道:“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给我们养老送终,他有自己的人生,不应该是带着任务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不用顾及外界所言。”
此话让她心中一暖,她轻轻笑道:“以前没拥有过,不觉得,现在,我其实有些舍不得了。”
“舍不得?”对方没听懂。
“舍不得我们百年之后,没有后人来替我们看看未来的世界,我们代代拼搏与努力,为了什么呢,若无人为我们留下一点痕迹,又如何证明我们存在过?”
“你的想法……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了,因为我看到,一个生命的终结实在太容易了,人生不过几十年,这只能叫做人生,而世代相承,才是延续,那才叫生命。”她往前几步,扑到他的怀里,将脸埋在他的胸口,轻声道,“我们再……我们要一个孩子吧?”
怀安有些困惑,觉得她今天比以往多愁善感了许多,但他什么也没问,将怀里的人抱紧:“我早就说过都听你的啊,那时我已发誓,若有违背,就让我垂暮犹离索,永久有效哦。”
抱了一会儿,他才道:“那天,你是要跟我说什么?”
她无奈地摇摇头:“我忘记了,等想起来再说吧。”
这话有些似曾相识,怀安记得数年前的夜晚,那时候,他们还没离开孟家,她挽着他的胳膊,从瓷艺社回去,也是这样说:“有些话,等天亮以后再说吧。”
可是后来,那话就再也没说过。
没说出口的话,就成了秘密。
医馆里,程逸珩还没来得及走。
有一大夫过来,往他身后病房里望了望:“人呢?”
“回家了。”他答,“还有事?”
大夫紧皱眉头向他看:“尊夫人……”
“不是我夫人。”
“……”
“是我妹妹,你有什么话尽管告诉我。”
大夫松口气,道:“令妹年岁不小了,这身子骨儿本身就不比年轻人,你可要跟家里人说,下次要是再有孕,一定得万分注意,稍不留神就会有危险的。”
“嗯,哦,知道了。”他对于这种事儿不好过问太细,也没有严重不严重的概念,糊里糊涂地点头。
“还有,人虽可以出医馆,但一个月内不能吹风,不能沾凉水,不然会留下病根。”
“哦哦哦。”
“另外,你要跟你妹夫说,至少半个月不能同床。”
“哦哦哦……嗯?”他往后一跳,“这种事我怎么说得出口?”
“这是正常医嘱,用得着谈之色变吗?”大夫瞥了他一眼,“你也有妻与子吧,你要明白,生育是伟大的,不应该觉得羞耻。”
他继续迷迷糊糊地点头,心不知道飘向了哪儿,闷声回应:“我没有妻与子。”
“早晚会有的啊,我现在说的关于生育问题,你先听一听,也能有个经验。”
他转了个身,缓声道:“不用,不会有。”
……
千里重洋,山长水阔。
罗兰艺术大学位于法国的浪漫之都,历史悠久。
一位短发女子抱着几本书,疾步走在校园的林荫路上。
才走几步,有伙伴追了上来,这伙伴是本地人,说出的话语在短发女子耳中,自然翻译成了自己的语言。
那伙伴道:“密斯沈,你要去找院方签字吗,顺便帮我跟我们教授说说好话,你知道,我根本就不是画画的料,我已经很努力了,就是达不到他的要求,我也没办法啊。”
密斯沈笑道:“可你们教授我没见过啊,谁知道是不是好说话的人?”
“他跟你一样,是中国人,你们都是那什么……龙的传人么,肯定比我好说话。”
密斯沈只好耸耸肩:“那我只能试一试看喽。”
她继续转身向前走去,走了几步,又回头望眼前的路,一片绿荫,将阳光撕裂成柔软的碎片,落在来时的脚下。
来的时候,只是打算学一学工艺制造,却未曾想能有机会进入大学进修。如今故园不平,她一己之力纵不能翻江倒海,但也愿意化成那江海中一颗渺小水滴。于是她递交了退学的申请,今日来找院方签字办手续。
顺便,受好友所托,帮他找那位同宗的教授求求情。
手续办好后,她在指引下找到了那教授的办公室,敲门而入:“孟教授,我来替……”
喜欢旧城暮色迟请大家收藏:()旧城暮色迟53中文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