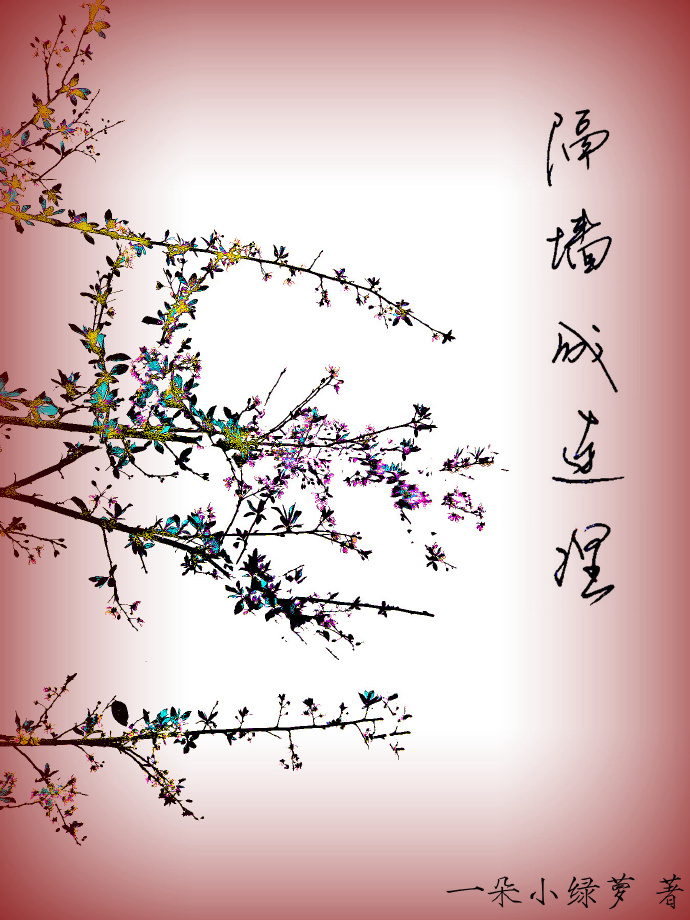淮楼将那人带进地洞里绑起来,点了穴,那人便呻|吟着转醒。他拍了拍秦戊的肩膀,走出了地洞。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这人应该就是那个下毒的凶手。他耳背后那道疤,很明显是曾经被逐出药王谷强行挖除的一株草药形状的刺青。
那是药王谷的人特有的标识。
赵全觉得后颈疼得厉害,想伸手去揉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着。他像一条蛇般在地上蹭动,刚想开口呼救时,眼前出现了一双鞋。
地洞很黑,勉强仰着头看上去,赵全并不能看到什么,只能从鞋子的样式知道这是个男人。
秦戊点燃火折子,攸地蹲下身凑到赵全面前,高热的温度竟让他打了个冷颤。
他看到眼前的人,面容俊朗却没有丝毫表情,看他的眼神冷得可怕。他听到那人幽幽叫了一声“陈方”,浑身都开始冒起了鸡皮疙瘩。
陈方,是他十五年前的名字。自从那件事后,他被四处追杀,费尽心力才侥幸逃脱至此,活了下来。
秦戊看到他瞳孔急剧收缩便知道是这人无疑,他淡淡开口:“你还记得你的表哥李卓强吗?十五年前在柴府做厨子的那个表哥。”
赵全浑身剧烈颤抖,“你是谁?是大人派来杀我的吗?”
秦戊心中一动,接着他的话说下去:“你已经多活了十五年,是时候走了。”
“大人,求大人开恩。我不会说出去的,我这十五年来没有泄露过半个字,大人饶命。”赵全挣扎着想爬开,却只能在原地乱蹭。
秦戊从他身上取下佩刀,银白的刀身,在火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凛冽。
“这话你就留着去跟你表哥说吧。”
“不要,你不能杀我。”眼看着刀已经靠近喉咙,赵全拼尽全力闪到了一旁,颈部被划出一道血痕,冒出细细微微的血珠。
“你若是杀了我,你一定会后悔的。”他惊魂未定地喘着粗气,“我找画师,把曾经跟我接头的人画了下来。如果我婆|娘三天后没有见到我,她就会立刻把画像交到官府。”
秦戊冷笑一声,“当初和你接头的,不过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你以为报官就能奈何得了大人吗?”
他用刀身轻轻地拍在赵全脸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子,“别怕,很快就过去了。”
“我知道画像没用,但我自然是有你不能杀我的东西。”赵全看到秦戊收回了刀,心下舒了口气,“虽然那人并不重要,但我以前在皇家医馆捡了五年的药,我能清楚地闻出来他当时身后跟着的那位仆人身上的味道。”
他停顿了一下,看秦戊并没有再举刀的意思,知道他已经死不了了,才继续道:“那是常年接触名贵药材的人才会有的气味,除了宫中的太医,绝不会有第二类人。”
“所以,你想要如何?”秦戊问他。
“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大阴谋,但我对那些没兴趣。你给我十万两黄金,我带着我婆|娘从此销声匿迹,担保再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这事。”
“可我只相信死人说的话。”秦戊又重新举起刀,对着他冷然一笑。
“我这些年鼻子越来越不好,所以一直让我婆娘记住那味道。如果她见不到我,会直接去找左相大人,向他禀明一切。届时,以左相大人的为人,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赵全咽了咽口水,抛出了最后的一块救生浮木,“这世上,除了我,没人能找到我婆娘在哪。”
“是吗?”秦戊轻笑一声,嘴角扯出一抹苦涩,“你当年被人收买,用飞煞毒死柴府上下一百零五条人命,虽不是你主谋,但事实确实是你没能经得起诱惑,白白残害了一百多条人命。”
“你不杀伯仁,伯仁却是因你而死。”
“你还是让你的娘子来找我吧。”
秦戊刚打开门走出地洞,便跑到一边呕吐起来。
胃里空空荡荡,只能不停地吐水,到最后已经连水都吐不出来,只能不停地干呕。
淮楼已经在第一时间给秦戊梳理了气息,却还是没能缓解他的症状,只能在一旁不停地顺抚他的背。
等秦戊稍微缓过来了些,他便带着他一同离开。走之前,在地洞放了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一切。
有的没的,统统都消失不见。
万俟安和吴亨交手的时候受了点轻伤,此时正在上药。
他看到淮楼带着秦戊进门,还急急忙忙地到了杯温水给秦戊,心下奇怪,“阿戊兄弟这是怎么了?”秦戊慢慢地喝着水没说话,淮楼坐在一旁道:“看到了些恶心的东西。”
万俟安“噢”了一声,随即一脚踢在绑在地上的吴亨,“对,都他|娘的是恶心东西。”
淮楼看了看秦戊,发现他的脸色稍微好了些,便对万俟安说:“通知官府过来抓人吧。”
“已经派人去了,估计还得过两天才能到。”
“好,那我们先回房休息。”淮楼不再多说,扶着秦戊随便找了间房间进去。把秦戊带到床边坐下,淮楼摸摸他的头,柔声道:“想说点什么吗?”
秦戊闭了闭眼,半晌才开口:“我杀了他。”
“你为父母报仇了,他该死。”淮楼一下又一下的抚摸着秦戊的头,带着他特有的气息和节奏安慰着这个惊慌失措的孩子。
秦戊转过头看着淮楼,望进他深邃的眼里,温柔和怜爱一览无余,让秦戊混乱的心绪就这么缓缓平静下来。
他无法等到官府来人将陈方抓进大牢,无法克制自己看到那个陌生又熟悉的面孔而产生的滔天怒气。
他小时候见过陈方,但是记忆已经很模糊了。刚才看到他的那一眼只是觉得有些熟悉,直到后来看到他耳背后的疤痕才确认这人就是老谭的那个徒弟,陈方。
陈方不傻,他为了活下去,也确实是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如果他真的遇到幕后主使派出来的杀手,在找到他娘子前,至少他是可以多活些日子的。
只可惜,他遇错了人。
他认为盛国最义薄云天的左相大人,反倒是那个最想让他死的人。
“淮楼—”秦戊刚一开口,就被他打断,“叫我景绥吧。淮楼是名,景绥是字。”
“景绥。”秦戊顿了一下,定定地看着淮楼,“你能不能再陪陪我。”
被心上人如此脆弱地需要着,淮楼只觉得整颗心又酸又甜的。
他温柔一笑,低沉的嗓音砸在他的心湖里,漾起细细微波。秦戊听到淮楼说:“睡吧,我等你睡着了再走。”
大抵所有的痛苦和不安,都会随着淮楼的陪伴而渐行渐远。
这一次,秦戊一夜无梦,睡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