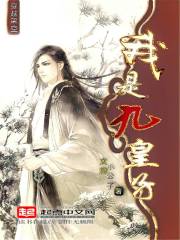神罚,在佛道传说中被指做天劫,由天罚神称为天谴,由神判人称为神罚,天劫分四种。地劫,泰山压顶,粉身碎骨。水劫,毒水泗流,肠穿肚烂。风劫,灭神风起,皮碎肉干。雷劫,五雷轰顶,魂飞魄散。
李通的肚子丶胸口以及喉咙已经完全溃烂,本来就难看面目扭曲的让人匪夷所思,浑身赤裸的被挂在房梁之上,粘稠的血水和黄色的浓水,交杂着一滴一滴顺着垂直的脚尖往下滴落。
平山县的县令发誓,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死状,和传说中的神罚水劫一模一样,哪怕是县衙里见惯死尸的仵作看了,也不禁心里犯恶。
房间的房门是从里面锁着,整个屋子里除了李通的尸体再也没有任何人,昨晚被李通带进房间的两名女子也不翼而飞。
两个看门的护卫被赶来的神教军副史打的没了人样,依然坚定的声称昨晚没有任何人进去李通的房间,李通在屋子里翻云覆雨的声音直到凌晨时分才渐渐消停下来,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奇怪的动静。
唯一的线索,就是在李通尸首的脚下发现了一面纸张。
纸张正面列满了李通所干的一桩桩恶行,他杀了多少人,强奸过多少良女一一详细的罗列出来,纸张的落款只有四个字:以神之名!
而在纸张背后,则用李通的鲜血,勾勒出了一个弯弯的图案,那是一把镰刀,血淋淋的镰刀。
神教军副使轻轻的放下那面渗人的纸张,皱着眉头看了眼依然挂在横梁上的尸首,冷道:“县令大人,你作何解释?”
惊魂未定的平山县令一惊,疑惑的看着副教使道:“上使这…这是何意?”
副教使转过头来,狰狞的看着县令道:“教使大人在你的府邸出了事,你不该解释解释吗?”
县令大惊,道:“上使这是何话?是教使大人自己要在县府过夜,负责守卫的也是你们神教军,与本官何干?”
县令如何不明白这个神教军副史是想推卸责任,他的上官李通无辜暴毙,而且还是一桩诡异的悬案,长生教总坛一定会追究下来,到时候谁也扛不住这个罪责。
副教使看了眼县令,冷笑道:“给你两天时间,找不到真凶你就自己去黔州府跟天师解释吧。”
县令面色阴沉的没有再说话,因为他知道自己即便再如何辩解都是徒劳的,长生教的人从来都不会听别人讲道理,他们说的话就是神谕。
那副教使也不再理会县令,招呼神教军兵士将李通的尸首取了下来,然后带着人匆匆离开了县府。
县令站在原地没有动弹,藏在袖袍中的手紧紧的拽成一个拳头,恐惧和愤怒充斥了他的双眼。
没有出乎县令的意料,即便他调集了整个平山县所有的差役,搜索了一整天,几乎将县衙翻了个底朝天,却依然没有发现分毫线索,连昨晚陪同李通的那两民女子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完全没了踪影。
李通的死好像真的是神所为一般,无声无息。
直到天黑只是,县令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府邸,没有心思吃饭,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经到了极限。
不管李通的死是神所为还是人所为,他知道自己都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凶手,能够毫无痕迹的杀掉李通的人,绝对不是自己县衙那帮混吃等死的衙役们所能对付的了的。可能那个长生教的副史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早就想好了将自己这个平山县令推出去做替死鬼。
长生教对秽教者的惩罚县令比任何人都清楚,长生教的人总会将一些他们称之为秽教者的百姓蛮横的抓去,然后将人折磨了完全没了人样再送到他的县衙让他这个平山县县令处置。
其实县衙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将那些死掉的或者快要死掉的人拉到乱葬岗去埋掉。
县令想到此处,不自觉的打了个寒颤,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和家人也会成为其中一员,成为乱葬岗的一只无主野鬼。
“不行…”不知过了多久,县令猛地从椅子上坐了起来,在屋子里焦急的来回踱步,双手不断紧张的揉搓,口中念念道:“不行,我不能被长生教抓到,绝对不能!”
随即县令来到房门口,将其妻子唤来,急道:“赶快收拾行囊,我们走。”
“啊?”县令夫人一时不知所云的疑惑道:“走?走去哪儿啊?”
县令不耐烦的怒道:“随便去哪儿,先离开平山县再说!”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叫你去你就赶紧去,再磨蹭你我都得死在这!”县令瞪大了眼睛,眼中泛满血丝,看上去极为恐怖。
县令夫人一哆嗦,似乎从没见过丈夫这般模样,不敢再多问,连忙去后院收拾行囊。
夜入三更,县城里平静的出奇。今晚没有月色,天空中乌黑的云朵随着秋风缓缓流动,让人不禁感觉到凉意渗骨。
县令府邸的后门缓缓打开,两个人影从门里走了出来,正是平山县县令和他的夫人。
县令夫人看了眼空空如也的大街,不禁有些害怕,轻声问道:“老爷,马车在哪里?”
县令冷道:“在这里坐马车很容易被人发现,我让车夫王福在前面等我们,穿过两条街就到了。”
说完县令谨慎的左右看了看街道上,确定没有人发现,一挥手道:“走!”
平山县县令和其夫人脚下疾步而行,竭力的压低脚步声,很快便穿街过巷来到了两条街外的一条胡同中。
走进胡同里,果然见到角落中听着一辆马车。县令夫妇二人皆是一喜,快步走了上去。
“王福?”县令来到马车旁,压着声音唤了一声。
没有动静,县令又连续唤了数声,胡同里却异常安静,一个人影也未见到。
“老…老爷,王福人在哪儿啊?”县令夫人有些害怕的问道。
县令心中忽然泛起强烈的不详之感,正想说话,忽见胡同口有一人一步一步的走了进来,夜色下,看上去极为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