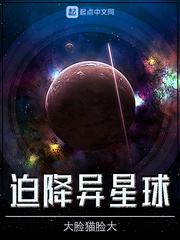“嘿,怎么说话呢!”
尚书府外,面对容艳却是凶恶的女人,凝韵馆的李妈妈没有任何惧态。
胸脯挺起如赳赳的斗鸡,向对方抖抖帕子,横眉冷笑道:
“看来,你就是这时府的管家奶奶吧?”
对方一掌打开眼前的绢帕,神色厌烦:
“拿开,一股子臊味。我告诉你们,我可是堂堂的尚书夫人。那臭表子的院子是本夫人退的,也是本夫人断了她的月钱。
自己是个什么货色心里没数吗,拿个不知哪儿弄来的野种,还想吃上我们时家啦,啊?!”
刁钻女人的话太过刺耳,听得名叫做“惊鸿”的女子羞愤交加,抱着孩子又是一阵痛哭。
几名凝韵楼的姑娘们被激怒了,七嘴八舌道:
“怎么说话呢!”
“惊鸿姐姐生的孩子就是时尚书的。”
“我们都能作证,再怀疑就让贞儿与时尚书做滴血验亲。”
“对,滴血认亲。”
“是啊,滴血!”
“没错,我们都愿作证,滴血认亲!”
围观百姓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们都是身份卑微的普通人,平日里就看不惯官府衙门恃强凌弱。
眼下一方是手无寸铁的妇孺,一方是当朝丞相的亲儿子,这些人自然会向着弱者说话。
时夫人见了,更觉气恼,转身向着门洞里大喊:
“你们这群饭桶还愣着干嘛,还不出来把他们都给我撵走——”
一队窄衣短打扮的护院冲了出来,手持棍棒,蛮横的驱赶人群。
李妈妈绝非是个善茬,低下脑袋就往一个护院的大肚上顶,嘴里哭天抢地:
“哎呦,我这是招谁惹谁喽。我们凝韵馆里栽培个姑娘容易嘛,我这是又请那琴师又请画师呦。
本以为她出息了让个官宦人家看上了,可生了崽子人家又不认,倒头来要把我这不沾亲不带故的老本吃净喽!
我带着人过来说道理,人家就要打死我!给你,你打,你打死我吧,我老婆子从此眼睛干净喽!”
那七八个姑娘也学着李妈妈的样儿,一边和护院们扭打在了一起,一边尖叫大喊:
“打人啦,朝廷大官打人啦!”
百姓之中不少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哪容得下凝韵馆的年轻姑娘们被恶人欺负,何况他们本就仇恨官府。
很快,小伙们纷纷加入了战斗,和时府的护院们撕打起来。
现场顿时变得混乱。
时书安气结,当即就把一腔邪火发泄到了自家夫人身上,手指女人,八字胡须桀桀而颤:
“你、你这个无知的妇人,都是你惹出来的好事!”
那女人本是内阁次辅张大人的嫡孙女,从前做姑娘时就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受得了气?
她尖叫一声扯住时书安的衣袖,追着他不停打,咬牙切齿道:
“好啊,你还敢怨老娘。你在外面风流快活够了,叫老娘给你擦屁股,如今还敢骂老娘……”
官道对面的茶楼三层,蛊笛坐在视野开阔的雅间里,嘲讽的目光隔着窗纱注视着时府门前的闹剧。
摆摆头轻笑一声,他自语道: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云汐不愧是只小狐狸,比九弟还要狡猾得多。”
……
日晷偏移,已过巳时。
热辣辣的太阳照射了皇宫承太殿前的广场,无遮无拦的刺眼。
因礼部尚书时书安迟迟未到午门,就快误了迎劳的吉时,帝君华南信大发雷霆。
之后派往尚书府打探的人如实回禀说,时大人是因惹上了青楼的官司,如今府外的街面上已然乱做了一团,怕是不能按时赶来与典礼仪仗回合了。
帝君当场暴跳如雷,狠罚了探子。
龙威震慑之下,百官无不惊骇,每寸下跪的身形皆是颤栗不止。
华南赫身着赭红衮龙袍,驱动眸光偷看丞相时凌和丹墀上的慧贵妃。
见他父女二人皆是面白失血,吓得几乎背过气去,男子垂低的俊脸悄然掬起一抹坏笑。
也难怪他这位皇侄儿会在今时疯狂至此。
先前东厂的暗杀行动、还有那非是空穴来风的毁尸邪药“化腐散”,都把华南信和他的王朝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百姓眼中,这位仁宪皇帝头顶的光环已是暗淡无光,成为了暴虐无常、喜杀无辜的魔鬼。
而今瀛使入京迎劳这等的大事再度节外生枝,礼部尚书与青楼女子苟且生子一事,很快就会闹到满城风雨。
那时,百姓嘲笑天家的事可大可小,而误了迎劳的吉时,影响大羿与瀛国的邦交事关重大。
华南赫与蛊笛兄弟两个心里最是清楚,此番将东厂暗杀事件流向市井,又一力安排凝韵馆的姑娘们大闹尚书府拖延时间的背后推手,正是顾云汐。
她这样安排的目的再明显不过,即由外及里,除陈推新,将内阁逐步换为一己的清流。
大羿朝野,内阁为中枢心脏,东厂是皮肤。
这两样一旦换新,自然可以撼动华南信,控制住整个皇室。
时间点滴流逝。
华南赫似笑非笑,向上拱手道:
“皇上,请恕臣直言。当务之急还需派典礼仪仗立刻赶赴璐苑,迎接使臣以做弥补。”
瀛国乃一小小岛国,虽由世袭的王上统治,然其不过是个傀儡皇帝,实权由三大将军把持。
也因王上的懦弱,养惯出三大将军的专横跋扈,目中无人。
这次以使臣身份入大羿的人,正是瀛国三大辅政将军之一的源仓大将。
传说此人性格火爆,是个很不好惹的角色。
想来人家千里迢迢跨洋越海而来,大羿官员却没能按时前往迎接,将人晾在太阳地里暴晒。
时候久了,那源仓大将必是不会高兴的。
华南赫的提示让华南信冷静了几分,沉吟道:
“眼下时辰误了,谁去都少不了被那源仓大将借题发挥,一番刁难责难了。”
丞相时凌巍巍匐拜在地,颤声道:
“回皇上,若皇上还不弃臣,老臣愿往。”
“你给朕住口,朕看见你就心烦。你身为内阁首辅治家不严,真是难当大任!去,把你那儿子领回家去,礼部尚书他不做也罢!”
华南信朗朗铿声,恹恹的挥手。
时凌叩头不断,泣道:
“养不教,父之过,是老臣之罪,老臣甘愿受罚。”
眼见时相危了,月西楼看看左右群臣,思量须臾,启奏:
“皇上息怒。那瀛国不过一小国,此此入京看似朝拜,实则为与我泱泱大国一较高下。
纵然天朝迎劳有误,也算给了他们下马威。如此,若要内阁首辅亲自去迎倒显礼重了。”
华南赫见缝插针,挑眉:
“听月督公的话意,可是要为皇上保荐人选了?”
又见月西楼神情忿忿的看过来,华南赫装作痴癫,捧腹大笑:
“哈哈,本王又忘了规矩。好,本王闭嘴。”
华南信冷眼瞥了他一眼,叹气。
这位九叔从疯了之后就无所顾忌,现在形势严峻自己也无暇和他计较。
“月西楼,你可有合适人选?”
皇上发问,月西楼不便耽搁,袅袅眼神扫过文官队列:
“微臣以为,礼部侍郎汪灿能当此任。”
汪侍郎多才,行事端稳。
最靠谱的是,此人素来与时党泾渭分明,这正是他月西楼想要争取到的力量。
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华南信眸中一亮,欣然笑道:
“你不说朕险些忘了,行止通晓六国语言,自然能担此任。汪行止,从即刻起你就是礼部尚书,快快带领典礼仪仗出宫去迎使臣吧。”
那汪灿年近不惑,官袍加身姿态清雅不俗,颇具儒风。
像是凭空掉下来的金元宝被他捡到,汪灿脸上无波无澜,恍是见惯了大阵势一般宠辱不惊。
端步走出文官队列,他撩袍跪倒,嗓音提高一度:
“臣叩谢圣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了好了,快去办差吧。”
华南信确似内心长草,急切的将人派出去了。
皇帝身侧,贵妃时沅卿眉眼愠怒不甘。视着月西楼的瞳中,涌现着恨意森森。
云汐在宫妃队列里亭亭玉立,嘴角衔起一丝微澜。
隐隐侧动目光,便与玉阶之下的华南赫双眸对在一处。
他含笑对她挤眉,眼底绯波跌宕。
她却未曾释怀先前的争执,只冷冷白他一眼,一副傲娇的小表情惹人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