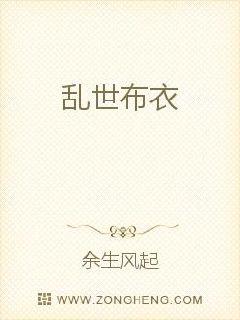秦岭东部的实际控制者、秦岭中部的实际掌控者、七万余秦岭山民和秦岭土民的东主大人……财力、人力与武力兼备的大周民间豪强李毅夫,度过了一个非常快活的六月下旬。
继续进行改革以配合李毅夫大计的公中职员忙得七窍生烟,好在有新定的休沐制度和涨薪资制度支撑着他们,否则还不知有多少人要请长假。
南山堡、明月集和丹江口的公中职员很忙,留在江南的方维良、成吏员等人更忙,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
江南工商势力无法将外来的商人排挤出去,便使用了最擅长的一招:拉拢分化。
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江南工商势力尽管恨得咬牙切齿,也只能允许外来商户在江南秩序的重建中分一杯羹。京西南路的外来户中,明月集大商户、丹江口船队、襄阳商人都被江南工商势力拉拢过去,南山堡的商人就此被孤立。
“真的挡不住了?”张清平、张永年和丁史航难得坐在一起,他们一起问主管商事的成吏员。
成吏员点点头。虽然成家大郎已经接近康复,但他仍觉得意犹未尽,还想从江南捞更多钱。
然而江南形势的变化是不可逆的,只听成吏员直截了当道:
“东主大人和老寨主带着秦岭子弟回返了。咱们没了话语权,京西南路那些靠山强大的商人又被拉拢走……没办法,是时候按照东主大人议定的方案,劝南山堡的人家回返了。”
“至于那些贪心不足,抱着侥幸念头,想打太湖沿岸茶园、水田、漆园、坊院、宅子的人家,咱们只能再提醒他们一次。万一陪惨了,或者被排挤得血本无归,只能自认倒霉!”
张清平和丁史航呼口气。他们知道公中最看重规矩,绝不会赔偿不听从公中劝诫的人家哪怕一文钱,于是决定多提醒几次相熟的人家让他们乖乖撤走。
张永年皱眉,拱手问道:“咱们南山堡的人家,总不至于将卖不出去的东西带回去,这些东西怎么处理?永乐伪朝那边要求更多粗盐、烈酒、石灰和药品,说什么医治妇孺的鬼话,又该如何答复?”
成吏员当然清楚,船舱两侧坐着的这几位其实也担负着代替东主考察、监督自己的重任,毕竟他还不是正经的公中高层。他也不需要隐瞒什么,将计划和盘托出道:
“很简单,咱们来个一石二鸟。”
“方腊那边不是同意转交一批大匠、名医和珍本书籍,只是要价奇高吗?就让南山堡的人家和明月集的中小商户把他们滞销的货换成永乐伪朝需要的,转给咱们。”
“咱们明面上载着粗盐、布匹、烈酒等硬通货北返,暗地里用这些东西和永乐伪朝谈判。至于谈成什么价钱,就看方维良的了。”
六月底七月初,李毅夫白日巡查作坊、水渠、土堡、新屋宅群和披甲内丁,晚上和刘素素或刘小慈开发新姿势。东主大人享尽温柔之余,也不忘亲自下厨开发新菜式,让秦岭山民遗属和孤身女子在饮食相关的行业上更有优势。
与此同时,几千里之外的方维良奉行李毅夫的意志,在与永乐伪朝沈寿等人的谈判中适当让步,永乐伪朝也让了一步。双方随即展开规模小但价值极高的走私,李毅夫要的是人才和知识,方腊要的是赖以吊命的物资……
视线转到屏障秦岭东部,同时也是进攻秦岭中部的桥头堡:拐子山口。
拐子山口已经建立起一座半永久性营寨。李毅夫的两位门生,秦钟和杨建川,正在查收踏张弩小队的训练成果。
李毅夫和刘成栋率兵回返后,正式更名为乡兵、弓手和土军的秦岭山勇终于装备了第一批一百七十把踏张弩,拉力超过了五十公斤。此举标志着踏张弩在本年的最大突破。
相比对指挥水平要求非常高的直弓小队,踏张弩小队的战法无疑简单太多。靠近了,射他娘的!
只见十个刀盾手、十个短矛手喊着号子靠近山脚。随着一声尖锐的哨子响,前面的二十人低头。
在掩护下靠近稻草人的十个踏张弩手立定,放上弩矢。然后将竖着的踏张弩放平,扣动扳机……
尖啸声响过。除两人脱靶外,其余八支铁弩矢成功将稻草人后面的木板击裂!
面容冷酷英俊的秦钟拿起锥形倒钩弩矢,仔细端量了一阵,说了两点不足,“这玩意儿不能重复用,变形得厉害。”
“而且只有一种弩矢,杀伤和破甲都偏弱,白瞎了金贵的踏张弩。”
杨建川从小沉稳平和,被山里的长辈打趣为“小老头”。只有在亲密玩伴的面前,他才会露出天真好动的一面。
杨建川摸着厚实的弩身,感受着踏张弩的结实用料,点头道:
“不错,是该向南山堡回信说一下,让他们加快做出几种弩矢。”
“想彻底控制秦岭中部,让公中派人到这里管制山民和土民,就要先压下蠢蠢欲动的几支人马。”
“能够隔断绳索和树枝的月牙铲弩矢一定要有。秦岭里的对手几乎没有甲,能重复使用的便宜弩矢必不可少,只要能杀伤没披甲的人就行。在秦岭里和善于钻山沟的打仗,还是踏张弩好用!”
直弓战法受到的限制太多。面对时分时合、穿梭游击的抵抗力量,缺乏弓箭手的秦岭山勇只能依靠踏张弩,才能压下对方的低劣弓箭。
秦钟无奈地观察了一会儿青铜弩机。他知道四眼仔和雷达等人已经很辛苦,一时半会儿搞不出钢质弩机也说明不了什么。
但只要钢制弩机不能大量生产,需要消耗大量铜的踏张弩便不能大规模装备。
分工明确、战术灵活的踏张弩小队解散。杨建川突然谈起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杨营东,只见他摇头吐槽道:
“我爹可真是……从小便教导我要懂事,要稳重。谁知他自己却开始跳脱了,还在江南冲撞过东主。”
秦钟自然听说了杨营东的事情。他却不以为意,搂着杨建川的肩膀道:“东主没有怪罪,就是最大的幸事,以后提醒叔父注意便可。”
“杨叔叔也不容易,自婶母大人走后……他将你拉扯大,终于娶上了续弦,性情跳脱也属正常。”
“那个杀人很凶残的大嗓门儿,应该如何处置。”
无法从噩梦中走出来的大嗓门儿在秦岭做下几桩杀孽,直到秦钟、杨建川接过拐子山口的防务之后才被拘押起来。
大嗓门儿和三伢子、大牛等人相交莫逆,跟这三家相交莫逆的人家就更多了。四眼仔那家伙更是娶的大嗓门儿亲妹子……好些人明里暗里为大嗓门儿求情,秦钟等人只能把难题抛给李毅夫这位东主。
李毅夫既要给新归化的山民一个交代,又不能让太多老山民寒了心,于是将难题抛给判堂。
李梦空等人傻眼之下,翻烂了薄薄的公中条令,发现大嗓门儿的事情属于擦边球。于是判堂传出消息,让想保下大嗓门儿一条命的人家或是“将功补过”,或是掏一千贯钱赔偿私了。
秦钟和杨建川又闲聊了一会儿,内容主要是东主大人结婚后,南山堡附近人家抢着结婚,以至于闹出不少笑料和误会的趣事。然后便迎接到了新任的军需执事和军法执事。
军需和军法官很早就有,几乎是李毅夫刚掌控实权便出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活动范围小和条令不健全,导致军需官和军法官无所事事,或者成为一般无二的指挥人员。
形势不同了,如今条件已初步具备。李毅夫想加强对秦岭武装的掌控,还要安抚秦岭山民和秦岭土民,都需要军需执事和军法执事掌控实权。
时间进入七月上旬。
就在李毅夫坐在一匹强健的大理马上,摇摇晃晃地向拐子山口进发的时候。几千里外的钱塘江南岸战场上,取得突破的刘光世和王师心正快速向北进军,固守钱塘江南岸营地、牵制永乐朝兵力的虞允文和张天垒正在经受最后的煎熬。
“哪来的一堆歪瓜裂枣、泼皮撮鸟,还不将手中的刀兵放下?!”
脸上有刀疤和烧伤的一位西军副都头露出半拉胸膛,恶狠狠地瞪着陈迦星一伙人。
这里是位于松江城附近的一个大周军伤兵营地。此时正洒着不疾不徐的羊毛雨,妇人和少女的哭叫求饶声和大周军士兵的淫笑声混杂在一起。
陈迦星的手下虽然长得奇形怪状,简单点说就是丑,但没有一个怂的,纷纷掏出奇形怪状的武器与几十名官军士兵对峙。其中有一个头大独眼的家伙,恨不能将剩下的眼珠子撑爆。
“行了,廖家兄弟,让那个陈迦星进来吧。”
不远处是一栋倒塌了一半的乡间小地主宅院,从那里传来一个中年汉子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却给人一种稳重之感。
副都头无趣地摇摇头,将双手刀放下,抬抬下巴说道:“只能进去五个,不能带刀子!”
陈迦星换上标志性的谄媚贱脸,朝副都头微微抱拳,带着歪嘴、一对脑子不好使的双胞胎兄弟和身着脏乱布袍的账房先生走向那栋小宅子……
“我说老哥哥,咱真就这么放他们走?”副都头的可怖脸在夕阳晚照中更显狰狞。他一边拿干布擦拭自己的刀,一边问门口的都头。
都头姓蔡,和副都头来自一个军,二人在西军中摸爬滚打已经十多年。左侧肋骨折断的他摸了摸腰间油布包里的交子,点点头说道:
“不要总想着是个商人,就得额外给咱们孝敬。咱们几个天南地北闯过许多年,难道你还没看出来,咱们绞尽脑汁地敲诈勒索,也没有某些人按规矩办事拿的多?”
“一些永乐逆民的女子而已,卖给这伙人还能再抓,做长期生意最要紧。面子啥的扔一边去,带更多交子回去才是正经营生,咱西北那破地……”
“而且你没听说长江上,凡是受秦岭东南那位李天王庇护的商人,一个个都很硬气?”
陈迦星为了让妻儿在南山堡过得好点,冒着危险奔走于战场后方的各处大周军营地,有时还突进到双方的拉锯地带。
陈迦星当然不了解李毅夫的计划,只知道多给南山堡送去一些生育之年的妇人,他的功劳便越大。于是他全面发挥自己的“专业素养”,专门低价买下被大周军摧残过的“从贼逆民”女子。
沦为军妓的江南女子不只是便宜,更难得的是不需要安抚。她们巴不得离地狱越远越好。
“大哥,大哥。刚才有个小娘子给俺道,道谢呵。”
歪嘴露着半口东倒西歪的烂牙,兴奋地跑到陈迦星身边说道。
陈迦星两侧的弟兄放荡地笑了笑。这些大周百姓眼中十恶不赦的恶贼或是拍歪嘴的脑袋,或是推歪嘴的后背,挑唆歪嘴去把那个残花败柳办了。
“咱们是人贩子,买下她们就是为了卖到另一个地方,居然道谢?真是稀奇。”陈迦星开始怀疑人生。
“是啊,大,大哥。俺感觉自己干了,干了件好事。觉得怪,怪怪的……”
哄笑声响起,陈迦星却心烦地皱起了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