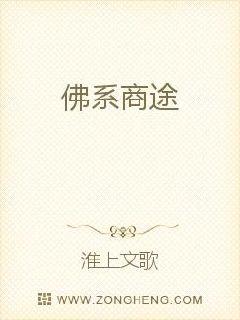到达长安时已是农历的五月,今春上元节后离开西都时,渭水两岸还是银装素裹,今日归来已是满城的葱茏。
物已非,人还在否?
乘着商队在城外的客栈短暂驻扎前去易寨更换马匹的间隙,我和秦冲、锅盔刘、沙米汉四人打马去了一趟西市的洛城邮驿。
上官老夫人盛情接待了我们,遗憾的是燕喜小姐已经离开了长安。
听老夫人讲西域楼兰今春干旱肆虐,黄沙埋城,燕喜小姐临时被派去西域,处理洛城邮驿楼兰分号的搬迁事宜。
是搬至鄯善国都扜泥城,还是往西前往龟兹、乌孙诸国,暂时还未定论,等到达西域后再作决定。
满心失落的离开洛城邮驿时,上官老夫人才忽然想起她女儿上官燕喜临行前还给我留下了一封信笺,内容如下:
“金城易兄,上元一别有时日也。燕喜日夜难寐,盼君归来,共赴山盟。怎奈家事维艰楼兰日危,燕喜挥泪前往,有负当日之约,吾兄勿怪!
金秋北雁南归之时,玉门关外,燕喜翘首恭候。山长水阔,锦书难托,寥寥数语,难诉衷情!”
白绢为纸的信笺还留有暗暗的幽香,细细读了两遍之后,我不禁思念成灾,泪如雨下。
燕喜小姐,我辜负了你的衷情,玉门关东去的敦煌沙洲,已有一位刘南儿的女子在那儿等着我了,我该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少主!你怎么哭啦!哈哈!想上官姑娘了吧!”看见我在马上默默的垂泪,沙米汉惊诧的笑道。
“少主想得姑娘何止一个上官小姐!肯定还有那个刘南儿,哈哈!那才真真的绝色佳人!”
在陇西庄园时,秦冲这小子应该早就瞅见了我和刘南儿之间的那种不可言传的暧昧。
这个时候尽然提起刘南儿,正好踢到了我的痛处,真是多情空余恨也!
前方的大街上有一队官家的车马正奔驰而来,我们赶紧打马躲到了街边,给这些不可一世的羌秦禁军腾挪地方。
“还是少主好啊!每到一处都会有佳人相约美人相伴,下辈子我一定也要投胎到富豪人家,做个人见人爱的少主人!”
沙米汉羡慕的叹道,拍着自己肥硕的肚皮,埋怨着苍天的不公。
“老汉,不要酸我啦!你不是想让我做媒吗?好啊!如果那个刘南儿能够看上你,我就做一回月下老儿怎么样?”
我正愁着怎么解决刘南儿这件事呢,沙米汉的叹息正中我的下怀。
这个家伙也算是西域柔然国的世家子弟,因为先祖经商失败家道中落才卖身于我家。
高大威猛、力拔千钧,一位很不错的少年郎。
可刘南儿不辞万里原是一心奔我而来,将来我却让她下嫁一位伙计,真是乱点鸳鸯谱啊!
“少主此话当真?”
听罢我言,沙米汉翻身下马,喜出望外的跪于我的脚下。
“这个这个,缘分天注定!老汉,你就等着吧!”我突然有点后悔刚才的做媒一说。
“少主,你就不要框我们老汉啦!刘南儿远在江南国色天香,你以为老汉是匈奴国的王子啊!再来一次昭君出塞?”
秦冲打马上前,递上剑鞘把沙米汉拉了起来。
“少主,桂之坊的兰姑娘托我从江南买了一块做夏衫的绢布,呵呵,我想现在顺路送过去!”一直没有搭话的刘真儿突然讪讪的笑道。
“走!我们陪你一道过去!喝酒寻欢的花销,本少主全包啦!”
少年人的情愁爱恨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刚才还在撕心裂肺的想念上官燕喜姑娘,为刘南儿的事情愁肠百节。
如今一听到刘真儿去桂之坊的提议,所有的思念和哀愁一扫而光,满脑子全是那些胡姬姐姐们柔弱如酥的香体、喘息呢喃的莺音。
我们四人再无任何的分歧和杂念,紧紧跟在刘真儿的马后,向桂之坊的方向狂奔而去。
长安之后渡过黄水大河,再过姑臧城、狼女神山,来到天之山下的祁山马场,已是这一年的夏历六月了。
再往西去就是千里荒凉的戈壁大漠,马车已不适合行走。
因此,在此地换装以骆驼替换马车西行,是我家商队每次回途经过天之山时的必做之事。
宽大的马车无法穿过山间的栈道抵达祁山马场,因此只能由木塔尼尔,芒东拉、奴葛他们把我们来时留在马场休养的两百来头骆驼、马匹赶下山来,在这河西的官道边上就地替换。
一时之间,沉寂的河西商道上人马喧嚣,驼峰成林。
伙计们忙碌着把马车上的皮囊一袋袋的搬到驼背之上,用结实的皮绳绑紧套好。
一马车的绸货刚好够十五匹骆驼装运,所以等所有骆驼的驼背都堆积如山的时候,马车上装货的皮囊也全部搬完了。
正如爷爷他们当初猜测的那样,木塔尼尔、芒东拉他们三位老伙计虽然一心想回归商队,但真正等到苏爷询问他们作何安排时,三位老伙计都含泪选择继续留在祁山马场。
妻子儿女在哪儿,家就在哪儿,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而秦冲、沙米汉、锅盔刘他们则虚惊了一场,从建康出发的时候,秦冲还在怂恿我向爷爷请求走海路回于阗。
三人最怕被苏爷选中,让他们替换木塔尼尔、芒东拉、奴葛做祁山马场的主事。
因为他们最年轻,有没有家小的拖累,如果真要替换的话,他们三人却是最佳人选。
不过于我而言,这三个家伙一路走来已经和我结成了兄弟般的友情,离开了他们我还真是舍不得。
离开岐山马场后,我们又在荒原上走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虽然还是来时的老路,但沿途的景致似乎已与来时有很大的不同。
只有一些爷爷反复介绍的路标,如一个荒芜的村落、长堑的烽燧、独特的山峰、南北走向的小溪等等,还有依稀的印象。
在天之山向西的余脉地带,向北穿越一处平坦荒凉的土塬,远处开始出现黄沙漫漫的大漠景象。
仲夏中午的骄阳似火,大漠深处隐隐可见一处金光灿烂的崖谷,终于又回到沙洲的莫高窟了。
刘南儿一行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到达了沙洲。
与她随行的除了我在陇西庄园见过的那位丫鬟和车夫家老外,还有五位沿途护送的刘府家将。
白轩画工告诉我们,半月之前外公和武威二人刚刚经过莫高窟,现在应该已到玉门关外的龟兹境内了。
望着远远向我们奔跑而来、彩衣飘摇的刘南儿和仙风神怡的白轩画工,我恍惚之中感到他俩分明就是石窟壁画之中遁出凡间的飞天仙女、青莲王子。
真乃天造地设的一对神仙伴侣也!
“公子!亲家爷爷!”一声吴侬软语的欢呼,刘南儿已是泪如飞花一般的沾湿了衣襟。
“七姑娘,你怎么在这儿啊?”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没有见过爷爷如此的惊讶。
看着刘南儿脉脉含情的眼神,爷爷似乎明白了其中的一切,他回过头来,手中赶马的皮鞭已经重重落到了我的身上。
“孽子!气死我也!”爷爷须发倒竖,双目喷火的怒骂道。
如果不是苏叔、秦冲他们在场的及时阻拦,他老人家非宰了我不可。
爷爷可能以为我是贪恋刘南儿的美色,瞒着刘老太公擅自做主把这个苦命的守寡女子骗到了这苦寒的北地。
原来陇西故人如今的儿女亲家,我若真是做了如此叛经背道之事,那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爷爷向来宠爱我这个长孙,一路走来我和秦冲他们做下的那些荒唐之事,他应该都了如指掌,但从未横加干涉,还有纵容之嫌。
也许在爷爷看来,青春少年沾花惹草不是罪过,这本来就是弱冠之年的娃娃们应该干的事情。
但唯独这一件,似乎关系重大,爷爷又急又气,坐在路边的大石上一时尽说不出话来,唯有皮鞭指我,似乎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吓得扑腾一声跪在他的脚下,有口难辩只能但凭爷爷的发落。
“亲家爷爷!公子无辜!一切都是奴家的过错,你要责罚就责罚我吧!”
刘南儿见爷爷如此气愤,吓得赶紧在我身边跪下,苦苦哀求道。
“七姑娘啊,你也是长在豪门士族,又出嫁过一回,我家金城不懂世事你难道也不懂?我和你爹爹少年故友,如今又是儿女亲家!你俩不经过两家父母族人的同意,没有媒妁之言,就私自离家出走!如让世人知道,你爹爹的颜面何存?你们江南刘府门阀士族的颜面何存?我们易氏一门在江南建康的家风声誉何存?你又如何让我武威、长安位孙儿在这江南立足下去!”
爷爷扼腕叹息道,让我也惊出了一声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