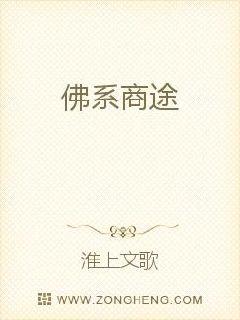西行的归途,旧风景、旧世事,闲话少叙。
商队朝行夜宿,马不停蹄的向西过淝水,经寿春,然后北上直奔淮水而去。
在距离淮水碧云渡约有五十多里地一处土城客栈,日暮天黑,商队就此住宿了下来。
“主人家,老叟向你打听个事情!”
店中没有几个留宿客人,有点冷清。
在店内粗糙的橡木案几边盘腿坐定之后,爷爷招手叫来了客栈店主。
一下子呼啦啦来了这么多的客人,店家伙计虽然一时之间手忙脚乱,但个个脸上都乐开了花。
听到爷爷的招呼之后,中年矮小的店主忙不迭的跑上前来,一边用衣袖擦着满手的油腻。
“客官老爷有啥吩咐?任凭差遣!”
“我们初春过来时,淮山碧云渡那一带匪患猖獗,不知如今可有缓解?店主小哥可否告知一二,老叟好预作准备往西另寻其他的渡口!”
爷爷向店家拱手笑问道。
“老爷要问这事说来可就话长啦!”店主听完爷爷的问询尽然在对面坐了下来,神秘的低声。
“有何变故,老叟洗耳恭听!”爷爷呵呵笑道,挥手让我给店家斟酒。
这建康带来的清酒是我们陇西庄园的自家酿造,商队临行前家老车叔特地为爷爷准备了十几坛以备途中饮用。
“好酒啊!呵呵,客官老爷爽气!”店家品了一口清酒后接着道。
“听南下住店的客官们讲,两个月前盘踞淮山上的那股悍匪一夜之间尽然凭空消失了!客官你说奇不奇怪!”
店家又端起酒碗咕咚咕咚的喝了两口,看来我们带来的清酒比他家的浊酒要爽口很多。
“确实奇怪!难道被官府剿灭了?或者是迁往他处?那么多人马,总不会一点踪迹都没留下吧!”爷爷故作不解道。
“没有任何踪迹,就这么凭空没了!碧云渡口的那十几只渡船全都还在,淮山顶上的老君殿、山腰上这伙盗贼的营房,也全部完好无损,可就是人全没了!”店家道。
“后来呢?那一带从此就安稳下来了?”旁边的苏叔追问道,我则抱起酒坛把店家的酒碗续满清酒。
“客官听我慢慢叙说,呵呵!更古怪事情还在后面。一个月前从北方来了一批逃荒的汉家流民,足足有两千多人!为首的是位付姓的员外,所有流民都是他的族人!这要搁以前也并不是啥大事,我们这一带居民三辈朝上的先祖都是来自北地!可如此举族南下的景象已有些年份没看到了。”说到这里店家的声音低了下来,像怕人听到一般。
“听说北方的后秦与拓跋鲜卑的魏国如今在边界地带剑拔弩张,大战眼看在所难免,这些难民或许是从那些地方逃过来的。”爷爷举酒敬店家道。
“客官老爷说的在理,可世人都说这些流民就是原来淮山上的那伙贼人!”店家伸长脖子在爷爷耳边低语道。
“那伙贼人如此乔装变换又是何苦!呵呵!”苏叔不以为然。
“如此猜测有何凭据?”
“听见过的客官讲,这伙人看上去没有一丝的饥馑之态,从碧云渡渡河之后就直接奔了淮山!”店家唏嘘道。
“后来如何?是否还如以前的匪盗一样占山为王,危害四方?”
爷爷笑问道,我也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变故。
心中暗笑这个符乾王爷真是头脑简单之人,就算冒充流民至少也要装扮的像一点啊!
“那倒不是,这些流民自称来自北地安邑,如今已在那位付员外的带领下归附了本地南梁郡,低价从官府那儿收购了淮水两岸数以万顷的无主之地,招募四方流民前来依附!淮山上的贼窝如今变成了安邑付寨。听说朝廷已下文书,要以安邑付寨为依托,在碧云渡一带侨置安邑县治!哎!不出数年,那个付员外定能成为淮水一带数一数二的门阀士族!客官你说这世事有多稀奇,呵呵!”
店家终于讲完了近三个月来淮山碧云渡世事变迁的怪事,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眼前的我们这些外邦客官,却是这场巨变的始作俑者。
“哎!天下纷争,身世如浮萍也!为贼为民往往都是身不由己,管他原来是贼寇还是流民,只要能够改恶从良,就是善莫大焉!”爷爷叹道。
这时,店家伙计已经端来了粟米烂肉,店主赶忙起身。
“饭菜已备好,各位客官老爷慢用!呵呵!慢用!”店主与爷爷拱手想让,忙活自家的事情去了。
第二日下午,我们的商队终于来到了淮水岸边。
两岸原本荒芜的阡陌原野上,无数个农人正在辛勤的耕耘着。
清明前后种下的黍稷豆麻之类的作物已经有一指来长,整个田野绿油油的一片。
“没想到千金的馈赠能够渡千人向善,救万家于水火,善哉!善哉!老苏啊,这一单买卖我们做得好啊!”
爷爷骑在马上双手合十对着大河虔诚的膜拜道。
“老爷商者仁心,渡人渡己,必将福源流长,泽被后世!”一旁的苏叔由衷的夸赞道。
“不走碧云渡了,东南二十里有一野渡,我们从那过河!”爷爷调转马头拂须笑道,一边打马去前方带路去了。
“爷爷,碧云渡近在眼前,我们为何还要舍近求远?”我快马追上不解的问道。
刚刚一气奔驰了五十多里,人马都已疲乏,爷爷的决定让我很是不解。
“改过自新之士,最怕遇见故人,我们就好事做到底不要再去叨扰人家啦!”爷爷哈哈笑道。
“尉爷和武威少主肯定是从这儿过河的!”一旁的刘真儿插嘴道。
“如此一来,我们就更不能从此渡过河了!”
爷爷扬鞭答道,头也不回的领着商队重新转回官道,朝东南方向的阡陌深处奔驰而去。
其实爷爷他们的意思我也明白,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君子处世之道也。
过淮水之后,商队沿着来时道路马不停蹄,人不落枕、昼夜兼程。
终于在中原雨季到来的前半个月,顺利抵达了洛阳,转向了西去长安的砖石驰道。
秦冲告诉我,有一年因为不知道这淮水之地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还有个梅雨季。
所以商队过了淮水之后,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走走歇歇,丝毫不知危险正在慢慢的逼近。
结果连续几天几夜的扯连大雨下来,淮水暴涨,奔腾的河水漫过了河堤,北岸的千里沃野尽成泽国。
原来的黄泥马道污水横流、软如丝绵,河水漫过车辕,整个商队的车马全部陷在了路中进退无门。
爷爷不得不忍痛舍弃了车上的货物,带领众人牵扯着马匹转移到附近的松山上。
就这样在凄风苦雨中停滞苦熬了约半个月之久,河水才慢慢退去,几天的暴日炙烤之后,商队才勉强从黄泥苦海之中磕磕绊绊的走了出来。
到了洛阳清点货物才发现,羊皮口袋在水中浸泡久了,遇到突然暴热的天气迅速的霉变腐烂。
而袋中所装的丝绸布匹更是损失惨重,几乎十不存二。
爷爷的商队来往西域、中土这么多趟,那年可能是唯一一次的巨亏。
幸亏人和马匹没有损失,归途的盘缠也没被大水冲走,整个商队才能安然的回到西域。
关于那一次惨败的经历,爷爷从来没有对我们这些家人提起过,也许他老人家也有点难以启齿吧。
面对的敌人不是官家匪盗,尽然是一场无法预测的连绵阴雨。
如此看来为商之道,除了地利、人和之外,天时也是太重要了。
西域大漠的春冬二季不走黄龙沙海,我已经见识过黄龙发怒大石飞天的威力。
而秦冲所描绘的这夏日淮水两岸的泥汤地、黄梅天,淫雨霏霏、湿热难耐、进退不得的难堪情景,我虽然没有亲历。
但这样的鬼天气带给行商之人的苦楚,我还是能感同身受。
在龙门山下的伊阙客栈休整了两日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平心静气的赶着马车,向西都长安的方向逶迤前行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