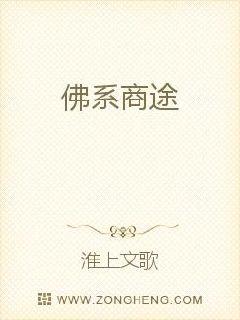佛家度人,是为了让世人破迷开悟、断恶修善,改过自新、离苦得乐。
而对于这些混沌蒙昧的土著野民们来说,开悟的首要之责应是移风易俗,彰显文明。
我们途径的耶婆提国和蒲罗中群岛,那些来自天竺佛国的传教者们,设坛传道广收门徒,教授土人农桑之事,改变他们千年的恶俗。
在我看来虽然收效甚微,但其中的目的尽在于此也。
但无论何种文明,吃饱肚子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管子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便是这个道理。
商船不久就要西归,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这些登岛的土著们朝夕相处。
所以我们就选一些最紧要的生存之法,每日手把手的教授他们。
如何钻木取火、如何保留火种、如何蒸煮木薯、如何烧烤糜肉、如何晒制海盐等等。
饮食之风的改变相对容易,撒上海盐、经过木火烧烤的肉食,其中的味道远胜于血腥的生肉,只需一尝便知。
一两天的功夫,这些土著便已迷上了这些美食。
他们每日的活动,不是去海中捉鱼,就是去海滩的崖畔猎杀海兽。
海滩上的烤肉大餐,每天都要延续到深夜才会结束。
一时之间,岛上焦香弥漫,充满了人间的烟火味道。
土著们的人生追求如此简单,似乎只要有烤肉可吃,便是在天堂中过日子了。
除了引火烤制熟食之外,他们尽然无师自通,有了羞耻之心。
一天午后,土著们的盛宴又开始了。
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些男女野民全都穿起了衣衫。
晒干或烤干的海兽皮缝制而成,围在了原本赤裸的腰间。
很像赫拉特城邦的酒肆中,埃及舞姬们的流苏短裙。
三十多个穿上兽皮裙衣的土著男女,正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癫狂起舞,哼唱着他们原先吟唱的那些神曲。
“大哥!这帮野民孺子可教也!哈哈哈!”
站在船头见此情景,我很是欣慰的长声笑道。
“是啊!要是在我大晋汉国,不出一年他们都能归化成为新朝国人!可惜我们就要走啦!”
林兄醉醺醺的叹道,又仰头喝下了两口薯酒。
自从船上有了足够的存酒,这位老兄的酒瘾终于得解。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明日我将酿造薯酒的技法也传给他们,但愿这些土著们将来能在岛上生生不息,千秋万代!哈哈哈!”
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便是教人向善。
眼见这些野民经过我们的几日调教之后,不再茹毛饮血有了开化之心,令人倍感欣慰。
“林青!春哥!你俩送几桶薯酒过去!让这些野民们也尝尝,我大汉的清酒是啥滋味!”
但凡喜酒之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便是劝人饮酒绝不吝啬,林兄也是一样。
听我所言准备向土著们传授酿酒之法,他挥手招来了两位小弟,以美酒相赠野人。
林青春哥二人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主家有令不敢不从。
便每人抱着一个棕木酒桶下了商船,向那野人堆里匆匆而去。
到了篝火盛宴
的现场之后,两位少年也许担心野民们糟蹋了酒水,尽然亲自打开酒桶舀出薯酒,转手递给了这伙土著的头领,那位年老的巫师。
巫师双手捧着酒瓢一饮而尽,木薯烈酒的辛辣之味顿时令他荡气回肠。
这位干瘪的野人老头,尽然手舞足蹈的狂吼了起来,不是苦痛之色,而是如醉如痴。
所有的土人无论男女,每人一舀烈酒下肚,半盏茶的功夫两桶送去的薯酒竟被这些野民喝得一滴不剩了。
看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很合他们的胃口。
完成任务的林青他们满脸坏笑着归来:“兄弟们有好戏看啦!这帮不知死活的猴子!如此烈酒也敢像喝水一般!嘿嘿!”
这两坏小子,原来是不怀好意,诚心要把这些土著们灌醉啊!
果不其然,薯酒的酒性很快发作,野民们个个痴醉成魔,围着篝火狂歌乱舞了起来。
晚霞染红了整个岛屿,随性而发没有任何编排的野民歌舞,节奏明快热烈,具有别样的美感,令人怦然而心动。
“老爷!这帮野人都是海量啊!喝成这样了还能歌舞嬉戏!”
林青嘻嘻笑道,显然这些土著的所为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所希望看到的不是这般场景。
靠在船舷边上看热闹的所有伙计,都心照不宣的狂笑了起来。
他们的所爱是野民们的酒后乱性,在这海国孤岛,上演一出落日下的春宫图。
怎奈这些土著如此贪恋美酒,如同吸食了忘忧花的毒蛊一般,尽然忘却了男女间的欢悦之事。
那个时候除了林兄和田伯年龄少长之外,我们全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纪。
正值青春壮年,却全做了海上孤客,终年无缘与佳人有约,真是愁煞人也!
五日之后,由东而来的海流汹涌而至,凛冽的东南信风带来了刺骨的寒意。
而西北海天之外的故国家园,此刻正是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我们该归去了。
这座我们生活了半年之久的南荒孤岛,从此也就成了这些土著野民们新的家园。
一同留下的,还有来自大汉文明之邦的酿酒之法、膳食之术和伦理之道。
这些土著今后会过怎样的世事,已经不得而知了。
后来的余生中,连接东晋汉地和天竺、波斯诸国的这条海路,我又走了不下十余趟,途中也曾遇见突发的飓风。
但再也无缘重回南荒,也从来没有在其他海商的口里听说过它。
好像我们曾经经历的这段往事,给予我等新生这个南荒乐土,只是冥想术和忘忧毒蛊中的一个幻境。
离开孤岛向西而行的第三天,噩梦再次重演,滔天的海潮阻断了归乡之路,把我们吹向了更为遥远的东方。
而这一次,船上所有人包括我和林兄在内,全都放弃了挣扎和抗争,任凭海船随风漂流。
沧海之外还是沧海,东方之外还是东方,似乎永远也靠不了岸了。
人是斗不过上天的,佛若灭我抗争又有何意?佛若救我,又何必苦苦挣扎!
过好当下便好,一切都会过去。
好在船上存粮尚多,饮水暂时无忧,每日还有美酒相伴。
管他东南西北,管他惊涛骇浪。
人生譬如朝露,唯有美酒可解
千愁。
就这么在沧海之中晃悠了半月之久,我们全已生无可恋的时候,沧海深处的遥远东方,尽然出现了连绵起伏的海岸和群山。
就如当年从东方岛上逃生归来,第一次看到迦南海岸时那般。
郁郁葱葱,莽莽苍苍,了无边际!
“少主快看!迦南海岸!我们又回到东罗马啦!”
锅盔遥看大陆早已望眼欲穿,见到久违的海岸尽然开心的嚎哭了起来。
而我早已看淡生死,没有了过去的那份狂喜之心。
只是合掌连唱了几声佛偈,感谢上天的不收之恩。
“肯定不是罗马国的迦南!也不会是西南的海国!贤弟啊!我们来到天边啦!哈哈哈!天不灭我也!”
林兄的须发已经遮住了他的全脸,只有一双赤红的眼睛还露在外边。
这些天来,这位从前无所畏惧的海商尽然也丧失了所有心劲,终日在船上饮酒作乐。
而且他最后的心愿,尽然是在临死之前喝光船上的存酒。
一年多来接二连三的飓风海难,对于林兄的打击真是太大了。
我们的商船如同中了魔咒一般,一只无形的巨手死死挡住了我们的归乡之路。
主人家尚且如此,其他的伙计便跟着一起颓废了下去,商船也因此错失了几次转舵向西的机会。
如今海岸近在前方,林兄终于又活了过来。
与船头的每个人激情相拥,手舞足蹈的如同小儿一般。
所谓乐极生悲,真是丝毫不爽啊!
我们全都沉陷在绝处逢生的狂喜之中,尽然忘了落帆减速。
靠近海岸时,又遇一股北方南下的暗流狂飙而来。
海船顿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向着岸边的石崖飞冲而去。
躲避来不及了,但听一声轰天的巨响,我们的船头与崖畔迎面相撞。
原本已是千疮百孔的船体,顿时土崩瓦解,众人的五脏六腑似乎都被震了出来。
有几位伙计更是飞出了船仓,重重栽入了旁边浅海之中。
因为帆索的阻挡,我才逃过了一劫。
“酒啊!我的老酒!林青春哥!快快下到船舱搬几桶上来!”
船体正在下沉,海边的暗流涌动,我们随时都有给商船陪葬的风险。
好在平时训练有素,稍许慌乱之后大伙便开始有序撤离,临行前还不忘带走各自防身的兵器。
秦冲和锅盔机警过人,先后纵身跳上岸边的石崖,然后伸出刀鞘把其他伙计一个个拽了上去。
林兄的手下也都是忠诚之辈,老爷有令救酒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这几个瓜娃硬是在船体沉没前的片刻功夫,冲进底舱搬出了十几桶薯酒,扔进了旁边的浅滩之中。
我们这些落魄之人夹着酒桶、相互搀扶着淌过海边的浅水、爬上山石嶙峋的海岸,第一次踏入这个陌生的新大陆。
发现海岸上已经站满了密密麻麻的土著,正在翘首围观着我们的到来。
黑发赤脸、身形挺拔、褐红色的衣袍似曾相识。
我的第一错觉,仿佛来到了东土河西的天之山下。
而这些土著,便是我家祁山马场的羌人大哥木塔尼尔和他的族人们。
(本章完)
商与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