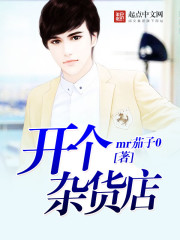第十节
转眼阳春三月,在成都这个城市里,人们却因为从来没有见识过真正的严冬而忽略了这个时节的可贵。城东的桃花,城北的梨花,城西的杜鹃,城南的海棠,更不用说城中刘禅亲自下令种植的芙蓉。虽然人们都不知道刘禅为何要在成都大街小巷到处种下芙蓉,但那花团锦簇的感觉却让这个战乱中的世界多了不少漂亮的颜色。
清晨,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浅浅的芙蓉清香中,人们纷纷的从暖和的被窝中爬了起来,纷纷钻出门外,见人就问:“皇帝陛下时候出征?”这个消息来自张大富的报纸。这个原来叫张富的人听说本是张天师的子孙,却因为发明了报纸这个东西人被刘禅亲口改名叫了张大富。其实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里的人们都不认为这个一年交几十个铁钱就能看一年的报纸能赚到多少钱,而且这个报纸还是每个月就出三份。但是听皇宫里靠近皇帝陛下的人偷偷传出来的话,说是就算一份报纸只赚那么一个子儿,那在整个城市里那么多户口,就算每十家订一份,也足以让张富成为张大富了。更何况还有民间偷偷流传的,说是皇帝陛下甚至给钱给张大富,让他刊登自己想看的文章。“这个实在是很没意思,”很多人都这样想,“自己喜欢看,就自己看就是,为要花钱了让大家一起看呢?”而很多狡猾的人却很快从皇宫里传出地话所动,纷纷早机会做成了生意。只希望自己的姓氏后能跟上个大富两个字,连成都卖烧饼的也是多了不少,还纷纷打出了订一年烧饼包送到家门的口号。
钟繇将刚满一岁的钟会交给侍女,将左右屏去,才回头看了身后的董祀一眼,董祀赶紧迎上前轻声道:“仆射大人,我等忠心耿耿从千里之外来投。而此次陛下北伐,却并未有我中原一人伴驾。以卑职之见。莫非是那庞……”钟繇将手摆了摆,轻轻的嘘了口气,才道:“陛下乃是有大智慧之人,如今军、政首辅皆乃先主老臣,但以钟繇之见,如今军政分离,分明是要避免一方做大。从此事来看。恐怕陛下也对其有所顾忌…….”刚说到这里,钟繇将茶水捧起来润了润嘴唇,这个茶水听闻是用开水泡出来地,有个逸事,说是陈到从陛下的一句话中体会来地,而后陈到的家人反复弄了半年,又去陛下那里偷来只言片语才做成的。如今成都人都以饮用这种清香无比的泡出来的茶叶为贵,连钟繇也不离开。很是喜欢那种一股浓似一股的清香。
钟繇将茶杯放在几上,接着道:“陛下对朝廷,无论是内阁还是军机处并非绝对的信任,而我中原来者,除了文则,并无半点军权。而文则又不与任何人交往,此次密传他南下,只带了武馆中十余个弟子……”叹了口气,钟繇接着道:“如今能居高位,乃是因曹皇后之力,老夫当年也幸而能对陛下宽厚有加,才使得如今我等能居庙堂之上,比之蜀中旧人也不遑多让。”说到这里,钟繇忽然转过头来,盯着董祀道:“听闻你收留了一个从许昌来地罪人。可有此事?”董祀一听。忙上前悄声道:“乃是当年曹植心腹杨修。臣只知道当初其将曹植隐在许昌,自己却偷偷在许昌开禁之后。从许昌易装逃到成都来。”
钟繇沉吟片刻,才道:“听闻此人机敏无比,更兼通晓军事,曹植将其依为臂膀。只是此人狂妄自大,侍郎可将他好好管教,或是能成为我等之奇兵也为可定。”钟繇曾经亲耳听到过刘禅演说当代豪杰,亲口夸赞杨修机敏聪慧,计谋百出,才能只略亚于张松。董祀听了,忙恬声应了声是。
两人各有心事,沉默片刻,钟繇忽然又道:“不知昭姬近日可去皇宫?”董祀面色微动,答道:“卑职拙荆最近常在曹皇后处走动。”钟繇听了,悠然道:“陛下对你的拙荆甚是礼遇,非常人可比。最近听闻马贵妃已有身孕,不妨让你的拙荆常常去走动走动,莫要失了亲近。”董祀顿时面色微红,自己那么点小心思居然被钟繇开穿,只得呆呆的跟着点头。钟繇看到董祀模样,笑道:“陛下甚有文采,但最近却并无佳作,昭姬若能常去走动,或能让陛下一唱胸臆。”蔡琰被所有的人都称为昭姬,而不是董夫人,这已是董祀心中难去的阴影。甚至现在自己成为侍郎,也常常被人认为是沾了昭姬的光。
皇宫中传来一阵号声,低沉的声音如攀天之龙一般,声音慢慢地放开了去,顿时全城的人都听到了这个号声。顿时城市热闹起来,人们纷纷往北门跑去,立刻便将通往北门的大道两边挤得满满当当。两排义务兵拼命的维持着大道两边的次序,街道上早已用水轻轻湿润,一阵凌乱的马蹄声传来,远远看见一个威风凛凛地将军带着几十个侍卫绷着脸先出了皇宫,人群顿时起来,有些见识的竟传出这个将军就是陈到陈叔至的消息。
刘禅手中牵着年仅六岁的刘永,在伊默等一班内臣的伴随下走出皇宫。刘永紧紧抓着刘禅的手,却不愿放开。伊默将刘永拉着,笑道:“陛下转眼就回,公子只要能好好读书,必能让陛下早归。”在刘禅新颁的法令里,皇子没有得到封号以前,都只称为公子,这倒是和战国时期一致,而皇子要得到封号同样需要功绩。
刘永却好象没有听到伊默的话一般,只拉着刘禅的手不肯放。刘禅也对自己在这个时代唯一的兄弟有了几分眷恋,将刘永地手轻轻拉开,柔声道:“哥哥只要将坏人赶走就立刻回来。”看着刘永一双泪光闪动地眼睛。这个兄弟懂事以后就没有见过父亲,将这个“皇帝哥哥”早当成了依靠一般。半晌才一声不响地放开刘禅地手,这个不爱说话的兄弟终于放过了刘禅。
刘禅在董允与费祎和一干侍卫拥护下,转过身跃身上马,便头也不回的望北门奔去。身后偌大的皇宫内,几双盼着回望的眼睛只盼来一个远去的背影,虽然已经过两个多月地缠绵。却依然让眷恋的神色让旁人们忘记了她们都是皇室中上上之人。
出到城外,会合关兴与张苞统领地一万御林军。万余人马一路向北。沿着诸葛亮所建造的笔直大道片刻便看到了送行的群臣,诸葛亮站在当先,其次是内阁数人与侍郎们以及成都大小官吏,甚至看到了刘璋站在其中,而刘循正一脸热切的站在父亲的身边。刘禅与众人纷纷别过,带上在旁边等候已久的庞统等人,一路北上。
沿当初入蜀之路。过广汉、绵竹、剑阁,从马鸣道口穿过,历经数日,终于赶到定军山,黄忠征北军主营便驻扎在此。刘禅赶到定军山下,只见方圆十余里都已被营帐与旌旗所覆盖。黄忠和严颜与一干武将纷纷从主营迎出数里迎接刘禅等人,刘禅与众人见过礼,未等走进营帐便开始打听夏侯渊动静。只因为在这个时代交通实在不便。信息传递更是慢得惊人,张松常常捧着半个月前的军情来给刘禅汇报,让刘禅除了能多知道点事情外,只能徒呼奈何。黄忠刘禅问起,忙将最近军情一一说了出来。
原来此时夏侯渊并未出兵来犯,只是长安各地都在盛传夏侯渊将为曹操复仇地消息。而这个妙才将军自从到了长安便一直在扩军备战。但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夏侯淳已经从许昌来到长安。
刘禅一行核心十余人来到营帐,在主位坐了下来,道:“高祖龙兴于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终于囊获关中。今日诸位何以教朕?”旁边董允迅速从侍卫手中取过一副地图挂在刘禅身后,只见其上正是汉中与雍州各地城市关隘详图。
此事在庞统心中早已盘算数月,见众人都不说话,便道:“出散关而兵逼陈仓。若能先借来羌兵。便是一条坦途。但我军骑兵不足,平原作战非我之长。出斜谷。过五丈原而击鹛坞,但如今鹛坞有夏侯渊大将徐晃大军镇守,只怕耗日时久反被夏侯渊所算,而此地一路向东,去长安路城居中。若出子午谷,”庞统顿了顿,接着道:“前次魏延将军兵出子午谷为司马懿所算,如今只怕夏侯渊已经加强兵力,非是等闲可破。”说到这里,庞统便不再说下去。
黄忠急道:“依士元所言,三关皆不可过,莫非要我等飞到长安?”
“正是,”庞统微微一笑,接着道:“某与吴天松已有一策在此。”说完,便将眼光转向吴华,众人纷纷将眼光聚在吴华身上。
吴华忙站起身来,道:“陛下方才已将我等之策略说出大半,我等所想,正与高祖同。只是反了过来,乃是明度陈仓,暗修栈道!”说到这里,吴华来到地图前,接着道:“自秦岭斜谷之西,有一小谷名曰绥阳小谷,乃是斜谷分支。我军可遣大军自斜谷出击,过谷之半既改走绥阳小谷。如此便可避开鹛坞之敌,而从此地向北不过一日既可抵达陈仓……”
未等吴华说完,严颜抢道:“此路莫非是庞辅所言陈仓之道?”
吴华摆了摆手,笑道:“我军若从此地出击,便可顺利到达关中,此时我军便不再进军,而是西征凉州!此时,若夏侯渊引兵前来,陛下则下令赵云将军从上雍出奇兵穿子午谷进击关中。若夏侯渊固守关中,我军可先让马超将军收复凉州各郡,再徐图关中。”
“若夏侯渊进击汉中,我等当如何?”黄忠沉声道。“莫非两位军师将陛下当做此行诱饵?”
庞统笑道:“若夏侯渊真若此,我便与赵云将军两路大军一同进击长安,则关中将非曹家所有。夏侯渊深陷汉中,必然首尾不能顾,必为我所破。”
刘禅听了庞统与吴华的说法,才知道竟然将自己的御驾亲征当成了诱饵,但这正是成功的关键,让刘禅不由的一阵心动。于是沉声道:“此事就此为止,明日再议。各位先下去多思量几分。”众人本要再论,但见刘禅面带疲惫,也各自散了去。
庞统紧跟几步,跟在刘禅身后道:“夏侯渊不敢进犯汉中,乃是畏惧山谷难以逾越。因此只望陛下能进击关中,如此他便可以己之长胜我军骑兵缺乏之短。但骑兵利野战,而步卒擅守城。若我军能抢占城池,便如在关中插入利刃,望陛下慎之。”
刘禅点了点头,笑道:“听了诸位所言,朕已有定义,明日再论。”庞统听了,只得下去。几个使女将刘禅迎到一个热气蓬蓬的水池旁边,侍侯刘禅泡在池中。让刘禅终于能从数日的马背生涯中舒展过来,闭目将庞统地策略想过一遍。虽然这个策略有将自己当做诱饵的嫌疑,但中原兵力强盛人才济济,若自己不将倾国之力用上,确实也难以突破秦岭。但以赵云去突破郝昭的子午谷,只怕是……赵云在刘禅的心中,并非是良将之才。在赵云一生戎马中,最多的是如何在危难时候保全,而不是在征战中获取胜利。
“赵云的能力是否真得值得信赖?”刘禅心中不由得打了一个问号。“若自己被困在陈仓而赵云却无法突破子午谷,那自己将不得不刹羽而归。”想到这里,刘禅想起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无赵云那么耀眼,但绝对实用,那就是自己秘密调到身边地魏延。
魏延带着自己从泸水带来的几个侍卫,正在一个偏营中静静得坐成一团。一个侍卫仿佛已经无法忍耐这个安静,将身体动了动,却被魏延一个眼色逼得一颤。
“将军,”坐在魏延身边的一个侍卫小声的叫了一声,魏延恩了一声,仿佛给了他几分胆色。舔了舔嘴唇,这个侍卫接着道:“四征将军皆是中将军,而只有将军是少将军,如今陛下更将将军从征南军团召到这里,莫非是还要追将军当初擅击子午谷之罪?”魏延呜了一声,却不说话,只将地上盯着,仿佛那才是他的战场一般。
“谁!”忽然帐外一个侍卫厉声喝道,魏延抬起头来,紧接着,便看见陈式将一个文臣模样的人推了进来,正是董允。董允笑嘻嘻的阻止了魏延起身,笑道:“陛下有秘旨给你,令你照秘旨行事。”说着,便将一个牛皮封住的信封送到魏延面前。魏延忙接了过来,取掉牛皮信封上的封印。只见其中放着几张布帛。展开面上一张,只见上面写道:“速去上雍!一旦得令即夺向宠军权,统领向宠本部一万士兵以及所有义务兵偷袭子午谷进击长安!”下面一张,却是一个下给向宠三兄弟的旨意。
魏延立刻收起牛皮信,低声喝道:“全部给我起来,马上出发!”众侍卫一听,赶紧跳了起来,去拿各自行装。董允一张手挡住魏延,笑道:“陛下说,若将军要走,必须脱下身上装备,陛下已经送来衣服让各位穿了出去。”魏延一听,笑了笑,道:“陛下想得可真是周全。”一边说话,一边几把将身上侍卫服脱了下来。从董允身边地袋子里找出几件衣服来。顿时本来雄赳赳地侍卫立刻便成了几个小兵。
魏延与众人待董允离开,立刻趁着夜色与众人一起穿出营帐,顺着营帐犄角偷偷的跑出军营,“碰巧”寻了十余匹马,一行人对着刘禅营帐方向磕了几个头,便起身跳上马背风驰电彻一般望东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