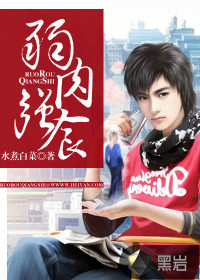一回到房间中,伊曼纽尔就立刻打开行李,从中抽出两张国库券,一本支票薄和几份产权转让证书,他将这些东西和钱夹一起装进了外衣内兜,又把外衣紧紧地裹在身上。银行家当然清楚,这种时候生命比钱财重要。可换一步来说,假如他失去了这笔钱财,他大概也无力保住自己的生命。这笔就是他挽救伊曼纽尔银行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努力失败——他很清楚,自己唯有以鲜血洗刷银行破产的耻辱。
弗朗辛检查了一下房间的门窗,但木制的门闩早已朽坏,根本起不了作用。于是,他拖过一把椅子抵在门前。这样一来,他就只好把行李堆放在房间里仅有的一张破旧的桌子上了。弗朗辛极其冷静地做着这一切。最后,他手里握着了上了膛的手枪,倚坐在床头。弗朗辛轻声对自己说:“这可真是一场冒险。”说完后,他吹熄了蜡烛,独自面对深沉的黑夜。
这间简陋的旅馆只在每个房间里预备了一支蜡烛,因此艾诺克小姐和她的贴身女仆只好守着这唯一一支蜡烛,挤在房间中央,瑟瑟发抖地盼着天亮。
维兰则坐在桌前,翻开了一本《名人传》,想藉此驱散心中的不安。
克里斯蒂娜在父亲的抚慰下沉沉睡去,兰德尔坐在另一张床边,手中举着蜡烛,守护着他的女儿。她还不满二十岁,烛光照着她那天真无邪的面庞。旅客中大概只有她在熟睡,什么能比庇护在父母的羽翼下更令人心安呢?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还不到十一点,夜色尚还深沉,艾诺克小姐房中的蜡烛却快要烧尽了。艾诺克小姐看着在烛心中上下翻腾的一点火苗,声音颤抖地说:“好玛格丽特,你去找一点蜡烛吧。”
“小姐,”女仆同样在战栗,“我该上哪去找呢?”顿了一顿,她补充说:“或者,我们向其他先生们借一借吧。”她明显希望安德丽娅可以和她一起出去。
艾诺克小姐同意了,她放下架子,和女仆一起推开了房门。
走廊里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漆黑一团,而是有一点火光。那是莫里赛特一手端着蜡烛,一手捏着手枪,在进行一次巡视。
弗朗辛先看到了这两位女士。他收起手枪,在她们面前停下了脚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莫里赛特先生,”女仆回答:“我们的蜡烛快点完了,可以向您借一点吗?”
“乐意效劳。”弗朗辛递过手中的蜡烛,“不过,如果想燃到天亮的话,恐怕还需要再取几支吧?”
“可哪里会有蜡烛呢?”
“楼下柜台里应该会有,”弗朗辛看了看艾诺克小姐和女仆,“你们愿意一同下楼取一趟吗?”尽管明知道楼下只有两具尸体,但恐惧的本性总是存在的。
或许是因为可以有人一道下去,玛格丽特答应了。
“走吧,”弗朗辛说,“不必拿蜡烛,楼下是燃着煤油灯的。”
两个人走远了,艾诺克小姐赶紧拿着蜡烛退回了房间。
十分钟过去了,两个人没有回来。在此期间,安德丽娅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她没有敢出去。但二十分钟过去后,艾诺克小姐就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她端起烛台,鼓足勇气走出了门。但她仍不敢下楼,于是,她站在走廊中,看着其它人的房间,试图从中找出一个可信赖的人。终于,艾诺克小姐走过去。犹犹豫豫地敲响了记者的房门。
此时,博得抵挡不住困倦,手肘支在桌上打起了瞌睡,一旁的蜡烛也几乎燃到了头,骤然响起的敲门声惊醒了博得,他惊跳起来,看到了桌上的怀表,指针指在十一点半的位置。谁会在这么晚的时候前来呢?维兰呼吸了一下,尽可能使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是谁?”
听到记者的回答,艾诺克小姐稍稍松了口气:“记者先生,是我,安德丽娅·艾诺克小姐。”
这个回答远远出乎了维兰的意料。想想吧,一位公爵小姐,深夜去敲一位男士的房门!不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倒也是无可厚非的。出于热心,博得还是打开了房门。
艾诺克小姐尽量清楚地向他讲明了事情的原委。博得在恐惧的气氛中仍维持了适宜的礼仪,他向艾诺克小姐伸出了手臂:“那么,艾诺克小姐,我乐意陪您下去。”
当两人走在楼梯上时,博得以一位男士在这种时刻应该保持的镇定态度向艾诺克小姐说:“小姐,我希望您有所准备,此时楼下或许会是一幅凄惨的景象,也许您更应该留在楼上。”
艾诺克小姐脸色苍白,但她没有接受博得的建议。和一个人待在黑暗的走廊中相比,与别人一起面对尸体横陈的大厅或许更能让人忍受。
尽管如此,当两人来到楼下,看到眼前的一幕时,艾诺克小姐还是失声尖叫了起来,博得也发出了恐惧的喊声。
玛格丽特的身体立在大厅中的一根柱子前,一把短刀穿透了她心脏,将她钉在了柱子上。弗朗辛·莫里赛特倒在柜台和沙发间的地板上。
夜枭第一个冲下了楼。他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然后毫不留情面地向艾诺克小姐呵斥道:“麻烦您闭上嘴,别像只猫一样招人讨厌。否则的话,我就把您也钉在这根柱子上!”这个强盗的语气表明他确实做得出来这件事。艾诺克小姐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她立刻安静了下来。
夜枭在大厅走动着。他看了看玛格丽特的尸体,又俯身去检查莫里赛特的情况。那位退役军人也走上前。但他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咽喉上的一道伤口表明弗朗辛在瞬间被这致命的一击结束了生命。林伯劳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向莫里赛特默立片刻,随后,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尊重,林伯劳半跪在尸体旁,将莫里赛特的遗体摆放端正。当林伯劳抬起弗朗辛的手臂时,他忍不住低呼了一声:“天哪。”弗朗辛的右手几乎被齐腕砍断,看得出他曾试图挡住迎面砍来的一刀。夜枭翻开莫里赛特的衣襟,那把象牙柄手枪仍别在原处,没有开过火。夜枭轻蔑地笑了一下:“戴惯了白手套的手是不会开枪的。”他站起身,背对着身后的人问道:“他们为什么下楼?有人知道吗?”
博得回答:“是艾诺克小姐托他们下来取蜡烛的。”
那位强盗没有理会博得,他在大厅中转了一圈,停在了安德丽娅面前:“艾诺克小姐?”
安德丽娅直直地盯着他,不知道该不该回答。
夜枭的声音无比柔和,在暗夜中如夜莺般悦耳;“我听说,您与德?罗斯林子爵的婚期就订在下个月,您在这个当口出门旅行吗?“
艾诺克小姐脸色更加苍白了,但她还是一言不发。
“您的未婚夫——您清楚我指的不是罗斯林子爵——大概在奥特伊等着您吧?也许你们在路上需要传递个信息,对吗?”夜枭的语调骤然一变,严厉得令人生畏,“艾诺克小姐,您究竟派您的仆人下楼干什么?”
“没有,”安德丽娅在夜枭的逼视下瑟瑟发抖,她近乎低泣着哀求道:“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是因为这一原因出行的,可我真的没有让玛格丽特给他送过信。我说的都是实话……”
“够了,”那位退役军人此时站了起来,插在了夜枭和艾诺克小姐之间,毫不畏惧地回视着夜枭,“你没有权利审问别人!”
一时间,所有人都以为马上就会有一场争执甚至打斗发生。新闻记者和银行家下意识地向后退去,只有克里斯蒂娜,这位做女儿的,以超出她这一年龄的勇气走上前,坚定地站在了她父亲身边。
片刻会后,夜枭笑了笑,移开了目光。他绕过林伯劳先生,换用一种较温和的态度向艾诺克小姐问道:“抱歉,艾诺克小姐。请允许我再问一件事,您了解您的仆人吗?”
“啊?”安德丽娅还没有从惊吓中缓过来。
“就是说,您认为,您的这位仆人会不会暗中给艾诺克公爵通信,透露你们的行程,以便公爵在适当的时机阻断您的计划呢?毕竟,违背婚约对于名门望族来说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
艾诺克小姐点了点头,惊讶渐渐取代了恐惧;“这有可能。”
夜枭转身走开了:“那么,艾诺克小姐,您不必担惊受怕了,这一路上会有人保护您的。您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您的未婚夫或许与强盗来往。”
“强盗?”这回银行家不能再假装事不关己了,他尽量以一种轻松的口气问道:“见鬼,您能不能说得再明白一些?”
夜枭用拇指指了指那柄短刀:“这还不明显吗?”
“您简直把我搞糊涂了。”博得大声说,强烈的好奇又一次占了上风,“这些又与艾诺克小姐的女仆有什么关系呢?”
“来人是为了不让她出去送信而杀死她的——应该看得出来,仆人的衣服被搜过。”夜枭的语调一如平常,“按这位小姐的说法,她只可能是去给艾诺克公爵送信的,因此我只能认为那位强盗是被艾诺克小姐心仪的那位未婚夫委派来的。”
“像您说的这样,那位强盗误以为从楼上下来的女仆是要出门送信的,于是……”
“是的。”夜枭代他说完了这句话,“一位强盗是不会只带一把短刀的,既然已经动手了,一个人和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弗朗辛?德?莫里赛特落得这个下场我一点也不奇怪。”
新闻记者略带责备地看了他一眼:“您不该这样说话。”
“好吧,”夜枭耸耸肩,“我不应该强求莫里赛特先生有太好的表现,毕竟,对方是躲在暗处,突然袭击他的。”
“躲在暗处?”
“听见有人下楼,那位强盗不会先躲起来吗?”
“可是,”记者环视了一下大厅。“难道他躲在柜台后吗?”
夜枭反问道:“除了这里他还能躲在那里呢?”
“可这样他就要和两具尸体待在一起了!”
“那又怎样呢?”夜枭装作丝毫没有理解博得的担心。
博得只好换了个话题:“就算我认同您的观点,那又该怎么解释这种行为呢?”他指的是可怜的玛格丽特,“总不会是为了向艾诺克公爵示威吧?”
“当然不是,我想,这大概和他藏身的地方有关吧。”夜枭以一种懒散的神气说着,走到柜台后面。他右手忽然在腰间一拍,紧接着一扬手,一把短刀从林伯劳和艾诺克小姐中间掠过,深深地插入了后面的楼梯木柱中。
安德丽娅又惊叫了一声,紧紧地缩起了肩膀。兰德尔看着他,冷冷的说:“夜枭先生,欺凌弱小可算不得什么本事。”说完,他用受过伤的手臂拔出了短刀,向夜枭掷了回去。
夜枭抬手接住了刀刃,平静地说:“谢谢。”把刀收回了腰间的刀鞘中。
至此,整个场景已经被勾勒了出来。一位强盗受艾诺克小姐未婚夫委托来到这里,正赶上玛格丽特和弗朗辛从楼上下来,强盗躲进了柜台内侧。之后,弗朗辛走近柜台取蜡烛,女仆则因恐惧而落在后面。强盗却误以为玛格丽特要借机出去给罗斯林子爵送信,急于阻止她。因为自己被柜台所阻挡,他在匆忙之间掷出短刀击杀了玛格丽特。同样,面对近在咫尺的强盗,弗朗辛来不及拔枪抵抗即被杀害。随后,强盗搜索了女仆的衣兜,没有找到任何信件,只好离去了。
事情已经清楚了,可有的人并不肯到此为止。
退役军人开口了:“众位,我在战争中听觉受到过损伤,往往听不见远处的声音。”人们奇怪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说这些的用意。
“因此,我可以发誓我当时没有听到楼下的动静。”林伯劳突然矛头一转,向众人质问道:“可是你们呢?难倒你们就什么都没有听到吗?”
“也许……”记者犹豫着,一时不敢轻易的否认。
“我确实听到了,但我没有,或者说我不愿意往坏处想。”银行家谨慎地选择着言辞,“对此我表示歉意。”
退役军人锐利的眼光从他们身一一扫过,最后停在了夜枭身上:“那么,您呢,夜枭先生?”
“我睡着了。”夜枭简单的回答。从他的表情上分辨不出他说的是真是假。
林伯劳没再说什么,银行低着头,专心地擦着他的单片眼镜,同时以一种含糊的态度不紧不慢地说:“少校先生,我想说的是,如果当时我下来了,现在倒在这里的就会是三个人了。”
林伯劳尖锐地回击道:“原来如此,看来金融家大概都要先去订购一颗大理石的心吧?”
“您错了。”夜枭接过了这句话,“这是理智,不做无所谓的牺牲。您是军人,假如您的上级命令您去夺取一个棱堡,您难道会直接率领部队迎着火力冲上去吗?您也会先部署兵力,把伤亡降到最少吧?”
“理智并不是怯儒的理由,”军人反驳道:“如果兵力充足,当然谁都有勇气带领军队投入战斗。但真正的军人,即使是在敌众我寡的时候,也应该浴血奋战到底。”
夜枭以一种冷淡的语气说:“行了,行了,您自己手上还沾着鲜血,却来谴责别人吗?”
“您没有听说过这句格言吗?”林伯劳庄重地说,“地狱中最热的角落,是留给在那些别人处于危难中仍袖手旁观的人的。”
听到这句话,人们都不由得沉默了下来。艾诺克小姐举起了双手,呜咽了一声,好心的克里斯蒂娜连忙搀扶住了她。
大厅角落中的落地钟在此时鸣响了起来,打破了沉默的局面。钟声本来是低沉暗哑的,但在这一片寂静中却显得分外清晰沉重,如同是对在场的每个人的审判。
终于,还是夜枭先开口了:“好吧,少校先生,我为我刚才说出的话道歉。不过,半夜两点可不是开庭的时间,我请求您允许大家都回去吧。”
“我没有这种权利。”少校生硬的回答。“这是良心行使权利的地方。”
夜枭不置一词。他俯身从柜台下翻出一捆陈旧的油烛,放在台面上,然后向楼梯口走去。当他经过少校面前时,他停下了,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您先请。”
林伯劳看着夜枭,后者的行为确定是发自诚意的。于是,兰德尔向其他人略一点头,带着克里斯蒂娜走了上去。
博得清了清嗓子,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建议,大家最好聚集到一间屋子里去,也好互相照应一下。”
“我不反对,”夜枭站在楼梯上说,“反正我是不会加入的。”
十分钟后,记者博得,银行家伊曼纽尔和公爵小姐艾诺克都坐在了博得的房间里。桌上和壁炉上都点上了蜡烛,摇曳的烛光充盈着室内,使人稍微安心了些。三个人围坐在桌旁,一开始还尽量找些话题闲谈,但随着倦意的袭来,三人先后伏在桌边睡去了。
;
本站重要通知:请使用本站的免费小说APP,无广告、破防盗版、更新快,会员同步书架,请关注微信公众号appxsyd(按住三秒复制)下载免费阅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