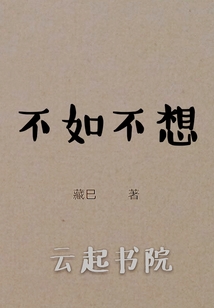手术室外,我坐在地上,缩在墙与凳子夹出的角落里。父母让我起来,我不答应,我只知道那样舒服,他们明白这是安全感。手术室的灯亮了好久,灯熄门开那一刻,我才感到自己的脚麻了。
母亲说大哥洗了胃,已经没事了。
我被父亲抱着,“爸爸,大哥为什么要吃石头啊?”
父亲没有回答我,他转头的时候,新生的胡须擦到了我的鼻尖。母亲低着头没有看他,我搓了搓鼻子。
假的没错,那什么是错?无知没错,那谁来弥补过错?错都错了,后来赎不了从前的错。
大哥和普通人不一样,他有“智力障碍”。我没觉得他可怜,他很幸福,脑子里只用装纯粹美好,心里不用记浑浊丑恶,不用学着长大,维持喜怒哀乐。他喜欢玩,我们就让他尽情玩。当我和寻安都还小的时候,我们跟着他;当我们过了爱玩的年纪了,我们陪着他;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离家越来越远,离家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念着他,但我们无法做到时刻守护他的周全。陪他玩的时候,大哥会一惯表现出开心。他把自己感受到的孤独本能藏了起来,我知道。
“南南妹妹,寻安弟弟,我们一起去玩吧,你们又好长时间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们长成了一米多的大人,大哥还会拉着我们陪他玩。
“你们就陪他去吧。”上了大学之后,母亲的衰老过程逐渐清晰。我承认她确实不是小龙女,虽然她的素衣一如往昔,施魔法的密室也原封不动。母亲在发现大哥患病之后憔悴得愈发迅速,她这一生都要照顾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她拜托我们的时候很无奈,就像一个走投无路的人祈求陌生人时的无奈。我们不是陌生人,是亲人,所以心疼她,不是同情。
“大哥,我们陪你。”我拉住寻安的胳膊,示意他说几句话。
“我们去哪?”寻安比我高出一个头。他不愿跟着去我知道,但是我的暗示他不能视而不见。
听到我们都说去,大哥手舞足蹈地往外跑,叫我们跟上。我们被他的愉快感染,也就由着他带路。
黄了的水稻更有食欲。青的时候不觉得,黄了之后才会把它们与自己每天都吃的米饭挂上钩。脱了黄色稻壳的米粒白得诱人,吃进嘴里的米香四溢,是把鼻子使劲往或青或黄的稻子里嗅不到的。下半年种的稻比早稻更香,秋天才是果实成熟的美丽时节。南方养水稻,我们村尤其。村长没有告诉我年产量的数据,数学好且空间感强的人瞧一眼占地面积应该就能估算出来,我旁边站着的寻安刚好就是。
“是一个很长的数字,往长了想就是。”不可一世的口吻,好像承包了这片田的地主。
稻子熟了,其他瓜果也能吃了。大哥带着我们去了村里一户人家的橘园,树上挂着的果子黄澄澄的,比大片的稻子还黄,看起来很诱人。大哥带我们来这的意图明显,贪吃了。
我环顾四周,园里最大的一颗树上挂了个牌子,“已打农药,后果自负!”很显眼的警示,农村里的老把戏,不是钻空子讹人,而是为了避免别人偷橘的狐假虎威。这样的虚假告示就像稻草人,一个吓唬鸟,一个吓唬人。我们不相信满园子都被喷了药,其实是不相信园主人能忍得住馋自己不吃。
“好好吃的橘子,把它们都摘回家!”大哥很兴奋,往自己的衣服兜里塞满了橘子。
但不经允许的偷摘还是理亏,何况家里不是没有种橘树。。
“咱们家有,不摘别人的。”
小孩子都不信大人的哄,小孩子从大人的百依百顺中感受爱。大哥见势就要哭闹,我便假模假样地陪着他摘。摘多了没地方放,一棵树就要被摘秃,我让他收手回家。
“好了好了,够了,咱们回家。”
小孩子精力旺盛,这才摘了几十分之一,还不够消耗他精力的几十分之一,我只能把他强硬往回拽。我让寻安帮忙,他们两个的个头才旗鼓相当。寻安让我松手,然后一把抓住大哥的胳膊,利落地弯腰起身之后,就把大哥扛到了背上。
“我不要背背!”大哥不愿被扛,在寻安的背上胡乱挣扎,橘子全被散落到地上。
“大哥,没事啊,我们这里还装着很多呢!”动静闹得很大,我怕被主人发现,想让他安静下来。我把他扶稳,让寻安赶紧离开,趁这座橘园还没被发展成是非之地。三人刚跨出门口,园主人及时赶到。
“你们干嘛呢?”
见有人来,大哥停止了折腾,他跳下背,径直走到主人面前,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
“我们在摘果果。”
“你要吃吗?给你一个。”
大哥的举动让我苦笑不得,同时脑子里琢磨该如何交代。
“原来是你啊,你又来偷我的橘子!我就说明明挂上了告示牌,怎么还会有人偷?原来是你这个傻子!”
“你说谁是傻子呢?”刚盘算好的赔礼道歉全不作数,我脑热挡到大哥身前质问,也没管前面站着的是个长辈。
“你大哥是个傻子全村人都知道,瞧你们一家人这德行,长得倒是个个标致,结果全是小偷!”
“你……谁稀罕你们家几个橘子啊!我们不是小偷!”我只能抬高气势,放大音调站稳立场,可零乱的橘子闪着刺眼的金色光芒提醒我,这都是自己作为当事人完成的佳作。
主人家从上到下扫视了我几遍,不自在的眼神逼退了我几步。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样笃定的不屑继续把我逼退。我没有证据证明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思绪浆糊般凝固,心里反击的鼓点也搅不动。
大哥不懂我们言语的交锋,但他还是害怕,于是他发出叫喊。我的理智暂时被哭声牵引,赶忙转过身来抱着大哥,让他别怕。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已经完全乱了分寸,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我彻底无助的时候会想到寻安。他一如既往的不动声色,在那些围观群众形成的背景里一眼就能找到。他知道我在看他,但我看不到那袭素衣里装着什么情绪,是不是跟我一样愤怒却无计可施。他走到主人面前,拿出几张百元钞票。
“我们不是偷,是买。这些钱,买你几个橘子绰绰有余了吧。”
“走,我们回家。”寻安背着大哥,拉着我坚定地往前走。我分明地感受到他的用力,掌心里突起的青筋咯得我生疼。
“寻安,他说话那么难听,为什么要给他钱?”我不是舍不得那些钱,有钱能使鬼推磨,给钱能使咄咄逼人的嘴闭上,但有钱显得我们没道理。
“多说无益。”他回答得潇洒,和他跳的舞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