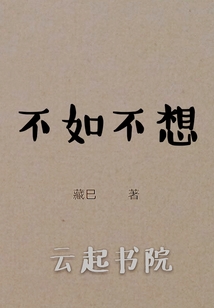我,出生于90年代,赶上了信息时代,迎来了技术爆炸。没有经历过大的经济波动,时局也很安定,但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们这一辈人大都是独生子女。我不是这大多数人中的一个,我还有两个兄弟。这种例外多少让我比同龄人更能经历一些磨人的事,毕竟从小就与人你争我抢,赢多了不骄傲,输多了也就习惯了。大哥比我年长几岁,爱闹腾,我们一家人都要为他伤脑筋。不陪着他玩吧,他哭;陪着他玩吧,就要把我俩整哭……我们都不喜欢哭,但我气哭是一件简单到不要任何技术水平的事,流眼泪就跟流口水一样是自然分泌,刺激闲着无事老找上门。至于弟弟,我和他号称是从一个受精卵分裂出来的,我比较着急,先从母亲肚子里钻了出来,结果就成了这小子的姐姐。姐弟区分得很不明确,父母常教导他要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于是我想以姐姐的姿态让他服个软都变得名不正言不顺。“弟弟”这个称呼没用过几次,我想我出世时候的着急都是干着急,多吸了几口尘世的气没让我得到任何优势,我只能对这个尾随者直呼其名,他叫寻安。寻安对跳舞无师自通,自打会走路了,就爱在我面前转圈。洋洋得意,见不得天赋异禀给他画的德性,但又必须承认这幅画是美的。他一岁开始转,转到我们二十五岁,二十五岁之后我没再见过他转。我们仨从小一起玩泥巴长大,虽然我是女生,但打起架来丝毫不会逊色,我知道不逊色的原因也不过是因为自己是个女生。男生不能欺负女生,这是长辈谆谆教导的“天生”,面对女生,男生天生不应该做一些事。做了这些事的男生不是男人,更别说是个男生。性别让男、女都吃亏,凭性别捞不到好处,没性别连好处的面都见不上。三个人,正好够人数过家家,我作为一家之母,和勉强坐上一家之父位置的弟弟,管着从不让我们操心的大哥。父亲不喜欢我们玩这种游戏,我们只能偷偷地玩,偷偷地躲在水稻地里角色扮演。
我的家位于村里稻田地的中央地带,就像一座孤岛,少了很多人气。不像其他村民一样挨家挨户,别人家的小朋友可以从这家蹿到那家,而我们只能从这块地蹿到那块地,就像地主家的儿女。这是从大范围来看,把范围缩小到离家数米内,我的家又是一栋几近完美的住宅,不仅五脏俱全,屋前还另外开垦出了一块绿地,养了些花草,种了些树木,还有一口见方小池塘。成群的小鸟迁徙来南方的时候,有几只也会选择在我家扎个窝。
南方的水乡少不了柳树。天气清明,它们锦绣,遇上池塘泛起的水雾缭绕,它们朦胧。看得清看不清我都喜欢看柳树,看不明白看得明白我都喜欢看。
院子里种了不少柳树,它们错落在池塘岸,见证着这个家的起与落。
柳树吸引着一种生灵,每到夏天嗞啦扯着嗓子叫,我都替它们觉得累,所以我们起小学会了爬树捉蝉。捉蝉就是帮它们挪个位,这样看似简单的形容,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我们乐此不疲,捉蝉就是与自己作对,我喜欢逆来顺受的生活,喜欢作对。
大哥行动矫健,理应是捉蝉的老手,我见不明白,他居然会怕这个游戏?我们上树的时候,他只会躲在门口远远地看。剩下一个寻安让我使唤,他既是我的垫脚石,又是我的捕虫网。
我喜欢垂下来的柳枝拂在身上的感觉,它挠痒的技巧无人能敌,我不闪躲,它只会温柔得让我流连忘返。后来我喜欢上了阅读、听音乐,文字把我搅进莺歌燕舞,音乐用柳枝挠我的敏感部位。有了它们,我舒服死了。夏天持续的时间长,我对世界充满好奇与期待的时候,常躺在柳树上构想这个世界还可以变成什么样。
父亲在一家化工厂工作,离家很近,一条直路,上个坡,再一条直路,拐个弯,就到了他上班的地方。我始终是对这个厂喜欢不起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里面那两根大烟囱,除了爱冒黑烟,它还定时放炮,每次轰隆那几下,整个村子都要抖三抖。父亲嘴里吐出的信息量比我读一本长篇小说还要多,他可以从早上起床一直说到到晚上上床。有时我起夜上厕所,经过父母卧室时还能听到父亲讲梦话。嘴皮子厉害的作用不小,我没问过,但父亲靠此把母亲成功侃到手的想法在我心里根深蒂固。
母亲让我骄傲了许多年。典型的东方美人,身段婀娜,性格温和,爱笑。狄更斯说,“只有在你的微笑里,我才有呼吸”,我一定得感谢母亲的微笑让我呼吸畅快。她能一袭素衣不沾一粒油烟做好一顿饭,吃饭的时候要专心,吃母亲做的饭我永远无法专心。母亲不爱出门,每天除了操持家务,剩下的时间全部留给了一间密室。看过《神雕侠侣》之后,我问母亲是不是里面的小龙女?那间密室就是她的古墓?母亲笑我说话没分寸、不吉利,她也不会像小龙女一样永葆青春。但她会摆出小龙女指导过儿剑法的认真,告诉我密室里面装着魔法,让我们一家人幸福地生活在这片田野里的魔法。我当然相信。
活物给世间带来了什么?除了感官触碰得到的人间百态,我想,更多的还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感情。
秋天,村子里的稻田会变得金黄一片。收割后的稻穗码放在一起,堆成草垛,从远处看,它们像一座座蒙古包。这些蒙古包成了我们三个小孩的第二个家,我们在这里重启合家欢,扮演一家人。
“南南,我饿!”
“南南,我要喝水!”
“南南,我冷!”
“南南,你陪我玩嘛!”
……
大哥很愿意把我当妈,遇到大小事会不犹豫地找我解决。我玩游戏不认真,很不走心把他当儿子,大小事都找寻安帮我解决。小男生之间的吸引力法则难推翻,小时候男女有别,男生只和男生玩,女生是带病毒的异类。大哥不是没有教唆过寻安离我远一点。
“小女孩儿麻烦,南南是个小女孩儿。”
寻安是天生舞者,还天生理智,他不把我当麻烦小女孩儿,倒更愿意和我形影不离。大哥明白招贤寻安得从我入手,于是玩游戏时紧扒着我,我猜。
从小理智的人从小玩不会过家家,寻安只会安静地坐在一边见我和大哥跳二人转,我清晰记得他常偷笑。
后来认识的夕雅说我胡编乱造,寻安怎么会让人发现他偷笑。他一直井井有条,不会出现无聊举动。
母亲爱给寻安穿素衣,因为只有他穿不坏。寻安一直干净,尘世污不了他,我,我们,都不能。他迎风起舞时的白色衣摆常在我眼前晃,我养成了无实物表演的新习惯,他不会时时舞蹈,我却会痴痴抬手捕捞,他的衣摆越来越透明,我永远也抓不到。我常和朋友讲述寻安在秋收田野里舞蹈时的模样,听过的人都觉得我言过其实,见过寻安本人后又心悦诚服。他的舞蹈赋予了那片生机已逝的田地另一种生命的意义,他从小就会用舞蹈表达情绪,愉快、洒脱。后来愤怒、想念。
“寻安,别跳了,该吃饭了!”
我们以石头代饭,杂草作菜,假模假样地吃饭。
“哎哟!南南,这饭好硬啊,我嚼不烂。”
我和寻安被大哥的话惊得猛然抬起头。看到大哥认真吃饭咽菜,我竟然忘记阻止。寻安拉着大哥急忙往回赶的时候,我还在原地思考他为什么这样做?父母知道了该怎么办?甚至,害怕他会不会死?
问题一连串的出现,我回答不了。眼前的残羹冷炙提醒我快回家。跑赢时间赶到时,父亲已经把大哥抱进车里。我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也许自己就是始作俑者,我做了一顿该死的饭。母亲抓着一堆东西跑出房间,看到她我更紧张了,我害怕她不再微笑。我畏手畏脚,低头站在原地不敢看她。脚尖对面出现另一对脚尖,我认出那是母亲的布鞋。她搂着我,温柔的声音让我不要害怕。
“我们一起陪大哥去医院,相信妈妈,他不会有事的。”
她还是微笑,它让我别忘记呼吸。
母亲紧握住我和寻安。发动机一声轰鸣,我一个激灵,真实地感受到一种难熬在我身体里熬,像火烧,像虫咬。一家人的血脉全部联系在一起,里面流淌着的,是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