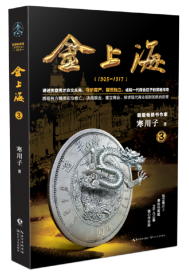偿债务俊逸轻生 走西东兄弟反目
俊逸、齐伯赶到时,阿秀的房间里亮着灯,院门虚掩着。
听到脚步声,楼梯的灯亮了,继而是楼下厅堂的。阿姨迎出来,打开堂门。
“把那包东西热一下,弄几道菜!”俊逸指向齐伯手里的袋子,里面是他们顺道买来的卤货。
齐伯笑笑:“我来吧。”
齐伯正要拐进灶房,俊逸叫道:“齐伯,让阿姨忙,您还有事体呢。”
齐伯将袋子递给阿姨,跟在俊逸身后走进堂门。
阿秀已经下来,见到齐伯,吃一小惊,旋即笑道:“齐伯,久没见您了!”
“早说要来呢。”齐伯抱歉地笑笑,看向俊逸。
俊逸打开提包,拿出一个包,递给齐伯:“齐伯,摆个香堂!”
见俊逸啥都备好了,齐伯没再说话,接过来,打开,是香、烛、牌位等一应摆香堂的物件,就动手布置起来。
阿秀显然吃惊,看会儿齐伯,又看向俊逸。
俊逸盯住阿秀。
“阿哥?”阿秀忖不透,靠前一步,小声道。
“今儿是个好日子!”俊逸的声音也很轻。
“嗯,”阿秀点头,“我看过皇历,晓得是个好日子,晓得阿哥会来,一大早就在等你,差点儿⋯⋯”顿住。
“差点儿什么?”
“差点儿它就过完了!”阿秀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
“它不会完,它永远属于你,属于我的阿秀!”俊逸握住她的手。
“齐伯,这是做什么?”阿秀看向齐伯。
齐伯已经摆好香案,香、烛也燃着了。
齐伯正要应话,阿姨走进收拾桌子,显然已把菜品备好了。
俊逸摆手止住她,转对齐伯:“齐伯,开始吧。”
齐伯点头,拿出一块红巾走到阿秀跟前,戴在阿秀头上。
“秀儿,”俊逸牵住她的手,“从今天起,从现在起,你是我鲁俊逸的正式妻子了!”
红盖巾里传出阿秀的哽咽。
接下来,在齐伯司仪下,俊逸、阿秀拜完天地。
俊逸当场揭开阿秀的盖头,转头吩咐阿姨:“阿姨,摆酒,上菜!”
阿姨摆好菜,上了一壶早已温好的酒,摆好酒具。
“齐伯,阿姨,请坐!”俊逸礼让齐伯、阿姨。
“老爷,我⋯⋯我也坐?”阿姨一脸惶恐。
“阿姨,坐吧。”俊逸再度礼让,“今儿是我与阿秀的好日子,俊逸⋯⋯谢你了!”说着亲手端起酒杯,为她斟上,也给齐伯斟了,敬上。
阿姨感动,哭起来。
齐伯端杯,老泪流出:“俊逸,阿秀,这一天齐伯想好久了,只没想到会是今晚。来,齐伯祝贺你们,祝你们百年好合!”说罢,一饮而尽。
俊逸三人尽皆饮下。
饮完三杯,齐伯又自斟一杯,朝俊逸、阿秀举起:“俊逸,阿秀,辰光不早了,我得赶回去,不定瑶儿回来了呢。”饮完,起身告辞。
俊逸、阿秀送出院门,返回也没再饮,俊逸抱起阿秀,径投二楼,放到床上。阿姨将场面收拾了,也回房间歇了。
俊逸关上房门,怔怔地坐了一会儿,下楼拿回提包并洞箫,坐在她梳妆台前的凳子上,对着她,两眼微闭,悠悠地吹奏。
乐音低沉、悠扬,在房间里回旋,似在追忆什么。
阿秀缓缓地脱掉衣服,双手托着香腮,含情脉脉地凝视他。
箫声转调,渐悲,如泣如诉。
阿秀听出来了,眼里流出泪,缓缓下床。
箫声越发悲凉。
阿秀泣下如雨,泪眼模糊地走到俊逸身后,柔软的酥胸贴在他背上,颤声:“阿哥,你是吹给我阿姐的吗?”
箫声颤抖。
“阿哥,”阿秀哽咽,“小辰光,我听阿姐讲,一听到你的箫声,她的心就碎了,人就醉了。我⋯⋯现在信了。”
箫声呜咽,俊逸泪水两行。
阿秀转到他的前面,扑进他的怀里,轻轻啜泣。
箫声戛然而止。
洞箫掉在地上。
俊逸紧紧抱住她,将她抱到床上。
俊逸脱掉衣服,将她压在身下,压得她几近窒息。
远处鸡鸣。
房间里一片昏暗。
俊逸溜下床,摸索着穿衣。
尽管声音很轻,阿秀仍旧醒了,拿被子掩住胸部,坐起来,轻声问道:“阿哥,你起介早做啥哩?”
“我要出趟远门。”俊逸给她个笑。
“是啥事体?”
“生意上的事体。”
“哦。是去哪儿?”
“西方,很远的地方。”
阿秀没有多想,拉亮电灯,穿上睡衣:“阿哥,你坐好,我来!”
阿秀跳下床,为俊逸梳头、编辫子,又从衣架上拿下西服。
“穿长衫!”
阿秀将西服挂回原处,取来长衫。
俊逸对镜审视许久,吻一下阿秀,走向门口。
“阿哥,你的包?”阿秀提醒。
“包用不上了,就放在这儿。对了,包里有个信套,过个几日,你交给齐伯。”
“好哩⋯⋯你啥辰光回来?”
俊逸凝视她,笑笑,再次吻她:“很快的。阿秀,你甭想我,我很快就会回来,我会永远守在你身边,一分钟也不离开。”
阿秀把头埋在他的胸前,点头:“我信你。我也永远守着你。”
天色大亮。
阿祥打开茂平谷行的大门,走进后堂,怔了。
挺举、葛荔背靠背盘腿坐地,模样一如入定的看相老人。
阿祥蹑手蹑脚地退到外面,见众伙计纷纷赶来,轻声吩咐:“嘘!你们先到街上溜一圈儿,放假一个时辰!”
众伙计不解,纷纷盯住他。
“愣什么呢?快走!”阿祥扬手赶人,将门关上。
众伙计心里打着鼓走了。
阿祥搬个凳子,守在柜台前面。
坐有不到半个时辰,在天使花园烧饭的女人急匆匆地走过来,敲门。
阿祥听到声音,启门出来:“嘘—”
烧饭女人一脸急切:“阿祥,伍掌柜在不?”
阿祥扯她到一侧,压低声音:“阿姨,我晓得米粮快没了,过会儿我就送去。”
“哎呀,我不是来讨米粮的。老和尚有急事体,你快去寻他!”
“晓得了。你先回,我这就去寻。”
女人匆匆走了。
想到阿弥公,阿祥不敢拖延,闪进店里,走到后院,觉得不妥,复走出来,隔着一道墙大声叫道:“阿哥—”
挺举、葛荔打个惊怔,各自弹起。
“老法师有桩急事体,要你快去!”
挺举、葛荔相视一眼,匆匆出门,如飞般赶到天使花园。
随着一声“阿弥陀佛”,阿弥公交给挺举一封书信,信封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伍挺举”三字。伍挺举一眼看出信是麦小姐写的,便瞄一眼葛荔,显然怕她发作。
葛荔白他一眼:“看我做啥?拆开呀!”
挺举拆开信封,拉出两页纸头,果然是麦嘉丽写给他的,字体又大又歪斜,中英文兼具。
挺举没敢细看,随手交给葛荔。
“又不是写给我的,给我做啥?”葛荔嗔怪道。
挺举展开纸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张纸中间,夹着一张汇丰银行的支票。
挺举拉出支票,心跳陡然加速,瞳孔放到最大,紧紧盯住上面的数字:100000。
“又是十万两?”葛荔兴奋道。
“是十万两!”挺举一字一顿。
“天哪!”葛荔急不可待地拿过来,从后面个十百千万地数着数字。
“快!”不待葛荔数完,挺举一把拉起她,撒腿跑向园外。
营业时间未到,但茂升钱庄的大门外面已经黑压压地站满前来兑钱的甬人,场面乱哄哄的,将街道堵得严严实实。
更多的人纷至沓来。
一个长者跳上高台,大声地维持秩序:“诸位,诸位,安静一下,甭吵甭闹。大家都是甬人,甭让外人把咱甬人看低了。鲁老板一向重诺守信,既已承诺,一定会兑现。请大家自觉排队,沿着街的右侧一直排下去,自己检查庄票,就按鲁老板讲的,从一两庄票开始,数额小者排前,数额大者靠后。”
众储户纷纷查验手中庄票,自觉地排成长长的一队。
开门辰光到了,但店门仍旧关着,不见一个店员。
众人觉得不对,再次喧闹,排在前面的用拳头砸门。
队伍乱了。急眼的储户全都集拢过来,将店门围了个严实。
众人正在闹腾,老潘、大把头赶到,拨开人群,站到门前的台阶上。
望到二人,众人情绪激动,纷纷嚷叫起来。
老潘站到最高处,用手势压住噪声,大声叫道:“诸位老少爷们,实在对不起大家,鲁老板这几日一直在外筹款,这还没有回来呢,敬请大家少安毋躁,少安毋躁,明朝再来!”
众人震怒,七嘴八舌,纷纷质问:
“哪能推到明日哩?”
“没钱就是没钱,把话明说,甭再欺骗我们!”
“快叫鲁俊逸出来说话!”
“对,叫鲁俊逸出来!”
“甭废话了,砸门!”
⋯⋯
众人涌向大门。
老潘、大把头死死守住大门。
众人将他俩推到一边,又推又砸。
大门被砸开。
众人齐涌进去,无不惊呆。
柜台后面的横梁上,一身长衫的鲁俊逸吊在上面。
老潘、大把头扑进来,失声悲泣:“老爷—”
众人七手八脚,将鲁俊逸放下。
老潘用手挡挡鼻孔,早已没气了。
挺举、葛荔双双赶到,见人们齐刷刷地围住庄门,低头默哀。
“诸位乡亲,”挺举高举支票,声音兴奋,“银子来了,这是汇丰支票,请大家耐心等候,我这就去汇丰兑银子去。”
没有一个储户理睬他,也没有一人看向他手中的支票。
所有人都低着头,表情哀伤。
在死亡面前,他们手中的这点儿银子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点儿银子,将一个从不食言的汉子逼到了绝路。
挺举怔了。
挺举迟疑一下,走向大门。
众人闪开,让出一条通路。
挺举与葛荔肩并肩走进大厅,看到鲁俊逸尚未完全僵硬的遗体,惊呆了。
待反应过来,挺举扑到鲁俊逸身上,将支票放他脸上,悲痛欲绝:“鲁叔,看呀,看呀,你看看呀⋯⋯钱⋯⋯钱哪,钱我搞到了,是十万两银子,十万两银子呀,我的好鲁叔啊⋯⋯”
碧瑶一觉醒来,顺安不见了。
“晓迪,傅晓迪!”碧瑶大叫。
没有人应声。
碧瑶坐起,皱眉:“咦,他是啥辰光起床的,我哪能不晓得哩?”
碧瑶又候一时,仍旧不见动静,见自己的衣服依然湿淋淋的,只好穿上顺安给她的衣服,推开房门,见外面大晴,已是中午。
碧瑶关上房门,回到屋里,瞟见桌上摆着一个信封,近前一看,上面赫然写着:“鲁碧瑶亲启。”
碧瑶震惊。
碧瑶拆开信封,抽出几页纸头,是顺安写给她的。
碧瑶读信,耳边响起顺安的声音:“瑶儿嗲嗲,昨晚听你讲起你阿爸的心愿,我如雷轰顶,一宵不曾合眼。自来上海,鲁叔待我如子,我事鲁叔如父。我爱你,我晓得你也爱我,但我不能拂违鲁叔心愿,做出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是哩,挺举阿哥在各方面都比我能干,我自叹弗如,鲁叔相中他,没能相中我,一定有鲁叔的道理。我爱你,但我不能伤鲁叔的心。爱人可以另寻,阿爸只有一个。没有我,你照样可以嫁人,没有鲁叔,你就没有阿爸了。我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离开上海,远走异国他乡,成全鲁叔心愿,成全你跟挺举阿哥的好事体⋯⋯”
碧瑶翻页,泪眼模糊,越看越快:“挺举是我阿哥,我晓得他是好人。你嫁给他,我一百个放心,一千个放心。瑶儿嗲嗲,我爱你。在这世上,我只爱你一个人。因为爱你,我不得不离开你。我要离开这块伤心地,走到天涯海角去,在那儿一个人伤心。我⋯⋯这就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瑶儿嗲嗲,永远属于你的,晓迪!”
“天哪!”碧瑶如雷轰顶,信掉在地上,急跑出来,大叫:“章虎,章虎!”
章虎走出屋子,佯作惊愕:“鲁小姐,你哪能还在这儿呢?我以为你早就走了呢。”
碧瑶急了:“快讲,傅晓迪哪儿去了?”
“咦,真是怪哩!他去哪儿你哪能不晓得?”
“快讲呀,急死人哩!”
“嗨,一大早他就寻到我,说是有桩急事体,要到外国去。刚好有班船去日本,我陪他买好票,送他上船去了。”
“船⋯⋯走没?”
“早走了,十点钟的船,这辰光怕是已经漂在大海上了!”
一阵天旋地转,碧瑶栽倒在地。
申老爷子的宅院里,葛荔推门进来:“老阿公,老阿公—”
申老爷子正在摆弄花盆,抬头看她:“啥事体?”
“鲁老板他⋯⋯寻无常了!”
“哦?”申老爷子老眉凝起,“慢慢讲!”
“阿弥公交给挺举一封信,里面有张十万两银子的汇丰支票,是麦基送给他的。挺举拿上支票赶到钱庄,鲁老板却在梁上挂了。”
申老爷子深吸一口长气,埋头摆弄花盆。
“老阿公,”葛荔的语气甚是惋惜,“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辰光!要是早到半个时辰⋯⋯”
“又能怎么样呢?”
“他就不会挂喉了呀!我们赶到时,他的身子还是热的!”
“他不是为这点儿银子死的!”
葛荔震惊:“咦,不为银子,又是为啥?”
“为许多东西,还有赎罪。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哪!”
“是哩。”葛荔凑过去,蹲在他身边,有点儿羞涩,“老阿公,我⋯⋯”欲言又止。
申老爷子继续摆弄花盆:“还有啥事体?”
葛荔嘴一噘,嗔怪:“老阿公!”
“讲呀!”
“你得看着我!”
申老爷子停住手,看向她。
葛荔脸上现出红晕:“我⋯⋯我得告诉您一桩好事体!”
“我这听着呢。”
“他⋯⋯就是那个小子,他⋯⋯欢喜我!”
“呵呵,”申老爷子先是一怔,继而笑了,“有人欢喜倒是一桩好事体哩,难得呀。”又故意皱眉,“不过,这桩好事体,老阿公有点不相信哟!”
“是真的,骗你是小狗!”
“讲讲看,你哪能晓得人家欢喜你哩?像你这种捣蛋鬼,没完没了地折腾人家,有十个小伙子也早让你吓跑了!”
“是⋯⋯是他自个儿讲出来的!”葛荔半是呢喃,“他讲,他一遇到事体,就会想到我,他还讲,他⋯⋯离不开我,他⋯⋯”陷入遐思。
“你是哪能讲哩?”
“我⋯⋯我啥都没讲!”
“是哩,阿拉小荔子啥都不会讲的,阿拉小荔子只会把头拱在人家怀里,拿胳膊搂住人家脖子!”
葛荔又羞又急:“没!”起身搂住他的脖子,揪住他耳朵,“老阿公,你瞎讲!”
“好好好,算是老阿公瞎讲。”申老爷子又开始摆弄花盆。
“老阿公,”葛荔半是说给自己,半是说给老爷子,“我想清爽了。打今朝起,我一心一意待他,我要对他温柔,我要让他明白,我也欢喜他,我心里想的只有他,我⋯⋯”
“呵呵呵呵,”申老爷子两手没停,“阿拉小荔子这是思春哩。是喽,二八是芳龄,小荔子已经二九了。若是等到三九,就是一个老姑娘,想嫁人也没人肯娶喽。”
葛荔再次搂住他的脖子:“老阿公,瞧你⋯⋯”
从汇丰银行取到的白花花的银子被依次装入银箱,一溜儿摆放在茂升钱庄的柜台后面。
钱庄职员皆穿孝服,悉数上阵,严阵以待。
兑钱的人排作长龙,在厅内盘了几道弯,由大门延伸到大街上,一直排出几百步远。前来兑银的人都在胳膊上绑了一块黑纱,神情默哀。
准备就绪,兑银开始。
老潘站在高台上,手拿一个土制的扩声器,朗声致辞:“尊敬的父老乡亲们,尊敬的储户,我,茂升钱庄协理潘冬雷,谨代表钱庄总理鲁俊逸先生,代表钱庄襄理伍挺举先生,代表钱庄所有把头、徒工,在此向信任茂升钱庄的所有储户、所有客户,致以深深的谢意。”说毕,弯腰鞠躬。
众人抹泪,低头默哀。
“茂升钱庄自开业迄今,以信为本,一诺千金,钱庄总理鲁俊逸先生正是因为这个‘信’字,正是因为有负诸位信托,方才舍身以谢。钱庄襄理伍挺举先生亦是为这个‘信’字四处筹措银子,历尽辛苦,筹到这笔巨款,我们从现在开始,正式为所有储户,所有支持茂升钱庄的父老乡亲、亲朋好友,兑现钱庄总理鲁俊逸先生的郑重承诺。”
一位长者问道:“潘协理,这些钱全是伍挺举襄理筹借来的?”
“是哩。”老潘应道,“鲁老板筹不到款,欲卖家产兑现诺言,但没有人能买,因为所有银子都被洋人卷走了。为替老爷解难,钱庄襄理伍挺举四处奔波,历尽委屈,终于在最后关头筹到这笔巨款。至于伍襄理是如何筹到的,如何为难的,在下也不晓得,在下只晓得鲁老爷、伍襄理几日来茶饭不思,天天在外面为诸位筹钱!”
众人无不敬服,交头接耳,传递伍挺举的名字。
“诸位乡亲,”老潘又道,“伍襄理总共筹到十万两银子。伍襄理吩咐,钱庄扣留一百两为鲁老板送行,五百两为钱庄与茂记职员支付欠薪及未来三个月的薪酬,余下九万九千四百两,全部用作兑付。我粗算了一下,资金充足,凡持百两庄票以下的客户皆可兑现。尽管如此,伍襄理仍旧吩咐由少到多,凡持有茂升钱庄庄票的客户,由最小数额,也即一两银子起兑,直到兑完全部现银为止。潘某在此敦请诸位亲友,视手中庄票数额自行调整排队顺序,凡违反秩序者,钱庄不予兑付。”
众人纷纷查看手中庄票,自动调整顺序。
庆泽遍体是伤,歪靠在自家楼下的一棵梧桐树干上。
庆泽身边,他的妻子与女儿抱头悲哭。
他家住在临街的二楼,楼下是个做小生意的店铺。
楼上传来钉门的声音。不一会儿,放高利贷的胖汉子从楼上走下,身后跟着两个恶汉。
胖汉子走到庆泽妻子跟前:“小娘子,我与你家老公立过协议了,房子作价八十两,小姑娘作价二十两,清账!”又朝身边的恶汉努下嘴,“带人!”
那个恶汉子走过来,一把拖过女孩子。
女孩子死死抱着母亲,惨叫不绝:“姆妈,我不去,我不去呀⋯⋯阿爸⋯⋯”
庆泽妻子死死拉住女儿。
恶汉子一脚把她踹开,将小姑娘强行抱走。
庆泽妻子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场面凄怆。
庆泽表情木然,犹如一个死人。
鲁家正堂悬挂着鲁俊逸的巨幅黑白照片,当堂摆放一口黑漆棺木,棺头贴着一个大大的“奠”字。
碧瑶没有号哭,也没有说话,只将两眼呆呆地盯住棺材。
阿秀跪在另一侧,一声不响,两眼痴呆。
齐伯一身麻衣,没有跪,盘腿坐在碧瑶旁边,一脸哀伤。
挺举、阿祥披麻戴孝,挨住阿秀跪着。
几个把头、十多个掌柜等忙前忙后。
商会大佬、宁波同乡、钱业掌柜等一个跟着一个吊唁,老潘与大把头站在门口接来送往。
祝合义来了。
祝合义焚香,烧纸,磕头,在完成一应礼节之后,双手拍动棺木,声音哽咽:“俊逸呀,我晓得你没有走远,就在这里看着呢。我这问你,你⋯⋯哪能非走这一步不可呢?天底下哪有过不去的坎呢?你聪明一世,又哪能糊涂在这一时呢⋯⋯”
合义嘟嘟哝哝,诉说一阵,将众人的泪水全都勾引出来,现场悲哭一片。
见众人全都哭起来,合义转身走到挺举背后,拍拍他的肩头,朝外努嘴。
挺举会意,跟他走到院子里。
“挺举,”合义问道,“我与汇丰约的是明天,你能脱身否?”
挺举眉头凝起,看向灵堂。
“挺举呀,”合义一脸殷切,“大家都在等米下锅哩,这事体你必须去,我数算过,其他人顶不起来。”
挺举点头。
“你准备一下,我们拿什么与汇丰谈,这辰光是求人家,我这底气不足哩。”
“我晓得。”挺举应过,再次回到灵堂里,跪在原来的位置上。
夜色渐深,该走的全都走了。
挺举缓缓起身,踏楼梯上楼。
楼上是鲁俊逸的书房,门开着。挺举走进来,拉亮灯,一步一步地走到鲁俊逸的座位上,看向他的书桌。
桌面上摊着一大堆材料,都与橡皮股有关。
摆在最上面的是两张报纸。
挺举的目光落在两张报纸上。
两张报纸都被鲁俊逸用红笔画了个圈:一个在四版的小角落里,不细心根本看不出来;另一个则是在头版头条,字体很大。内容是相关的,小角落是汇丰银行停止以股票抵押的公告,头版头条赫然刊登的是汇丰银行以股票抵押的一整版大字公告。
挺举将两张报纸折叠起来,看向空中,泪水盈出,喃声:“鲁叔,我晓得了,您走得不甘心哪!”
翌日上午,祝合义的马车早早来到鲁家,叫上挺举,直驱外滩,在汇丰银行的大楼前面停下。二人下车,走到汇丰门口,向阿三递上拜帖,讲清是大班约来的。阿三禀报,不一会儿,一个穿西装的洋人走出来,引领合义、挺举上楼,走进一个大而敞亮的办公室。
洋大班查理坐在大班桌后,正在眉开眼笑地接电话,说的是洋文,叽里咕噜,语速甚快,即使跟着麦小姐学过一阵英文的挺举也听得稀里糊涂。
大班讲完电话,放下话筒,几乎是在霎时间敛起笑容,脸皮绷紧。
引他们进来的洋人显然是个助理,对大班简要讲几句外语,指向二人。
大班的目光鹰一样射向二人。
合义走前一步,深鞠一躬:“在下是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祝合义,因商务事体拜见大班!”
大班查理站起来,既不鞠躬,也不拱手,连个握手礼也没给,出声即是咆哮:“It'stheve
ytimethatyoucomehe
e,si
ceI'mgoi
gfo
you
ight
ow!(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去寻你们呢!)”
合义没有听懂,急了:“大班?”
查理拉开抽屉,拿出一沓庄票:“Lookatthese!Theya
eall
otesf
omyou
Mo
eyHouses,a
dthetotalsumexceedi
gtwomillio
lia
gofsilve
!Theya
ef
omdiffe
e
tMo
eyHouses,
ea
lyhalfofwhichcamef
omMaoshe
gMo
eyHouse!AlloftheChi
eseMo
eyHousesa
eu
limitedliabilitycompa
ies,a
dtheNotemea
smo
ey,mea
ssilve
,the
efo
e,allthe
otesshouldbecashed!Ihavethe
otesa
dyoumustgivemethesilve
.Othe
wise,Ihavetostopa
ybusi
essexcha
ge,especiallythet
a
sfe
offu
d,toallthemo
eyhouses.That's
otall.I'llgototheMixedCou
t,sueallofthe
elatedmo
eyhousesatthelaw,a
dhaveallthei
p
ope
tiessealedup,a
dgetthemf
oze
!(好好看看这些!它们都来自你们的钱庄,总数超过一百万两!它们来自不同的钱庄,单是茂升就有五十万两。所有中国钱庄都是无限责任制,庄票就是钱,就是银子,因而,所有庄票必须兑现。否则,我将终止与任何钱庄的业务往来,终止借款给钱庄。这并没完,我还要将相关钱庄告上会审公廨,封存并冻结其所有资产!)”
祝合义一句也没听懂,因是求人,见他这般震怒,只好赔上笑脸,软声细语地自说自话:“大班先生,我们此来,是想与您商谈贷款救市一事!”
查理显然听得明白,忽地站起,用拳敲打桌面,声音更加激昂:“Fo
Rescue?YouChi
ese,alla
echeap,lazya
imalsseeki
go
lyfo
gold!Youalwaysw
iteNotesthat
eve
ca
becashed!Youalwayswa
ttogetmo
eythat
eeds
olabo
!Youalwaysi
vesti
placesthat
eve
exist!Whatyou'vegotiswhatyoua
edese
ved,yetyoucomehe
efo
escue?Tellyouthet
uth,I'mo
lyaba
ke
,whatIwa
tismo
ey.Allthe
oteshe
e,o
thistable,shouldbecashed!Notape
yisa
exceptio
!(救市?你们中国人,都是眼睛只盯在金子上的贱骨头、懒畜生!你们总是写出无法兑现的庄票!你们总想得到不需要劳动的金钱!你们总是投资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地方!闹到这步田地,你们是罪有应得。实话告诉你们,我是银行大班,我所想的只是钱。凡是这个桌子上的庄票,统统都要兑现!每一分钱也不例外!)”
祝合义继续赔笑:“大班先生,有话请讲清爽,我晓得你会讲汉语的,请用汉语,慢慢讲,凡事皆可商量!”
“Ido
'twa
ttospeaktoyou!YouChi
ese,youlazybegsi
s!You...(我不想跟你说话!你们中国人,你们这群懒惰的瘪三!你们⋯⋯)”
听到“瘪三”二字,祝合义方才晓得他是在骂人,面孔变成青紫色,身体颤抖,正不知如何是好,站在他身后的挺举猛地跨前几步,径直走到桌子前面,两眼火一般逼视大班。
大班被他的目光震慑住了,下意识地后退一步,惊愕地盯住他。
挺举语速缓慢,中英文兼具,字字如锤:“密斯托大班,阿拉拿瘪三,阿拉拿恩里猫。油阿奇特,油,麦基,麦克麦克油,麦克麦克麦基,嗷嗷阿奇特。(从袋中掏出一堆股票,摆在桌上)油洗,油阿奇特,油煤克死多克,油奇特阿拉码内!(从另一只袋中摸出两张报纸,指着被鲁俊逸圈起的两份大小不同的公告)油洗,歪奇特阿拉?油、麦基狼狈为奸,出公告哄骗阿拉,奇特阿拉,腿克阿拉码内,八抬,油拿扫里,油克死阿拉!海浮油古德哈胎?海浮油锐参?海浮油戈德?我他戈德提起油?夷佛饮油!呆佛饮油!(M
.Ba
ke
,阿拉
obegsi
s,阿拉
oa
imals。Youa
echeats.You,KimMc,muchyousa
dmuchkimMcs,allalla
echeats.Yousee,youa
echeats,youmakestocks,youcheat阿拉mo
ey!Yousee,whycheat阿拉?You,KimMc狼狈为奸,出公告诱骗阿拉,cheat阿拉,take阿拉mo
ey,but,you
oso
y,youcu
se阿拉!Haveyougoodhea
t?Haveyou
easo
?HaveyouGod?WhatGodteachyou?Evili
you!Devili
you!大班先生,阿拉不是瘪三,阿拉不是畜生。你们才是骗子。你,麦基,很多你,很多麦基,统统都是骗子!看看这些,你们是骗子,你们制造这些股票。你们欺骗阿拉钱财。看看这些,为何欺骗阿拉?你与麦基狼狈为奸,出公告诈骗阿拉,欺骗阿拉,拿走阿拉银子,但你不说对不起,反过来咒骂阿拉。你良心何在?你道理何在?你上帝何在?上帝是如何教育你的?你内中邪恶!你心驻魔鬼!)”
祝合义听得云里雾里,只是觉得解气,同时又怕事体闹僵,忐忑不安,紧紧盯住大班。
查理被挺举的浩然之气震撼了,大张嘴巴说不出话来。
挺举稍稍退后,二目如火,紧盯大班。
大班从惊愕中醒来,目光落在报纸的两个圈圈上,内心先自怯了,脸上浮起笑,绕过桌子,走到挺举跟前,热情地伸出手。
挺举也伸手出来。
二人握住。
查理语气谦恭,改用汉语:“先生,请问贵姓?”
“免贵,在下伍挺举,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挺举沉声应道。
“伍先生,幸会。我叫查理,非常乐意与伍先生这样的中国人交朋友。”查理指向旁边的沙发,礼让二人,“伍先生,祝总理,请坐!”又朝外大叫,“来人!”
显然,查理的中文很棒。
门开了,一直候在门外的助理走进来。
“为二位先生上茶!”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查理悉心听完祝合义的诉求,答应放款救市,但讲他不能完全做主,要与其他银行大班协商。
返回途中,祝合义一脸兴奋,不无叹服道:“挺举呀,没想到你这洋话讲得介好,连洋大班也让你讲得服服帖帖!不瞒你讲,我看你像是在训斥他,真正捏了一把汗哩!”
挺举轻轻一叹。
“我就记住了最后一句,‘呆佛饮油’,啥意思?”
“呆佛是恶鬼,饮油是他的心。我说他心里有恶鬼!”
“哦。”合义闷头想一会儿,颇是不解,“这个大班真还是个贱骨头。我敬他,他骂我们。你骂他个狗血喷头,他反倒笑脸相迎,礼敬有加!”
“因为他的心里有个恶鬼!”
“是哩,”合义重重点头,“挺举呀,祝叔服你了。你这心劲是做大事体的,商会的事体,你要多操心。老爷子走了,俊逸也走了。锦莱、进卿他们扛不起大事,祝叔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祝叔过谦了。老爷子一走,在我们甬商里,就数您德高望重。祝叔想让挺举做啥事体,早晚吩咐就是!”
“头疼先顾头,眼下最急的是救市。你讲讲看,查理大班会不会把款子利利索索地放给咱?方才听他讲得倒是不错,但洋人重的是利益,救市牵扯到真金白银,不见货祝叔放心不下呢!”
“他会放的。不仅是汇丰一家银行,其他银行也会放!”
“不会吧!”合义颇是惊讶,“哪有介好的事体?”
“洋人是来做生意的,市场崩塌,首先对他们没有好处!”
合义若有所思。
顺安没有去日本。
因为碧瑶的存在,所租的小阁楼不能住了,章虎这儿也不能住了,顺安得设法为自己选个新家。
在橡皮灾后的大背景下,顺安毫不费力地选中了一套新居,是一处离静安寺不远的中式院落,颇为雅致。交割的不仅是房舍,还包括所有家具及一些搬不走的用品。房主炒橡皮破产,卖房还债,这要从大上海搬回老家安徽。
章虎过来时,顺安与房主交割已毕,几个老阿姨正在打扫。章虎里里外外巡视一遍,走出房门,不无满意地赏着院中的景致。
“章哥,怎么样?”
“啧啧啧,”章虎赞叹几声,“介好个院落才八百块,连家具也配得齐整,兄弟这是捡了个大便宜嗬!”
“呵呵呵,”顺安乐不可支,“是哩。要在过去,单是宅院少说也值五千块!”
“兄弟,”章虎一屁股坐在院中的一把老藤椅上,“章哥这儿有两桩事体与你相关,想听不?”
“章哥快讲!”
“一个是你老丈人名下的所有不动产,会审公廨将在明日前往查封!”
“哦?”顺安惊讶道,“鲁家财产与会审公廨有啥关系?”
“关系大了去了。茂记宣布破产,姓鲁的名下财产必须查封,由拍卖行统一拍卖,偿还债权人。茂升单是欠汇丰银行就有三十万两贷款,且不说汇丰银行持有的茂升庄票,被汇丰告到公廨了,自然由公廨首先查封。”
“茂升的债权人多了去了。进钱庄时,我详细背过规程,钱庄若是倒闭,剩余资产理应首先偿还小额客户,轮不到洋人呢。”
“这就是我要讲给你的第二桩事体,茂升钱庄已将一百两以内的小额庄票全部兑清了!”
“啊?”顺安一脸震惊,“那⋯⋯鲁叔他为啥上吊呀?”
“姓鲁的上吊在先,钱庄偿钱在后!”
“啥人偿的?”
“你的那个阿哥,伍挺举!”
顺安目瞪口呆,好半天方道:“十万两哪,他⋯⋯哪来介许多洋钿?”
“有贵人帮他!”
“啥贵人?”
“我这正琢磨呢。”章虎若有所思,“听说他拿的是一张汇丰银行支票,十万两整,就跟你的那张一模一样!”
“难道是⋯⋯”顺安心里一动,“麦小姐送他的?”
章虎看向他,不解:“麦小姐为啥送他?”
“章哥有所不知,麦小姐相中了挺举阿哥,麦基差点儿要招他为婿呢。”
“娘希匹!”章虎大睁两眼,“要是这说,想必是了。”
“唉,”顺安长叹一声,“挺举阿哥这⋯⋯哪能讲哩,鲁家败了,钱庄破产了,有多少银子也是打水漂,啥人要他偿还这笔钱了?再说,眼下市面上银子最缺,他却把介许多银子⋯⋯”
“赚了吆喝哪!”章虎鼻孔里轻轻哼出一声,“就这辰光,满城甬人都在称颂他哩!”
“吆喝又不值钱!”顺安嘟哝一声,一脸惶惑地蹲在地上。
天色昏黑,鲁家灵堂一片阴森,俊逸的棺木前面亮着长明灯。
没有外人了。
挺举面对棺木跪着,身边是阿秀,碧瑶一人跪在棺材的另一侧。
齐伯、阿祥皆在院中忙活。明日出殡,他俩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
挺举又跪一时,猛地想起什么,在衣袋里摸几下,掏出一个信封。这几日忙得昏头,他把麦小姐的信完全忘了。自从收到信,他还真没有细读呢。
挺举展开信,就着长明灯读起来。
第一页是麦嘉丽的字迹:“伍,我很难过,我很很难过。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伤心,但我知道,一定有什么错了。一定是我爸爸错了。我爸爸是好人,他一直是我的好爸爸,但是,你那么伤心,就一定是我爸爸错了。无论爸爸做错什么,我都要对你说声对不起,说麦克多的对不起。我爱你,我爱天使花园,我爱所有天使,我到Af
ica(非洲)去,你等我两个月,我一定回来⋯⋯”
字迹歪歪扭扭,有不少错别字。
挺举轻叹一声,心道:“麦小姐,你太天真了!你根本不了解你的阿爸!”
挺举展开第二页纸头,落款是麦基,写道:“伍先生,我敬佩你,也为股票造成的结果深表遗憾。请你相信,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个生意人,我只想做生意,从头到尾都是做生意。股票成为今日状态,我始料不及。我生意失败,走投无路才冒险去做橡皮股票。起初,我只想赚点钱,但后来,中国人自己疯了,上海滩整个疯了,我控制不住局势,别无办法,只能离开上海。你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商人,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很可惜,你不能成为我的女婿。P.S.像你这样的人不应该贫困,这张支票送给你做资本,祝成功。”
这封表述流利的信当是出自里查得之手,亦当是麦基的口述。
挺举放下信,闭目,心道:“鲁叔,我晓得你有许多想不开的地方。麦基父女的这两封信,我一并儿烧给你,相信你读了,啥都明白了。”
挺举将两封书信连同信封放到长明灯上,点着火,看着火苗燃起来,搁到焚烧冥纸的大瓦盆里。
齐伯端着两碗稀粥走进,对碧瑶道:“小姐,喝口粥吧!”
碧瑶如痴似呆,没有理睬。
齐伯将稀粥放在她旁边的凳子上,将另一碗粥摆到另一侧,对阿秀道:“阿秀呀,你也得喝一碗。老爷走了,大家都伤情。可无论多伤情,饭得吃,是不?这还没出三天,我晓得老爷不会走远,就在这个屋子里,就在这根梁头上盘着,看着你和小姐哩。你俩都不吃,老爷⋯⋯伤心哪!”
阿秀的眼里流出泪水。
齐伯守了一会儿,长叹一声,将粥碗搁她旁边,转向挺举:“挺举,你出来一下。”
挺举起身,随齐伯走到院里。
“小姐、阿秀不吃不喝,哪能办哩?再撑下去,怕是要出大事体!”齐伯一脸忧急。
挺举的眉头拧起来。
“阿秀好劝,主要是小姐。”
“是哩。”
“你晓得晓迪在哪儿吗?怕是只有他能劝动了!”
“我寻他去!”挺举略一思考,拔腿走向院门。
挺举大步流星,直奔四马路的翠春园,找到陈炯,要他寻找顺安。陈炯安排炳祺寻访,自与挺举坐等音讯,聊些灾后的话题。
约过半个时辰,任炳祺打外面兴致勃勃地走进。
“有消息了?”陈炯问道。
“有,”炳祺应道,“鱼和鱼一群,虾和虾一群,那小子果然就在王公馆姓章的那儿!”
“这辰光在不?”挺举急问。
“不在。有人见他后晌与姓章的出去了,这辰光还没回来呢!”
陈炯看向挺举。
“我这就去王公馆!”
“炳祺,”陈炯看向炳祺,“带几个弟兄,陪伍兄走一遭!”
“谢了,”挺举摆下手,“没啥事体,我自个儿去吧!”
挺举赶到王公馆,隐在门外一棵树下。
交子夜时,两辆黄包车在门外停下,章虎、顺安跳下车子。
挺举站起来,疾步过去,横在顺安前面。
顺安看清面孔,震惊:“阿哥?”
“是哩。”挺举淡淡说道,“等你交关辰光了。”
章虎走过来。
“章哥,”顺安指着挺举,“这就是我的挺举阿哥!”
“老熟人了!”章虎象征性地朝挺举拱手。
“有扰了!”挺举拱手还过礼,转向顺安,“借一步说话!”言讫,大步走去。
顺安迟疑一下,跟在他后面。
章虎盯二人一会儿,慢腾腾地走向大门,闪身进去。
顺安跟有几步,语气紧张:“阿⋯⋯阿哥?”
挺举走有百十来步,站住。
顺安跟过来。
“鲁叔没了,你晓得不?”挺举盯住他,直入主题。
“晓得。”顺安几乎是呢喃。
“既然晓得,为什么不回去看看?鲁叔待你不薄,总该送个行吧!”
“我⋯⋯有些事体,这⋯⋯这还没来得及呢!”
“这辰光应该没事体了,跟我走吧!”
“我⋯⋯还有一些事体!”
“傅晓迪,”挺举目光逼视,“不是我请你,也不是鲁叔非要见你不可,是小姐需要你!鲁叔没了,家没了,小姐什么都没了,只有一个你,傅晓迪!”
“咦,”事已至此,顺安只能豁出去了,遂梗起脖子,“阿哥,你哪能讲出这话哩?小姐是小姐,我是我,你哪能把我和她生拉硬扯在一起哩?”
挺举欺前一步,目光逼射,一字一顿:“甫顺安!”
“甫顺安”三字听得顺安心底发寒,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阿⋯⋯阿哥⋯⋯”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晓得不?”
顺安再无退路,稳住步子,扎好架子:“阿哥,你这讲的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小姐有喜了,你难道不晓得?”
“有喜?”顺安假作糊涂,“她有什么喜?她阿爸没了,她当有悲才是!”
“甫顺安⋯⋯你装什么糊涂?她怀上的是你的孩子!”
“阿哥,”顺安一咬牙关,“你甭拿这个来吓我,我啥都晓得的!鲁叔偏袒你,鲁叔欢喜你,鲁叔一门心思要把宝贝女儿嫁给你,想把他的家业传给你。这些你也是晓得的!这辰光,鲁叔没了,家业没了,你不会是⋯⋯想把这盆脏水浇在我头上吧!你⋯⋯”
见顺安竟然说出这话,挺举怒不可遏,一拳揍在他的腮帮子上。
挺举出手结实,顺安也不躲闪,被他重重地击倒在地。挺举仍不放过,俯下身,照他头上、身上挥拳猛揍。
顺安既不挣扎,也不还手,只将两手牢牢地护在头上,听凭他的拳头落下。
挺举越揍越不解气,正往死里揍,章虎慢悠悠地踱过来,冲挺举道:“姓伍的,你打够没?”
挺举站起来,扫他一眼,一个转身,大踏步径去。
章虎扯顺安起来,不无纳闷:“还手呀!哪有挨打不还手的理儿?真没见过这般打架的!”
顺安口里咕噜一阵,吐出一口血水。
啪的一声,一物顺着血水落在地上,是一颗牙齿。
章虎看向那颗牙齿。
顺安拾起牙齿,站稳身子,望着挺举渐渐模糊的背影,心道:“挺举阿哥,这顿打,加上这颗牙,算是补偿你了。”
夜深了。
鲁宅灵堂依旧亮着灯。
挺举一步一步地挪回来,一直挪到灵堂门口。
碧瑶、阿秀一边跪一个,依旧一动不动。
阿祥歪在地上,睡去了。
齐伯迎上,示意挺举走到院子里,小声问道:“寻到没?”
挺举点头。
“他不肯回来?”
挺举点头。
“是哩,”齐伯轻叹一声,“我晓得他不会回来的。老爷早就把他看透了,可惜小姐⋯⋯”
“齐伯,”挺举亦是压抑,转过话题,“鲁叔这⋯⋯是运回老家安葬,还是暂寄四明公所?”
“你哪能想哩?”
“照规矩,该让鲁叔魂归故里,可眼下不成。听祝叔讲,商会再不作为,市场整个就要崩塌,可商会里,老爷子走了,鲁叔走了,彭叔与祝叔不一心,其他各帮各行皆成零散,自顾不暇,很难召到一起,祝叔独力难撑,要我帮忙,我⋯⋯分不开身哪。”
“就放在四明吧。市场不能崩,公事紧要!”齐伯盯住挺举,“挺举呀,明日就要出殡,有桩事体,齐伯得先跟你打个商量。”
“齐伯您讲。”
“你鲁叔膝下无子,小姐顶不起丧盆。齐伯思来想去,这个丧盆⋯⋯”
“齐伯呀,”挺举流出泪水,“这事体不消讲了。我到上海后,鲁叔待我如子,鲁叔的丧盆,我责无旁贷!”
“有你来顶丧盆,你鲁叔也就安心了!”齐伯抹泪。
鲁俊逸的出殡仪式极是简陋。
前来送葬的多是老员工,少部分甬人也赶来送行。
几个吹手吹着丧乐。
二十四抬灵柩拴好,抬棺者分别是钱庄各把头、各店掌柜、阿祥等,全都是齐伯安排好的。他们各穿丧服,分别站在灵柩两侧。首杠是留给挺举的,空在那里。
老潘高唱:“摔丧盆!”
挺举走到棺前,跪下,拜几拜,长哭数声:“鲁叔—”将烧纸钱的灰盆拿起,捧过头顶,用力摔下。
丧盆啪的一声,碎为裂片。
老潘再次高唱:“起棺!”
全场起哭。
挺举走到空着的排头位置,抬棺。
唢呐声起,鞭炮齐鸣,花圈、纸人等被送葬的人纷纷扛着,走在最前面。
齐伯与几个女眷跟在后面。
碧瑶、阿秀没有眼泪,各被两个女人架着,像木偶一般迈着步子。
阿秀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箫,那是俊逸最后用过的。
挺举等扛着棺木走在中间,后面是陪同出殡的甬人,无不以泪洗面。
穿着长衫、戴着宽边毡帽和墨镜的顺安远远躲在看热闹的人群后面,偷眼看向抬棺的挺举,又看向被人搀扶着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的碧瑶。
会审公廨的两个廨员引领一队巡捕大步疾走过来,直奔鲁家。
两名廨员的手中拿着一厚沓子封条。
望见出殡队伍,这些人怔了,让到一侧。
顺安长叹一声,拉下帽子,扭身远去。
傍黑,四明公所义冢区寄棺房里,鲁俊逸的棺木上堆满花圈。
齐伯、挺举、阿祥、碧瑶、阿秀诸人一直守着。
祝合义走进来,在挺举耳边嘀咕几句。
挺举跟他出去。
二人来到济元堂,祝合义摆出一封电报:“有两个好消息,一是南京发来电报,朝廷同意以两江厘金与海关税银作保,向外国银行贷款救市,贷款限额为五百万两,要我以商会名义主持商谈。二是查理大班打来电话,说是英、德、法、美、俄、日等六家银行,同意救市,要和我们商谈具体条款,要我约定时间。六国银行公推汇丰查理大班、德华克拉姆大班、花旗爱德华大班为商约代表,商会也定三人,我算一个,你算一个,还有一个,你看啥人合适?”
挺举不假思索:“彭伟伦!”
“好,就他吧。”遂对外叫道,“来人!”
助理进来。
“去广肇会馆,请彭议董明天上午七时赶到商会,商谈向外国银行贷款事宜!”
助理应过,匆匆出去。
公所义冢区,阿祥飞快跑来,气喘吁吁:“齐伯,不好了,老爷宅第让会审公廨查封了!”
齐伯惊愕:“啥辰光查封的?”
“就⋯⋯就刚才!”
碧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惊战。
“小姐的行李呢?”
“让他们扔出来了。还有老爷、伍掌柜及您的东西,全都在院子里堆着,我这刚刚搬进门房里!还有钱庄和所有分店,全让他们封了。”
齐伯面孔冷峻。
“阿哥呢?”
“祝总理叫去了,在济元堂。你去对他讲一声!”
“好哩。”阿祥转身跑开。
齐伯缓缓跪下,双眼闭合,一双老眉重重凝起。
阿秀突然出声:“齐伯!”
齐伯睁眼:“阿秀!”
阿秀掏出钥匙,递过来:“你⋯⋯你们⋯⋯搬到这儿吧!”
齐伯看一眼碧瑶:“这⋯⋯哪能成哩?再说,你住哪儿?”
“我不想住了。我这陪陪阿哥,就回老家去。”
齐伯听她语气自然,没有多想,装好钥匙,微微点头:“也好。家里自在些。”
阿秀从身上摸出俊逸交给她的信:“阿哥出门时,要我过几日将这纸袋子交给你,这几日过了,我该交给你了。”
齐伯猜出是俊逸托付他的遗书,接信套的手微微颤抖,泪水流出。
夜深深。
四周阴森,秋虫鸣叫。
义冢区一棵树下,阿秀解下头上白白的孝巾,搭在最下面的树枝上,绾个结,又搬块石头垫在脚下,将头伸进套里,右手拿牢箫。
阿秀默默诉道:“阿哥,你说你永远陪着我,我这也永远陪着你。你哪能走的,我也哪能跟着。我把这箫也带上了,让你吹给我和阿姐听⋯⋯”
阿秀眼睛一闭,蹬倒石块。
商务总会与外国银行的谈判地点确定为汇丰银行大厦的四楼。会务厅里,长条几案两边,双方代表各自就坐。银行三个代表,查理居中。商会代表,祝合义居中。一份由银行方拟定的合同书中英文草案一式六份,各代表人手一份。
“这份草案由六国银行共同商议,汇丰银行执笔起草,提请贵会审议!”查理率先发话。
合义三人低头审看。
查理三人神情悠然,一边品啜咖啡,一边欣赏窗外。
“查理先生,”合义抬头,皱眉,“不是讲好贷款五百万两吗,合同上为何只有三百五十万两?”
“我们对贵方的偿还能力存有疑虑,先贷出这一笔,投石问路!”查理的声音不冷不热。
“我们是由**出面担保,偿还绝无问题!”
“我们担心的恰恰是你们的**。”
合义茫然:“我们的**有何问题?”
“你们是官员责任制,一任官员一任政,人亡政息。昨天是袁道台,今天是蔡道台,明天就可能是李道台或张道台。蔡道台任上的合同,其他道台如果不认怎么办?”
“我们一向遵守合同!”
“这是你们的商人,不是你们的官员。我们不信任官员,因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做事,不按照合同做事。我们要的是合同!你们的商人没钱了,只能靠**担保,所以,我们只能先贷这么多!”
合义长叹一声,接着往后看。
“查理先生,三百五十万,仅庄票就抵扣一百五十万,是不是有点儿⋯⋯”彭伟伦发话了。
“怎么了,彭先生?你们的庄票不抵扣,难道要我们上门兑现吗?根据初步统计,我们六家银行共收你们的庄票近三百万两,我们没有全额抵扣,暂先抵扣一百五十万两,已经是充分照顾你们的需求了。”
“这⋯⋯”
“A
yp
oblem?(还有什么问题?)”
挺举扬起头:“有。”
“伍先生,有何异议?”
“年息百分之八,太高。还款时限三年,太短!”
“年息百分之八,是银行贷款通例。时限三年,也是通例!”
“但凡贷款,没有通例,只有牟利。请问诸位先生,此番贷款,你们是想救市呢,还是想趁火打劫,乘危牟利?”
三个洋人面面相觑。
查理苦笑:“伍先生,此话何解?如此非常时期,我们愿意贷款,就是救市。既然是贷款,就要收取正常利息。我们收取正常利息,伍先生为什么说成是乘危牟利呢?”
“正常贷款,是正常利息。救市贷款,就当是救市利息。我们是为救市贷款,你们是为救市出贷。你们对出贷救市的款收取正常利息,就叫乘危牟利。如果是正常贷款,正常担保,请问诸位,有没有客户一次性贷款三百五十万两?若是有,对银行来说这将是多么巨大的生意。真有这样的好生意,似乎不该是我们来求你们吧?”
查理语塞:“这⋯⋯”
“还有,查理先生,”挺举拿出一册书,摆在桌面上,“这是你们的公司法,按照书中所讲,凡是破产企业,就当以破产看待。茂升等七家钱庄既然已经宣告破产,你们为什么还要抵扣它们出具的庄票?”
查理再次语塞,看向其他二人。
三个洋人皆是怔了。显然,他们在应对中国企业时,从未考虑过他们曾经立过的这个法。
“伍先生,”查理寻到解释,“破产法是针对我们公司的,你们是钱庄,不是公司,我们的公司是有限责任,你们的钱庄是无限责任!”
“查理先生,”挺举侃侃应道,“有限也好,无限也好,都是破产。产既然破了,你让它们如何负责?产是它们的,赚钱赔钱都是它们的,既与**无关,也与市场无关。如今它们破产了,你们却让与它们无关的**与市场负责,这合理吗?再说,这些钱庄是承办你们洋人的橡皮股才破产的,换言之,它们破产是因为与你们洋人做生意。中国企业是无限负责,中国人之间做生意,父责子还,理所应当。然而,眼下是中国企业与你们洋人企业做生意,按照这些年来的惯例,如果中国企业没有守约,你们就会告到会审公廨,用你们的法律来制裁。既然你们总是使用你们的法律来制裁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今天破产了,为什么你们又不用你们的法律了?”
查理三人显然没有料到伍挺举会讲出这个理,各吸一口长气。
“三位大班,”伍挺举语气恳切,“我们贷款是为救市,你们出贷为的也是救市。既为救市,就不能按寻常贷款计息!上海各业遭此重创,恢复期至少需要三到五年,而你们在三年之内要我们还贷,这不利于市场恢复!”
“依伍先生之见,如何计息方为妥当?”查理问道。
“无息!”
在场诸人,包括祝合义、彭伟伦也是一怔。
德华大班克拉姆啜一口咖啡,嘴角一撇:“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异想天开!”
花旗大班爱德华笑着应和:“Yes.”
“中国人还有一句成语,叫杀鸡取卵。”伍挺举端起面前的茶杯,悠然地啜一口,淡淡回应,“你们是想吃这只鸡慢慢生出的蛋呢,还是想杀死这只鸡呢?相信诸位不会如麦基一般目光短浅吧!”
“伍先生,你们稍坐,容我们商议一下!”查理说完,招呼二人。
望着三个洋人走出房门的背影,彭伟伦不无担心:“贤侄呀,你这要求有点过了,哪有贷款不出息的理?”
“是哩。洋人讲规矩,定了的事是不会变的!”祝合义附和。
“彭叔,祝叔,”挺举坦然一笑,“既然是做生意,就要讨价还价。我这么讲,不过是给他们留足打折扣的余地!”
话音落处,三个洋人由外面进来。
查理的语气较前缓和许多:“伍先生,祝先生,彭先生,我们一向遵守规则。我们决定,茂升等凡是宣布破产钱庄的庄票,暂不列入抵扣,但尚未宣布破产的钱庄,其庄票必须从贷款中扣除。贷款年息定为百分之四,贷款期限放宽至五年,可以吗?”
合义三人相视,轻轻点头。
“好吧,就这么定下。”祝合义拱手,“我代表商会,代表上海各界,谢谢查理先生,谢谢克拉姆先生,谢谢爱德华先生!”
“不必客气。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可以签约了。”
阿秀追随俊逸,断气之后仍旧握着那管箫。齐伯做主,打开俊逸的棺木,将她放进去,使二人相依相偎,再把那管箫摆在二人中间,箫口放在俊逸唇边。
天气湿热,俊逸的尸体开始腐烂,散发出刺鼻的味道,但碧瑶执意不离开。齐伯无奈,强行拖走她,召来马车,载往阿秀家。
天已傍黑,阿祥忙着收拾院子,将阿秀的被褥换作碧瑶的。
碧瑶坐在院中,冷冷地看着他们。过有良久,碧瑶抬起手腕,目光落在顺安送给她的翡镯上,眼里盈泪。
齐伯端出一碗粥,走过来:“小姐,喝碗稀粥吧,是齐伯专门为你煮的,不冷不热,正合口!”
碧瑶擦把泪水,接过粥。
“小姐,”齐伯声音柔和,“待阿祥打扫好,小姐就可到楼上去了。这个院子虽说不大,却也啥都齐备呢。”
碧瑶的泪水再流下来,滴进粥碗里。
“小姐,甭伤心了。心是伤不完的,身子骨儿要紧。我这为你换碗粥。”齐伯说着,伸手去拿碗。
碧瑶似是没听见,将碗放到口边,将和泪的粥大口喝下。
碧瑶喝得很猛,似乎要把所有的苦与怨一口气喝进肚里去。